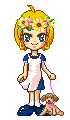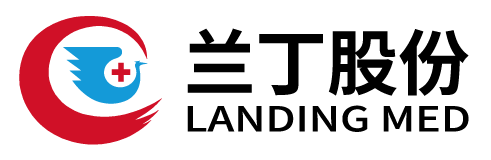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长篇小说连载)爱,永不止息(全文完)
一切安排好之后,彦锐才顾得上我。再次在QQ上相遇,彦锐明显感觉到我情绪不对。
我的有意疏远,还有带刺儿的说话方式。
“怎么了,丫头,是不是怪我这一阵子没理你呀?”
“没有。”
“我真的是太忙了,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
“嗯。”
“这段日子,你还好么?”
“还好。”
“你生气了,我能感觉的出来。”
“说了没有。”
“那是怎么了?”
“没怎么。”
。。。。。。
彦锐不说话了,对话框里的光标静静的闪烁,我不知道要如何对彦锐说我心里的彷徨与矛盾。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却不敢张口,怕张了口之后狠心下的决定,抵不过对彦锐的三言两语,三下五除二的就被他缴了枪,不得不乖乖的举双手投降。
看着彦锐暗下去的胖企鹅头像,心里很是难过。想想这般突兀的对他冷漠,总归太伤人心。我只是不想自己爱上彦锐,却从没想过要与他形同陌路。彦锐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我。
我犹豫了一下,发过去一个笑脸。我知道彦锐还在,只是还在为我刚刚的冷漠而独自生闷气。
果然,他很快的发回一个委屈的表情,接着又是一个哇哇大哭的表情。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对彦锐,我真的狠不下这个心,他像个既淘气又耍赖而偏偏又招人喜欢的孩子,让人舍不得丢不下。
叹了一口气,给彦锐发过去一个拥抱,彦锐这才转悲为喜,回了我一个大大的笑脸。
以后再说吧,无论如何,我不想在彦锐事业刚刚起步之时,让他难过。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三十七)
彦锐到了新单位后,生活变得很忙碌,但每每有时间休息,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和我在网上聊天。也许,这种交流方式,不管对他还是对我,都已经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习惯。
由于彦锐是新人,一时间还接不到什么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忙活所长的案子,做一些琐碎又繁杂的事情。
做律师这一行,和从医很不一样,不能守株待兔,而要主动出击。这就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熟人介绍熟人,朋友介绍朋友,慢慢的逐渐形成自己的客户群。彦锐初来咋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这对他不是什么难事,那么多年在社会上的摸爬滚打,不是白白混的。
彦锐从搞好同事关系下手,请一些小科员偶尔吃吃饭,送送小礼品,吃饭的时候一起谈天说地,很快就熟识起来。其实即便彦锐不这么做,单单他的帅气和魅力就已经将那些小姑娘们迷的五迷三道,每日有事没事围着彦锐打转。彦锐笑眯眯的和众妞打着哈哈,但总会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既不近,也不远。
彦锐和我提起这些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的泛着酸水,臆想中将他抓、挠、扣、掐了无数遍,还给他起了个外号,“花蝴蝶”。
我酸溜溜的问他,那么多妹妹,有没有一个入你法眼的?
彦锐似乎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暂时没有。
我心里的大石放了下来,但彦锐的一句话,又让我提高了警惕。
不过,有个小妞儿我倒是挂念了很久,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我一听之下心头刚刚落下的石头又悬了起来,急忙追问,谁?
你!
彦锐这个坏蛋!
不过,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甜蜜。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三十八)
彦锐突然的告白,让我既高兴又难过。我想接受,但理智上又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感性的我和理性的我,在同一个身体里争吵不休,搅的头要炸开一样的疼。
我打着哈哈和彦锐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借口有事出门,急匆匆的下线。
第二天,彦锐依然没事人一样和我聊天。反倒是我,一颗心像是装了无数个秘密,说话颠三倒四,不知所谓。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天,我被自己折磨的异常烦躁,本来已瘦成一条的小脸更加惨白,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总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骗彦锐这几天有事不能上网,然后彻底让自己冷静一下,想个明白。
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两只胳膊枕在脑后,瞪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想着我和彦锐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说心里话,彦锐是一个不错的男人,或者说,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男人。文雅、幽默、沉稳、练达,有上进心,有事业心,有正义感。对我温柔又细心,我的坏脾气,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的包容。尽管我总说彦锐像孩子,其实我才是任性的孩子,还未长大。
这样的好男人,我配么?
我的自卑心又开始作祟。想起我平凡的样貌,想起我支离破碎的家,想起目前的窘境,想起未明的前途,心里乱如一团麻。
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清晰的收入耳中,大家都睡的很香,很沉。我又翻了一个身,将身子弓成一个虾米,又胡思乱想一番,不知什么时候也昏昏入睡。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三十九)
梦中,我梦见了去世的母亲,拉着我的手,似乎有话要和我说。我抓住她的衣角,哭着说我想她,可一眨眼,母亲就不见了。于是,我哭着醒来,枕巾早已被泪水打湿。
母亲去世后,最初我每晚都梦到她。梦见她坐在老家的土炕上,盘着腿,弓着背,脸还是那样浮肿而苍白,眼神呆滞的望着窗外。因为,透过那一片窗,总能清晰的看见我回家的小路。
有时候我在梦里和母亲哭诉,和她讲离开之后我的苦涩和艰难,母亲怜惜的看着我,却不说话。有时候,母亲还和从前一样,拉着我的手,和我唠家常,讲到开心处,会动情的在我手上拍两下。
再后来,母亲渐渐淡出我的梦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将母亲淡忘,又或者,是母亲的魂魄有意让我淡忘,总之,母亲不再那么频繁的出现在我的梦中。
学医的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我历来不相信神鬼之说,不信奉任何教派,不追捧任何神圣。我只信自己,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但母亲去世之后,我总盼望着能再和母亲相见,于是很想相信,这世间果真有另外一个空间,能让母亲的魂魄所依,能让我们母女相见。
我不怕鬼,甚至希望见到母亲的鬼魂。
我记得,将母亲火葬之后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因为夜里要打更,只留我一人在家守着偌大的房子。住在隔壁的姑姑问我,怕不怕,要不要到她家去睡?我说,怕什么,就算是母亲的魂魄回来看我,我喜欢还来不及,又怎会怕?
我总觉得透过窗子的一角,母亲站在窗外在黑暗中凝视着我。姑姑听我这样说,吓的嘴唇都白了。说了几句闲话,就匆匆的离开了我家。
我穿上鞋子,跑出门外去看,院子里静悄悄的,唯有树影在晚风中微微摇曳。
回到房间里,那种感觉又回来,于是又跑出去看,如此折腾几次,终于无奈的作罢。
醒来后,拉开窗帘,寝室里洒进一片灿烂的阳光。我坐在床上,眯着眼睛想刚刚未做完的梦,母亲在梦里,到底想和我说什么?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冷静了几天,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还是和彦锐做朋友,或者是知己,但不能是恋人。彦锐这样一个好男人,值得比我更好的女孩去珍惜他。
再次在网络中见到彦锐,他很兴奋。和我撒娇,逗我开心,向我嘘寒问暖。我心里针扎一样的痛,但还是强作欢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我有意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走钢丝一般,小心翼翼握着手中的平衡杆,不能太热情,也不会过于冷漠。只是平淡,平淡的像无味的茶,虽能饮,却无茶香。
我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告诉彦锐因为老板下达了任务,要求把科室里的一万张病理片在毕业之前看过三遍。以我目前的水平,那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甚至在镜下尚不能看出一个完整的圆,进度慢的如同蜗牛。所以,我要下苦功多读书。还认真的数了数书架上的专业书,告诉彦锐一共有十几大本等着我去读。
理由是真的,老板也确实是这样要求我做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但只有我知道,这根本构不成我疏远彦锐的理由,只能叫做借口,一个掩饰自己的真实的借口。
彦锐心里虽然十分不愿意,但还是十分理解的同意了我的要求,不会再过于频繁的和我聊天。只说,丫头,你要注意身体。我看了,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彦锐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也许他那时已经猜出了我的意图,但只是没有挑破。
我记得他那一晚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还是朋友么?”
我咬着嘴唇发过去一个笑脸,然后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悲伤,趴在书桌上放声痛哭。
从那之后,彦锐不再每晚找我聊天,但还是偶尔会发过来一些留言。有关心的,有逗我开心的,还有一些关于他的零零散散的消息。我每次看到他的留言,心里又温暖又悲伤。
这一切,就是我想要的结局么?
如果是,为何如此难受,心疼的快要不能呼吸;如果不是,那我想要的,又是什么?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一)
发泄痛苦、麻痹神经的方法有哪些?狂哭,狂发脾气,狂吃,狂工作?我掂量了一下,挑了一种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来麻痹自己,疯狂工作。
由于还是个学生,也无所谓工作,不过是白天在化验室值班时跑的勤些,动作快些,话少些,弄疼患者多一些。
不值班的时候,把自己关在病理室里,整天闷头看片子。从技术室抽出一盒盒的片子放在身边,一张接一张的看,对着报告看,对着书看。
接触病理一年多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在镜下看出一个视野,而是两个圆圈。这让我很苦恼,也很难过。我向很多人请教如何能看成一个圆,问也问了,说也说了,但始终还是两个圈圈。无奈之下,放弃了这种奢侈的幻想。心想,反正能看到就行了,管他一个还是两个。
却怎知,在一个特平凡的下午,我微微调了一下目距,竟然神奇般的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圆。和原来的两个视野的大小相比,不知要大上多少倍,也清晰多少倍。我一眨不眨的盯着镜下的图片,怕一闭眼就失去了眼前的景象,双手因兴奋而有些发抖,心里高兴的想大叫一通。
这一张片子像看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我不知道原来这些细胞还可以这么清晰,这么鲜艳,这么好看。直到这张片子看的想吐了,才极不情愿的把视线挪出了目镜。
会不会只是一时巧合,下一张还能看成一个圆么?我心里犯了嘀咕。
又抽出一张片子,重新坐在显微镜前,再次从目镜里望进去,调整了一下焦距后,依然还是一个圈。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能够完美的由二变一,我很欣慰。
有一次,小雅、芳芳和我,三个人一同在病理室看片子。我挨着小雅坐,芳芳在我俩身后。我抬头换片子的时候,瞥见小雅一会戴上眼镜,一会摘下眼镜,如此反复。
我好奇的问她,那是干嘛,不嫌麻烦?
小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着我,指着我的眼镜说,你看片子的时候也戴眼镜?
我说,是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么,你不戴?
小雅又问,能看清?
我笑了,带着眼镜还看不清,这镜子不是要淘汰了。
小雅又问,不别扭?
我糊涂了,别扭什么?我从来没觉得我在戴眼镜。
小雅看猴儿似的看着我,终于摇了摇头,竖起拇指,还是你牛!
我一直不明白,看显微镜和戴眼镜有什么冲突。小雅说我是一个怪人,不能理解常人的思维。我说小雅瞎讲究,一会摘一会戴的,不嫌麻烦。
直到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参加了一次医学会议,有一名我崇拜已久的皮肤病理专家在会议现场阅片会诊。我意外的发现,他也是摘下眼镜看显微镜,再戴上眼镜看图片,和小雅当年一模一样,如出一辙。这一次,我真的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怪胎。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怪胎还有没有,所以,留心了一下单位里大病理室的同事们,大家不约而同的重复着摘眼镜戴眼镜动作,要么就是一直不戴,看过显微镜后,几乎趴在桌子上看报告。
我是特例么?是么?但愿不是,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二)
白天我用工作麻痹自己,晚上下班之后,直接抱着两本书去教室学习。我怕打开电脑,怕看到彦锐的留言,怕自己忍不住,又去找他。
在教室里待了几个晚上后,还是无可奈何的回到寝室。教室里一双双一对对情侣的甜蜜背影,扎的人心里更加难过。躲了前面,躲不了后面,躲了左边,躲不过右边,我躲来躲去,把自己躲进一个角落里,结果一抬头,全教室的情侣都赫然收入眼底。我的心啊,像三九天掉进冰窟窿里,拔凉拔凉的。
回到寝室后,趴在书桌上,无精打采的翻着砖头一般厚的专业书,好半天不翻一页。那些枯燥的文字,再也没了吸引力,眼睛盯着一行字看了五六遍,还是不知所谓。干脆合上书,打开了电脑,也习惯性的登录了QQ。
一上来,就看到彦锐的留言。
“丫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接到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案子。虽然只是个小案子,但得来不易。你还好么?看书不要太用功,小心眼镜度数又要涨。”
“丫头,我今天发工资了。虽然没有在北京的时候多,但心里很开心。在现在的单位里,能够学有所用,这比什么都值得庆贺。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请你吃饭。”
“丫头,我鼻炎又犯了,早上一起床,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用冷水洗了脸后,脸又有些肿,抓起来好痒。你这个专职医生做的不合格呀,连自己的病人都不管了。”
。。。。。。
彦锐一个又一个的留言,看的我既窝心又伤心,看到后来,心又开始疼了。
谁来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
上帝刚刚睡醒,恰好听到了我的乞求,于是打着哈欠派来了天使,我最好的姐妹,小七妹。
这丫头对着我,轻飘飘的挥舞了一下手里的魔法棒,大声的说,我要光!结果我的世界,真的光明起来!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小七妹是我读本科时同一寝室的姐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行七,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七妹。
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热情、阳光、积极、活跃,和我的性格截然相反。她身上有一种魔力,任何靠近她的人,都会不知不觉的被她活泼的性格所吸引。如果说我是一潭平静的湖水,那她就是一团跳跃的火焰,都说水火不相容,可性格的互补,却反而让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整日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起温书,一起逛街,甚至床铺都是挨着的,睡觉时头顶着头。
小七妹是个热心肠,为人仗义,乐于助人。虽然家庭条件优越,却从未因此瞧不起穷苦出身的同学。因此,她交的朋友,多是出身贫寒,却又极其优秀。多年之后,她的那些朋友们,多是博士或是博士后,不是出国留学就是在海外工作,即便留在国内的,也多是某名牌大学讲师或某著名企业精英。而我,则是她交的诸多朋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
如此古灵精怪的一个丫头,又长了一副可人的样貌,身边的追求者自然少不了。追她的男生,一个排都不止。那些男孩们卯足了劲,变着花样的追求方式,让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乡下妞,看的眼花缭乱,羡慕不已。
她的那些感情经历,从来都乐于同我一同分享,这也是我枯燥的大学生活中,不为多得的一点生活乐趣。那些男孩们写给她的求爱信,足足有一个纸盒箱。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她一起读那些情意绵绵的信。周末的时候,同她一起回本市的家里,两人窝在床上,倒出一箱子的信,一边读一边听她讲那些男孩的故事。读到有趣之处,一起笑翻在床。那些故事,每一个都比那些虚构的爱情小说,更精彩,更有趣。
可以说,我见证了七妹的每一段感情经历。看着她在感情的世界里慢慢成熟、稳重,虽然几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找到了那个最适合也最疼爱她的人,从此相知、相爱、相守。看着她甜蜜幸福,看着她披上嫁衣,为她祝福,替她开心。直到她成了孩子的妈,但在我的眼里,依然是当年那个活泼风趣的小姑娘,依然是我可爱又可敬的小七妹。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四)
正当我矛盾万分之时,网上偶遇小七妹。我如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拉住她,把我和彦锐的事,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和盘托出。讲完后,问她,我该怎么办?
七妹就一句,若是不爱,就及早放手;若是喜欢,就不要错过。
醍醐灌顶!
犹豫了一下,我又怯怯的说,我怕,怕受伤。
七妹一针见血,没试过,怎知一定受伤。
我惶惶的说,我怕自己配不上彦锐。
这一回妹妹怒了,顷刻间噼里啪啦发来一串话。你堂堂某名牌大学医学硕士,端庄文静,知书达理,性格温婉,家世清白,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怎么就配不上他?再这样贬低自己,小心我杀过去,扁你一顿。
七妹就像一门迫击炮,发射的炮弹,眨眼间就将我的种种顾虑消灭殆尽。动作干净利落,且连死角都不留。最后一颗还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轰”的一声在我头顶炸开,将我厚厚的盔甲炸的稀里哗啦。散落一地的甲片,还“嘶嘶”的窜着轻烟。
不愧为小七妹,大学时代几年的团支书真不是白当的,三言两语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针针见血。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的七妹妹,心里的窗终于打开了。
阳光,撒进心房。心不疼了,而是,温暖如春。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五)
我满心欢喜,准备向彦锐告白。偏偏上天弄人,彦锐因公出差,乡下地方,通讯闭塞,连上网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等他回来再说。
心里像踹了只小兔子一样,每天惶惶不安。既盼着彦锐早点回来,又怕彦锐回来的太早。
表白的那一刻,真怕自己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初夏过后,天气越来越热。每天穿着白大衣在值班室里忙来忙去,一会的功夫,就出了一身的汗,黏黏的贴在身上。
炎热的午后,头发湿嗒嗒的粘在额头上,我右手握着移液器,左手握着试管,眼睫毛上热得快滴出水来。一次性口罩上的塑料杠,将鼻梁硌的痒痒的,抓又不能抓,歪过头,抬起胳膊,将鼻梁在上面蹭了几下,又继续埋头做化验。每一次操作都马虎不得,一桌子的血液试管,不是查梅毒,就是查艾滋病,哪个我都都惹不起。哪怕沾到一丁点,心里都会惶恐不安。
偏偏那一阵子,经我的手连着查出几个艾滋病。技术员及上级医生对此很重视,经过反复审核和多次重做试验后,确认我的报告无误。
其中一个患者来取报告时,刚好我在。那是一个相貌清秀的男孩,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孩,高大帅气,很有男人味。
看着两人有些躲闪的眼神,还有似有似无的亲密小动作,我一下子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是一对男男同性恋。
门诊经常会看到这一特殊的人群来看病,尽管有些时候是其中一个独自前来,但作为医生,只要一看发病的部位,和皮疹的分布和形态,心里已经猜出几分。
对于这一特殊人群,我起初很不理解,甚至很是厌恶。男人的娇媚,让人看了,心里总说不出的翻江倒海。直到后来有了电脑之后,机缘巧合下,看了那几部反映男同性恋的经典电影,如《霸王别姬》《东宫西宫》《蓝宇》,才隐约发现,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情,也可以那样的缠绵悱恻,动人心弦。
世界让人越来越看不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在这样一片小小的天地里,我即便半眯着眼睛,也能撇见到那么多的千奇百怪和惊世骇俗。爱情,婚姻,家庭,在欲望面前,总是那么不堪一击。
透过这一副镜片,静静的看着小小门诊里上演的世间百态,我越来越怀疑,这世上,是不是真的存在永远不变的誓言,和永不变心的爱情。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六)
化验室热的像蒸笼,没办法,从病理室翻出一台弃用很久的电风扇,放在化验室的窗台上。虽然它的大头已经锈迹斑斑,并且不见了防护罩,按钮也不甚灵光,但接上电源后,还是善解人意的送来一阵阵凉爽的风。
午后的日光很毒,透过窗子照在椅子上,不小心坐上去,烫的人龇牙咧嘴,跟老家冬天里的热炕头似的。太阳晃得我眼花,于是起身去拉窗帘,想遮住刺眼的阳光。刚刚伸手去拉窗帘,中途经过风扇的手,“刷”一下就被快速转动的扇叶刮了一下。还没等反应过来,手指上的血已经汩汩而出,顺着手指、手腕,滴在地上,像一朵朵绽放的血色梅花。
看到了血,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没有痛,只觉得整根手指都是麻木的,像打了麻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处置室,护士长和护士兰姐看我这副样子,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儿,帮我处理伤口。口子很小,但割的很深,恰巧在指尖上。都说十指连心,这话一点没错。直到包好了,我才缓过劲儿来,钻心的痛。
回到化验室,看到一路血迹斑斑,娘啊,真够血腥的!
手指伤了不要紧,活儿没法干了。小雅和芳芳恰巧不在,愁的我满地乱转。恰巧大师姐在隔壁诊室出诊,看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晃来晃去,便过来看我。
可找着亲人了,我举着包的像粽子似的手指头,跟大师姐一顿抱屈。
大师姐是老板的开门弟子,毕业后就留在了科室。性格沉稳、干练,对师妹们呵护有加,对我们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有时候,我们几个有了事情,不是先想到老板,而是先找大师姐商量。
师姐看我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呀......
“你呀”之后,再无下文。综合我平时的表现,我知道师姐未说出的潜台词十有八 九是,“怎么总是马马虎虎,毛手毛脚,什么时候能稳当一些呢?”
我伸了伸舌头,用另一只手搂住师姐的胳膊,跟师姐撒娇,“下回一定不这么马虎大意了,俺向毛主席保证!”
于是,整个下午,师姐一边出门诊,一边帮我忙活化验室的活儿,好在病人不是很多,不然,我真是罪过了。
多亏师姐提醒,才想起要去打破伤风疫苗。平时看着患者跑来跑去跟走迷宫一样的挂号、缴费、领药,总觉得没什么。轮到自己时,排队挂号、排队领药、排队打针,楼上楼下的跑,折腾半个小时这针才算顺利的扎上。
老百姓的话说的一点都没错,看病,还真是难!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七)
晚上回到寝室,手指又热又疼,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找出几片消炎药,吞了下去。想了想,又掏出一瓶维生素C丸,倒了两粒,又吞了下去。
没来由的,右眼皮跳了一下,心里慌慌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要有祸事了?
这种感觉,在母亲临终的那天早上有过。这次......
呸!呸!胡思乱想什么,手指头伤了,脑子也秀逗了!
晃了晃头,翘着手指头从书架抽出一本专业书,认真的翻看。可看着看着,心越来越慌,眼皮也跳的厉害。
干脆合上书,打开手机,按下快捷键,给父亲拨了过去。好半天,父亲才接了电话,我急忙问,怎么这么久才接。父亲说,看电视看睡着了,才听到。我又问,爸,你最近还好吧。父亲睡意朦胧的说,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吧,照顾好自己才是。
和父亲聊了一会,知道家里一切安好,先前悬着的心才算落回原地。
爸,你千万要好好的。我在心里默默的说。
又捡起书接着看,看了没几行,又想起彦锐。他出差走了几天,一直没有消息。不会是他出了什么事吧?但愿不是,千万千万不要。
匆匆忙忙打开电脑,找到彦锐的头像。灰的,不在线。
不死心,又打了一个问号过去,没反应。看来,真的不在。
我从来没有那样急切的想找到彦锐。彦锐,你到底在哪儿?
担心了一个晚上,快要关电脑就寝时,彦锐的头像突然亮了起来,又很快的回给我回了一个笑脸。
我的一颗心,这次,才真真正正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放回了原位。
夜里,睡的很熟,很踏实。
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场噩梦,已经悄然开始。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四十八)
第二天刚上班,芳芳神神秘秘的拉住我和小雅一起去病理室。一路上,芳芳低着头不说话,我和小雅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心里升起不详的预感,莫非真的出了什么事?
进了病理室,芳芳转身关好门,让我俩都坐下,自己坐在我俩对面,低着头,沉默。
空气中流动着压抑的气息,让人透不过气来。小雅终于忍不住,拉住芳芳的手说,“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事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我们能帮忙的一定帮。”
芳芳抬起头,脸都白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芳芳,抿了抿嘴唇,最后叹了一口气,小声说,“不是我,不是我出事了。”
我和小雅齐声问,“那是谁?”
“是老板”芳芳颤声的说,“老板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俩离开椅子,紧张的盯着芳芳。
“你们俩千万要挺住啊~~~”嘴里这样说,我却看到芳芳全身在颤抖。
“快说!!”我和小雅异口同声。
“老板去世了~~~”芳芳说完这个爆炸性新闻,一张脸更加苍白,一双眼快要汪出水来。
“什么?!”“这不可能?!”我和小雅惊讶的冲着芳芳喊道。
老板身体一向还好,就是偶尔血压会有点高,没什么其他大毛病,怎么会突然。。。。。。
芳芳舒了一口气,将她刚刚从小师妹和大师姐那里听到的消息,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俩。
连着几天,我们几个学生谁都没有见到老板。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上周四的集体阅片。那天老板无意中提起这一阵子胸口偶尔疼,我们几个学生劝他去检查一下,平时少抽烟少喝酒。老板笑呵呵的答应了,却依然烟不离手,酒局照赴。
由于师娘出国在外,老板和师娘两人常年分居,唯一的女儿又在学校寄宿,所以,老板经常一个人在家。如果说屋子里还有其他什么活物的话,只能算上鱼缸里的几条鱼和一只小狗。
几天了,见不到老板踪影,大师姐连着打了几个电话给老板,都无人接听。打电话到家里,依然如此。大师姐很担心,和几个小师妹聊天的时候提了几句。两个师妹听了之后,一起去了老板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开,心里突然有了不祥的感觉。于是打电话给老板的女儿田田,田田在男友的陪同下急三火四的赶回来,推开门一看,老板躺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门窗皆完好无损,但为了稳妥,大家还是报了警,通过医学鉴定,确认是突发急性心梗。死亡时间,大概就在头一天夜里。
我听到这里,心跳慢了一拍。那不正是我眼皮跳的厉害、心慌难安的时候么?
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彦锐,却唯独没能想到老板。
天意弄人?
孰之过?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