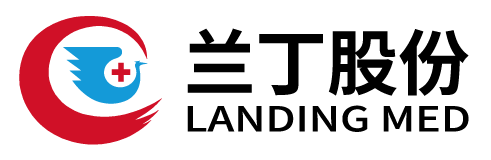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长篇小说连载)爱,永不止息(全文完)
| 以下是引用花开茶靡在2010-7-26 11:52:00的发言:
爱这个字含义很广,友情、亲情、爱情还有其他的感情,一篇文章里若来来回回只是围绕爱情打转,那不是一篇能打动人心的好文章,顶多算是一本粗糙的言情小说。
爱的味道是什么?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如果单指爱情而言,个人觉得,那味道更像茶的清香。而品茶总是由浓到淡,细细品来,满口余香。一直浓的是糖水,但糖水喝多了容易腻,还要小心血糖高。
我看不见你想说的那个字是什么,“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看到了什么,和内心有着莫大的关联。至于永不止息的是个体还是性别,这个问题,本就不该问出口的。如若您果真在“细细地读”,那答案自然就在心中。 |
我来填个词吧,爱生活!呵呵~花花姐是个爱生活的人~
刚看了你住院医考试那段,竟然可以自己下载模拟题?今年的规范化培训考试中心在卖这个模拟题,好像是几百块钱多少套题来着!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呵呵,不过好在我过了~考试挺折腾人的!

- 眼看,心悟,博览群书,行万里路~爱家爱国爱自己!
那谁说了,“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会有的。”我这块海绵还能挤出更多的水么?姑且一试,也许还有那么点点发呆的时间可以用来构思一下小说。至于动笔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更新日期。具体是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总要忙过这一阵子,也许是下个月,也许是下下个月,or next year~~~~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三月份排在急诊科轮转,日班、中班和夜班倒的人黑白颠倒,有点怀念在老家的舒服小日子。
有一天,在急诊大厅里门口无意中撇到有一名女记者在采访外科的一名医生。原来是一个智障患者玩火把自己和家里的房子点着了,全身大面积烧伤,报社记者得到消息后,立即赶来做现场采访。
我想起彦锐曾经和我提过的那个小记者,于是趁不忙的时候给彦锐发短信,问他那个小记者怎么没想到到医院去蹲点?我这儿就一个采访的不亦乐乎的,这可是第一手新闻。彦锐回我,这招那丫头早试过了,还用你提醒,没用。他问我,你很闲?怎么想起来关心她的事情了。我讪讪的答,我吃饱了撑着了,闲着没事做了。发完短信赌气坐在长条椅上闷头写病历,死彦锐,臭彦锐,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
四月初,小毕突然提出要搬家。我很吃惊,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要搬走。
小毕一开始还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后来架不住我死缠烂打,只好告诉我,再这样和我合租下去,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我合租和他找对象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拦着不让他找。小毕一摊手,无奈的说,我要真带回一女孩,你和我合租着,人家不还得多心啊。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我自从来到南城就和小毕一起合租,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商量着办,心里早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看待,突然间说要搬走,心里感觉怪怪的。但为了这哥们的终身大事考虑,俺还是收起了那丝丝难过和不舍,和他一如既往的贫着,“有空常回娘家来看看啊!”
小毕很快找好了房子,在一个离市中心有些距离的住宅小区,自己租下了整套房子,当起了二房东。将旧房子粉刷一新后,小毕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参观他的新家。嗨,还真不赖,一进门的客厅大得能打羽毛球。三个卧室,一间书房,租金也不贵,唯一不好的就是一楼,相对有些潮湿。
做了二房东的小毕很快在医院里找到了室友,一个ICU的男护士,挺机灵的一个小伙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嘴特甜。我在ICU轮转的时候,一口一个程昱姐,任谁听了都觉得受用。
小毕搬走的时候正是租房的淡季,我在院内网上挂出的出租启示好久无人问津,于是自己在这套不算宽敞的老房子里独自住了一段时间。小毕的离开,表面上我表现的满不在乎,心里其实特难过。那感觉就像身边突然少了一起奋斗过的战友,把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扔在了战场上。而且那段时间彦锐很少上网,更很少电话联系。于是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无助感,心里空荡荡的。
空虚用什么来填满?一是吃,二是玩。
我向来对玩不感兴趣,况且当了那么多年的乖孩子,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于是,我把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吃上。街面上的东西好吃的太贵,便宜的又不好吃,想经济又好吃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乎,兴致勃勃的买来了锅碗瓢盆,甚至菜板和擀面杖,自己玩起了过家家。
老妈在世的时候心灵手巧,厨艺针织女红乃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这个才女老妈却愣没能把她这一身的本领传承下去。到了我这一代,除了勉强会做几样面食之外,其他全是一头雾水。
自己填饱肚子很容易,最常做的就是饺子,一次包出许多许多的饺子分批冻在冰箱里,冻好了装在口袋中,留着以后慢慢吃。饺子吃腻了,就煮米饭蒸鸡蛋羹,拍个黄瓜,拌个凉菜,再不济炸碗鸡蛋酱蘸着黄瓜吃,也能吃的心满意足。
那是我来南城之后吃的最幸福最满足的一段日子,一个人吃饱了把桌子推到一边,歪在床上看电视剧。看困了就睡一觉,睡醒了换个姿势继续歪着,直到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才把残羹剩饭收拾下去,扔进水槽里,等到下顿之前再去刷。
这样浑浑噩噩又逍遥自在的日子过了一个春天之后,我猛增了二十斤。原来苗条的小蛮腰突然就变成了水桶腰,一张瓜子脸成了胖猪脸,衣服也瘦了。眼看着夏天就要来了,那条去年穿着还有些肥的蓝裙子愣是扣不上扣子,两片衣襟中间隔着一巴掌的距离,却只能相视而叹。
我拍了拍奇迹般长出来的游泳圈,无奈的坐在阳光里,叹息着。郁闷中,鬼使神差的想起家乡一句老话,“养肥了,该出圈了。”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89)
转眼到了六月份,我终于找到了合租的室友,是本院的两名小护士。我把大一点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们,自己搬到了小一点的主卧。
两个妹妹都不错,脾气性格都和我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做吃的,有什么好东西好玩的都一起分享。日子变得轻松愉快,而我的体重也直线上升。
一次在单位里遇到年初一起轮转认识的同事,惊讶的指着我的一身肥肉说,“呀!几个月不见,怎么胖这么多!”我这个难过呦,不自在的扯着自己的衣襟,脸红到脖子根。
是呀,怎么说胖就胖了呢,像吹气球一样。这个,是不是得减减了?
于是有意识的少吃,但忍了几天,饿的眼冒金星,走路都在打晃。饿了几天,终于忍不住大吃了几顿,结果反而比原来更肥了。此路不通,只好加强锻炼。和护士妹妹一起跳健美操,做仰卧起坐。坚持了一个月,掉了两斤,似乎也没多大效果,后来也再没坚持。
七月份在杭州召开本专业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本来在外面轮转是没机会去的,由于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去杭州玩玩,于是央求主任准我去见识见识。主任见我说的可怜见的,又无限向往,于是爽快的答应。于是,有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杭州之行。
第一次去杭州,却是个雨天。连着下了几天几夜,淅淅沥沥的,连绵不绝。即便如此,还是趁着开会的间隙,拉着一个学生陪我到西湖转了一圈。西湖边的垂柳随风轻荡,湖中泛着几只轻舟,三五友人坐在小船内品茗聊天,船娘带着斗笠披着蓑衣在雨中摇着船桨。像是一首诗,又如一幅画,这便是烟雨江南吧。
在断桥上留了一张影,又远远的望了望雷峰塔,天色已晚,也累的实在没了力气。拖着一身的寒气,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惦念已久的西湖。
本以为只这一次了,心里还有些惋惜,没能看遍西湖的全貌。只是没想到,在那之后,因为各种会议又连着去了五次,直到听到西湖二字,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六次当中,有五次在下雨,同事们笑称我为“雨的使者”。
从杭州回来不久,科室因为人手不够,临时调我回到病房独自管病人。
吓!主任还真放心我!虽然床位不多,让我独自来管理,这个,这个,我能行么?我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把担忧和主任说了,谁知主任笑眯眯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同志,你没问题的,好好干,我们看好你呦!”
彦锐听说之后,也在电话里鼓励我,“丫头,你行的,相信自己,我也看好你呦!”
既然这么被看好,还有啥犹豫的,那就上吧!阿米尔,冲!!!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0)
第一次带着学生查房,心里很忐忑。查房的时候表情很僵硬,连手都在抖。除了问“您今天觉得怎么样?”之外,不知道还该问点啥。倒是患者对着我跟连珠炮似的问了一堆的问题,整的我有些招架不住。尤其是本地患者的方言,不分节奏的噼里啪啦汹涌而来,我听得脑仁儿都疼。虾米和虾米嘛,一句听不懂!
查了一圈房回来,大呼了一口气,心情特沮丧。处理医嘱,给患者换药,打电话叫会诊,接叫会诊的电话,间或护士来电话提醒医嘱开迟了,哪些药缺货了,一会又是家属来了解病情,又是患者咨询费用。。。。。。我像陀螺一样,转呀转呀,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
忙忙活活的过了一天,觉得这一天说的话快赶上平时一周说的话。回家把自己扔在床上,一动不想动。睁着眼睛盯了好半天天花板,突然想起明天主任要查房。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主任历来以严格出名,明天不知会问到什么问题,万一在患者和学生面前答不出来,那我这张老脸就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放松的神经又绷了起来,不情愿的爬起来,翻出专业书认真的看。看了一会,胃开始丝丝的疼。老毛病又犯了,每当紧张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胃病就会跟着添乱。胡乱找了几颗胃药吞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盖好盖子,抱在怀里贴近胃的地方。
这么一折腾,也没心情看书了。打开电脑,看到彦锐在线。和他聊了一会,告诉他我的胃病又犯了。彦锐知道我有这个老毛病,急忙催我去床上躺着,都这样了,还上什么网啊。
胃也确实疼的厉害,刚刚吃的药不知是不见效还是没到起效的时候,疼的人直不起腰来。于是乖乖的听彦锐的话,关了电脑,躺在床上。给自己灌了个热水袋,抱在怀里,盖上小被子,可怜兮兮的盯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月光柔柔的撒在身上,伴着清风轻拂着我的面庞,好像妈妈的手在轻抚我的额头。不知不觉,泪水打湿了枕巾,又想妈妈了。是不是人在生病的时候,都特别想念妈妈?
不知什么时候睡过了过去,第二天查房,胃疼好了些,但还是不太舒服,一路捂着肚子皱着眉头跟随主任去查房。主任历来细心,见我一副痛苦的模样,问我是不是不舒服。知道我胃疼之后,随手从白大衣兜里掏出两片达喜片,让我嚼了吃。主任自己也常常胃痛,所以都会随身带着药。
心里感动的跟什么似的,连声谢了主任,接过药片揣进大衣口袋里。主任见我没有马上吃,于是冲我做了一个吃药的动作,我笑了笑,只好打开包装,扔了一片药片到嘴里。
我的亲娘啊,这是什么味儿啊?!这药也忒味儿了吧!比胃疼的滋味还难受!
趁着主任正在给学生分析病情,我偷偷溜开,跑到办公室,吐了出来,又喝了一大口水漱了漱口。心里想,主任呀,您的心意我是领了,只是,小同志我实在受不了这味儿。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1)
很多人说我对患者太好了,好到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好到为了患者而常常得罪护士。初初到病房工作,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和护士闹的很不愉快。护士长为此事,几次三番提醒我,不能只听患者的一面之词,有时候我的态度也影响她们工作的开展。比如,患者有时候会向我抱怨,该给的药没发给他,而实际上是药房断货了,或者是领药领迟了;患者和我抱怨,护士没有按时给他抽血化验,而事实上是那一天休息,全院都不做类似的化验,只作急诊化验。。。。。。如此等等,我最初的时候只是听患者的一面之词,继而去质问护士,为此科室的大小护士背后对我颇有微词。
一个主管医生如果和护士配合不好,那是顶麻烦的一件事情。虽然说大家各做各的工作,但总是会有些事情需要协作。我向科室高年资的医生请教相处之道,也暗中向其他科室的医生学习,发现大家在工作中都和护士们相处的很融洽,从主任到住院医,说说笑笑,彼此合作愉快。
通过观察和学习,我发现自己以前有多么愚蠢。一个好医生,不单单是会关心患者会解决病痛,也应该擅长处理医患及同事之间的关系。嘴巴甜一些,遇事多想一些,手脚麻利一些,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些,没什么事是化解不了的。
从那之后,在临床工作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再犯武断的毛病。有了意见分歧,遇到抱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患者理解护士工作的辛苦,调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在病房待了一个月,让我迅速成长。一个人很苦也很累,却也有快乐有满足。每当患者握住你的手连连感谢,每当值班时家属送来一句关心的话语,每当患者亲切的叫我“程医师”,每当送走一批批康复出院的患者,那种满足和欣慰是无法言语的。
我常将病房的主管医师比作“管家”,“家”管的好不好,从身边人对他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怕和敬,是两个概念。让人怕和让人敬,更是两种境界。想来,这和打仗带兵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虽小医师,但在这一份热爱的工作中,能得到认同、理解和称赞,足矣。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2)
十月的东北,夜凉如水,我站在空旷的机场出口,打了一个寒颤。
此次回乡,专为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事。母亲去世多年,骨灰一直寄存在火葬场。老一辈讲究入土为安,母亲生前拉着我的手交代,将来有那一天,要将她埋在向阳的山坡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能完成母亲的夙愿,心里惭愧不已。一来,当时尚在求学,未能独立;二来,家徒四壁,生活潦倒。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年了,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诺言。
一片薄云遮住了月色,夜色变得更加朦胧。南城还在过夏天,长春已隐约有了秋意。我紧了紧肥大的外衣,伸着脖子在人群中寻找彦锐的身影。彦锐说好要来接我,等了半天,却见不着人影儿,不知是不是有事耽误了。正琢磨着,手机叮咚响,收到彦锐的短信,“出门,我在停车场。”
刚走出门,一阵风吹来,冷不丁的打了一个寒颤。迷茫的望着停车场,一片漆黑,除了车还是车,哪有人的影子。正踌躇间,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顺着声音望去,隔着好远,一辆车的车灯亮起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车前冲我招手。不是彦锐,还能是谁呢?
我提着行李奔向他,走到他跟前已经是气喘吁吁。彦锐机灵的接过我手里的行李,回身放进后备箱里,回头冲我坏笑,“呵~嗯,胖了,丫头。”
这世上也许再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彦锐那些象声词的意义,同样的字,同样的发音,不同的语调甚至间歇,都代表着他不同的情绪,甚至能以此判断出他那时的想法。这一声久违的“呵~嗯”,有些许的调皮,些许的调侃,还有一丝丝的亲密。
我了解彦锐,甚于了解自己。
不好意思的裹紧外套,腰上的游泳圈清晰的显露出来。我一甩马尾,不理他,径直开了车门,稳稳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彦锐见我没搭腔,低头笑了笑,也钻进车子里,发动油门,回过身倒车。
“哎,我真胖了么?”隔了一会,我绷不住了,转过头问彦锐。彦锐一边开车,一边说,“嗯,是胖了些,不过还好。我也胖了,你没看出来么,双下巴都出来了,呵呵。”我借着路灯认真的看了看彦锐的脸,果真如此。下巴上青青的胡茬掩不住他有些圆润的下巴,和多出来的一层褶。
“你说,我们是不是都老了?”我落寞的问彦锐。
“别提老,提老我伤心,好歹你还小我五岁呢。”彦锐调侃道。
当彦锐熟悉的气息再次环绕着我,我多日来罩在心头的阴云终于暂时散开了。在南城的时候,由于工作上遇到一些烦心事,连着些日子,心里阴云密布,整个人很抑郁。直到那一刻坐在彦锐的身边,久违的熟悉感让我放松下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读书的日子。
(193)
彦锐依旧带我回到姐姐家,回去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了,我们俩蹑手蹑脚的进了家门,径直走向客厅。厅里一张小床,还有一张沙发。彦锐轻声说,“你睡床,我睡沙发。”我在黑暗中摇头,“不,你睡床。”说着,扭着彦锐的胳膊,把他推向门旁的小床。
彦锐无奈的笑了笑,没再推辞。他知道我的脾气,知道和我争下去也是无用。于是,掀开小床上的被子,和衣而睡。我见彦锐躺下了,自己才歪进沙发里,盖上彦锐给我的小被子,阖上眼睛休息。客厅里的老式钟“滴滴答答”不紧不慢的走着,像一首催眠曲。可我却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倒是一会的功夫,耳边传来彦锐轻微的鼾声。黑暗中,我不觉莞尔,暗自想,这哥们,累坏了吧。
心里胡乱想了一会,不知什么时候也睡了过去。历来不翻身睡不着觉的我,这次竟然老老实实的一个姿势从头到尾,我怕翻身吵醒彦锐。
天快亮的时候,彦锐叫醒了我。为了不打扰姐姐一家,我们俩又悄无声息的溜出了门,出去吃了早餐,彦锐把我送到车站,掏出提前替我买的回家的客车票。“今天上午我有个案子要开庭,就不送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发短信告诉我,我去接你。”彦锐的一双眼布满了红血丝,我仰着头看着他因休息不好有些憔悴的脸,心里又是内疚又是心疼。
“放心吧,你开庭后回去好好休息,昨晚害的你没休息好。”说着自然而然的帮他平了平有些卷的衣领,下意识中的动作,根本没经过大脑考虑。
彦锐有些不自然,不好意思的也自己整了整衣服。“时间不早了,快上车吧。到了家给我发短信,省得我惦念。”彦锐挥挥手,递过手里的行李给我。
“好。”我接过他手里的行李,转身下了楼梯。楼梯拐弯处,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却只看到彦锐刚刚转过去的背影,心里没来由的疼了一下。来不及多想,就被身后的人群推搡着继续向前走。
坐在回家的客车上,望着窗外熟悉的车站,心里很不是滋味。每次都是短暂的相遇,随即又分开。如果当初不是那么倔强,如果当初再努力努力,会不会今天会是另一番情形?
客车缓缓的发动,车载广播里放出熟悉的音乐,林俊杰的那首久违的《江南》在耳边轻轻吟唱。想起几年前,也是听着MP3里的这首歌回家,听了一路,也想了彦锐一路。
正靠着车窗发呆,收到彦锐的短信,“回去好好葬好妈妈,有什么困难和我说,我能帮的一定帮,别自己扛。”一句话说的我泪如雨下,哥们啊,干嘛总要对我那么好呢?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4)
回到老家,在亲戚们的帮忙下,把母亲的骨灰安放进祖上的坟地里。下葬的时候,按照祖辈规矩,女人们是不能参加的。于是我只能和女性亲属站在玉米地里,等着仪式结束。鞭炮声中,仪式终于结束。我被通知可以去磕头了,于是一脚深一脚浅的踩着土坷垃一点点靠近。
新坟就立在面前,黑土白碑,坟尖上一块红砖下压着一摞纸钱,在太阳下反着灼眼的光。墓碑上母亲的名字映入眼帘,我的眼泪止不住噼里啪啦的掉下来。跪在墓前,满怀思念,满腹心酸,深深的,深深的磕下三个头。心中默念道,“妈,安息吧。”
安葬好母亲,我在乡下的一家饭馆里宴请这次帮忙的亲属,以示答谢。席间,大家感慨良多。三叔不无惋惜的说,“唉,这要是大嫂还活着,看见咱们草儿现在这样出息,不知该有多高兴。。。。。。”父亲听见了,暗自抹眼泪。三叔的一句话,说的大家无限感慨,一时间席上的气氛很悲伤。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也差点掉下来,但还是忍住了。吸了吸鼻子,举起酒杯向各位长辈敬酒,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父女的帮忙和照顾。这些年来,如果不是有这些亲戚的扶持和关照,我们父女俩会过的很艰辛。
回来一次不易,故此这次回乡向主任多请了几天假,在家陪陪老父。
老家的十月,天气有些转凉。我从小体质差,和妈妈一样怕冷,所以老爸早早的把土炕烧的暖暖的,让我能舒服的趴在热炕上烙肚皮。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老爸注视着我的慈爱眼神。爸舍不得叫我起床,常常是早餐热了又热,等着我醒来一起吃。
年纪大的人通常觉少,每天天不亮,爸就起床了,披着衣服站在院子里抽烟。我有一次熟睡中听见爸推门的声音,朦胧晨光中,透过窗子看见爸站在院子里,烟雾缭绕下,佝偻的身影显得愈发的孤单。
我劝爸,该找个伴儿了。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又常年不在家,他实在太孤单了。我知道孤独的滋味,一个人一栋房,一天没有一句话,冷了没人关心在乎,病了没人嘘寒问暖,那滋味真的不好过。爸辛苦了一辈子,晚年不该如此孤单。
爸不说话,只是默默的抽烟。良久,对我说,“你妈,是个好女人。”
我不知该如何评判爸和妈这一生。
我看着他们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因为疾病,因为贫穷,还有那些家家都有的鸡毛蒜皮的事。也曾闹过离婚,也曾彼此冷战,也曾吵的脸红脖子粗,但最后还是一路扶持着走到了最后。
想起西方婚礼上那段经典的誓词,“爱她、忠于她,无论她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传统而含蓄的中国人,虽没有西方人的浪漫宣言,却能将这句话的真谛切切实实的实现在平常生活中,而爸和妈就是最好的例子。自我记事起,妈就在吃药,身体就是病怏怏的,爸和妈虽然经常磕磕绊绊,但从没说过要离开妈的话。
爱,真的可以永不止息。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见了。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5)
彦锐的办公室。
我小心翼翼的打开皮箱,露出包了一层又一层的花苗,一棵绿牡丹的嫩芽。
彦锐素来喜欢花花草草,办公室里的花总能被他养的枝繁叶茂。这次回来,聊天中无意中说起养花,我答应送彦锐一盆家里的绿牡丹。彦锐接过我手里的一柸黑土包裹的嫩芽,小心翼翼的放进花盆里。
“来年回来,就能看见它长成一大盆了。这种花生命力极其旺盛,繁殖很快,也好养活。”我一边帮忙松土,一边欢快的说。
忙活完之后,洗干净了手,彦锐倒了一杯茶给我,两人坐下来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说到兴起,彦锐又提起多年前他曾向我极力推荐的一名网络作家,兴奋的说,那作家最近又出了新书,让我务必回去要看看。我点了点头,彦锐推荐的书是一定要看的,能让他如此推崇的作家不多。不由想起那一年我们俩同时追读连载小说,彼此交流心得的岁月。
我逗彦锐,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在网上考他诗词的那档事。彦锐笑,说我当年古灵精怪,聊什么不好,非整什么劳什子的唐诗宋词。也亏得当年记忆力还不错,搁现在可没那精神头了。
正聊的开心,彦锐的一个同事敲门进来,向彦锐咨询事情。我站起身,踱步走到他的书柜前。隔着一尘不染的玻璃门,一眼瞥见当年送给彦锐的《考研英语单词背诵》和《医学解剖图谱》,立在书架最显眼处,当年我亲手包的书皮依然光艳如新。回头偷看了一眼彦锐,见他和同事凑在电脑前不知说些什么专业名词,正讨论的欢。
这些年来,和彦锐之间的感情,忽而亲密忽而疏远,但一直彼此关心彼此照顾。那些年少时的爱恋和倾心,还有他给予我的回应和关怀,时不时的会钻出来,在脑海中停留片刻。但很多时候,总觉得那是一场绚丽而美妙的梦,似真似幻,仿佛那一切仅仅发生在我的梦中,从未真实存在过。
轻轻抽出那本解剖图谱,放在手里翻开扉页,当年读书时留下的稚嫩的笔迹还清晰可见。这一切都提醒着我,那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我的痴狂和爱恋,我的纠结与痛苦,还有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纷繁,都曾真实的存在过。
正抚着书页发呆,彦锐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一下从我手里抽走图谱。我惊了一下,瞬间从回忆中走出来。彦锐低头一边翻着那本图谱,一边问我,“呵,你送我的。”
“我记得。”我转过身,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彦锐和我对视了一会,突然不着痕迹的和我拉开距离。走到电脑前,告诉我最近加入了老同学的qq群。当年那班老同学们,都已经是孩儿他爸他妈。大伙儿常问他,孩子几岁了,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自我调侃,“孩儿他妈还不知道在哪儿藏着呢,哥们我现在逍遥着呢。”
我正想糗他几句,彦锐又告诉我,他的初恋女友要结婚了。“你说,我该随礼么?”
我问他,“你还介意当年她离开你么?”
彦锐摇摇头,“早不介意了。”
“那你们还是朋友么?”我又问。
“嗯,是”
“那不就结了,既然是朋友,就给她祝福。朋友结婚随个份子,很正常的事啊。”
“呵呵,你说的对。”彦锐想了一会,轻松的笑。
聊了一会,时间不早,彦锐送我去机场。一直把我送进安检,他才转身离去。
我拖着行李缓缓走在候机厅长长的过道里,心里无限感慨。一年又一年,聚了又别,别了又聚。而下一次相聚,不知又是何时?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196)
十月底,东北下了第一场雪,而我还在南城与炎炎夏日做着抗争。到了十一月中旬,天气转凉,淅淅沥沥的小雨连绵不绝的下了十多天。
我的身材依然肥硕,甚至和夏天相比,更甚之。天冷了,懒得出家门,每天下了班一头扎进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冷了,肚子似乎也成了无底洞。仿佛有万丈深渊等着我去填,从前不感兴趣的小食品也变得如此美味。叫外卖成了家常便饭,春天时买来的锅碗瓢盆再无用武之地,连菜刀都生了锈。
那是一段极其颓废极其堕落也极其抑郁的日子。
由于在其他科室轮转,身边的人都不是很熟,工作量也不是很大,每天浑浑噩噩,做好了自己的分内工作后,就望着窗外发呆,一天里很少能说上几句话。
同一组里有个辅助科室来轮转的医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见我每天闷闷不乐,建议我去信基督教。我委婉的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这姐姐似乎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一有时间就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基督耶稣有多么多么好。一次,科室里一个病人床头拍片,医生护士们都躲在楼梯道里闲聊。这姐姐又向我劝说,我被逼急了,只好撒了个谎,说自己是个佛教教徒。这一招很灵,从此之后,基督姐姐再也不对我进行狂轰乱炸,而我的耳根子也终于清净了下来。
世界终于安静了,但对于我而言,又有些过于安静了。
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忽然间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快乐弄丢了。
夜里,常常漫无目的的在网上乱逛。或者,翻来覆去看很老很老的港台和大陆的电视剧。偶尔,去天涯上翻看一些连载的小说。有一天,无意中在一个帖子里见作者提到一种聊天工具,新浪UC。我很好奇,于是下载了安装在自己的电脑里。
这是一个类似于qq聊天室的地方,只不过里面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些甚至不敢恭维。我常去一个叫做“北京之巅”的聊天室,我希望,北京人的贫嘴能为我带来些许快乐。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一旁看热闹。偶尔有人搭讪,也不搭理。后来有一次,看见公屏上有两个人在争论一个医学常识,对于我这个专业人士来说,他们争的内容特可笑,于是禁不住和其中一个人攀谈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被视为精英的那种。嘴茬子相当厉害,说话一套套的。
最开始和他聊,总是在辩论,彼此互不相让。他贫,我比他还贫。他不按常理出牌,我比他还古灵精怪。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了一段日子,突然有一天,精英说,他爱上我了,要和我见面。
这祸闯大了。我早过了玩网恋的年纪,而且,一次,已经遍体鳞伤,发誓再不玩这种另类的爱情游戏。
我磨破了嘴皮,精英还是不折不挠,向我充分的展示了他死缠烂打的精神。被他缠的没办法,只好想了一折,骗他说自己已经是两个娃儿的妈。出乎意料之外,精英很快回我,“我也有妻有子,儿子已经五岁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爱你。”
奶奶个球的,整半天不是网恋是婚外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啊,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气急败坏的从这个怪异的圈里连滚带爬的退出来,并且删了程序,注销了账号,发誓从此再不涉足那个颓废的世界。
我的世界,再一次安静下来。而抑郁,也再一次不请自来。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突然有一天,彦锐从qq上发来一个网址,让我去下载一个游戏。
我惊讶,问彦锐不是中毒了吧,整个什么玩意儿发过来。彦锐说,没影儿的事,不是病毒,去看看,下载下来,帮我玩个游戏。
带着满心的好奇打开那个网页,原来是网络游戏《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各个版本我都看过,而且看过不止一次,书也看过很多遍,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几乎烂熟于心。但游戏,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这事从玩游戏上就可见一斑。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大游戏,在别人看来如此简单,对我来说,却如难如登天。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玩的来的只有那版最原始的连连看。
网络游戏?这已经远远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我问彦锐,“哥们,你是不是太过高估我的水平了?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游戏白痴,你就不怕我把你在游戏里那点家当都败光了?”
“甭担心,有我呢。”彦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拍着胸脯向我打包票,“赚了算你的,亏了算我的,嘿嘿~~”
好吧,正好本小姐闷的发慌,玩就玩吧,谁怕谁?我还真不信了,本姑娘一堂堂名牌大学研究生,连个网络游戏都整不明白,这书还真是读到太平洋去了。
好家伙,这游戏还挺占地儿。全下载下来费了一个钟头,一个盘的空间都被占满了。笨手笨脚的安装上了,电脑变得奇慢。
彦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游心”,很适合他。然后告诉我密码,让我用他的账号登陆,他则用一个同事的账号登陆。一点点教我如何操作,如果赚分等。
这个虚拟的世界很新奇,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眼球。它既陌生又熟悉,当看到那些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出现在视线里时,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更奇妙的是,可以操纵着自己鼠标下的那个小人儿,去和那些大人物并肩作战甚至激烈火拼。
彦锐的游心,在游戏世界里是个威武的大侠,明教弟子。当我第一次用鼠标操纵着这个长相俊俏却一身肌肉的大侠时,心里乐开了花。彦锐教我让他如何蹦如何跳,如何跑步如何耍大刀,甚至如何打出各种套路的拳法。我却偏偏要另辟蹊径,非让大侠打哈欠吹口哨一会蹲下去抱拳一会倒地装死。彦锐直呼“丫头,别闹”,却拿我没办法。直到我玩够了,才一本正经的教我其他的规则。
彦锐让我有空的时候多上去做做任务,通过任务升级,获取法宝,然后卖钱。我傻呵呵的问他,“有了钱干嘛?”
“有了钱可以买装备,买坐骑,买法宝,反正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彦锐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那有了这些有啥用?”我锲而不舍。
“有了这些,可以提升装备,做任务的时候更容易,级别高了,机会就越多,也越强大。”彦锐孜孜不倦的教诲。
“强大了之后又怎样?”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强大了之后,你就可以呼风唤雨,想欺负谁欺负谁!”彦锐在qq上发过来一排坏笑。
“哈,这个我喜欢!”现实世界里受欺负,却无处发泄。而虚拟世界里可以欺负人,只要你足够强大!这个世界,我简直太喜欢了!
好吧,姐们从今天开始要做回大侠!大刀,向小鬼们的头上砍去!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冯小刚曾写过一本书献给爱妻徐帆,叫做《我把青春献给你》。套用冯导的书名,“我把黑夜献给它!”它是谁?我想,你懂的。
白天依旧是浑浑噩噩,如同行尸走肉。到了夜晚却是两眼放光,精神抖擞。白天不懂夜的黑?nonono,不如说白天不懂夜的美。
我自由自在的在虚拟世界里徜徉,并且一天天的壮大。最初的时候,我只按照彦锐的交代,每天上去按时完成门派任务。做好了之后,就去差不多的场景杀几个妖怪,拣些宝贝,然后屁颠屁颠的拿到当铺去换钱。
我带着一杆破旧长枪,在游戏里疯狂发泄。只要鼠标轻轻点几下,招起招落间,级别小的妖怪瞬间一命呜呼,溅出几滴鲜血和一声惨叫。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让人禁不住热血沸腾。我有时候会禁不住怀疑,人类是不是天生嗜血?还是我骨子里,本就有暴力倾向,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显露出来?
拣东西拣到手软,多的时候根本塞不下随身携带的行囊。只能打一会跑回城市里,在当铺换些钱,存进仓库里,然后再跑出来打杀。一个晚上来来回回的跑,忙的不亦乐乎。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坐骑,穷啊,只能靠两条腿儿倒蹬,平均跑一次要两三分钟,但还是乐此不疲。
彦锐知道后,从我们的钱庄里取出些积蓄,买了一个大一些的行囊,“丫头,给你换个大点的带着,省的老跑来跑去。”彦锐又说,等咱攒够了钱,就去买个坐骑,省得老自己跑来跑去,一点不拉风。彦锐这话,听得人心里嘎温暖。
我在游戏世界里找回了从前的彦锐,这里的彦锐亦师亦友,亦兄亦父,无论任何时候都罩着我,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一点伤害。那种久违的关心和疼爱,让人又窝心又感动。虚幻世界里,我们为着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谋划,甚至彼此帮助,配合得亲密无间,这种感觉很棒。游戏将我们紧紧的栓在一起,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多年前我刚刚认识彦锐的那段日子。
不能否认,我喜欢这个游戏,它带给我活力,驱赶走抑郁。但我更喜欢的,却是有彦锐陪伴的日子。这种感觉,让我着迷。它让我和彦锐有了更多的话题和共同点,我们聊天的频率也渐渐频繁。他不再躲躲闪闪,我也不再犹疑猜测,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尽管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讨论游戏。
我沉浸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乐不思蜀。恨不能化身为其中的人物,不用烦恼现实如何。
华灯初上。
我已经在这个武侠世界里杀了上百只妖怪,“吼喝”声充斥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换好衣服,登陆进游戏,就在电脑前如老僧一般入了定。
我这边刚登陆,彦锐的qq头像蹦了出来。“丫头,你是不是在用游心?”
“啊,刚登上。”我嘴里含着一瓣橘子,快速回应着彦锐。
“呵呵,我就说嘛,怎么玩的好好的,突然被迫下线。”
“呀,我不知道你在上面,那我退出来你玩吧。”我急忙解释。
“别啊!我用同事的账号进去,你继续。你到太湖去,我去那里找你,咱俩一起杀怪。”
彦锐同事的账号是个女侠,名字挺个性,叫“惊艳一妖”。我常常背地里叫她“妖女”,“惊艳”这两字确实名至实归。星宿派出身,身形凸凹有致。头扎两个圆形小髻,上飘两条红色丝带,有些像最早的《街霸》游戏中的中国妞。一身紫色劲装,手持双花大斧,身手干净利索。杏眼,桃面,樱桃口,走起路来风姿卓越,小蛮腰扭啊扭的,令人神魂颠倒。我常常跟在这小蛮腰身后,盯着她的背影一路狂奔。一边跑一边不忘调戏彦锐,“嗨,妞儿,你长得真俊,给爷笑一个!”
游戏里,我是大侠彦锐是女侠,这种反差让游戏变得更有戏剧化。妖女的级别要高一些,于是游心和妖女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这个看似弱不禁风实则心狠手辣的女子来保护我这个大侠。游心就是一跟屁虫,妖女去哪儿他去哪儿,负责在关键时候来些猛烈的招数炸倒一批小妖。
彦锐或者该称他为妖女,惯用的招数是每到一个场子,就扭着小腰飞快地四处晃荡一圈,惹了一群妖怪跟随而至,再回到我的身旁,然后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如果妖怪很多,妖女就会大喊,“快用大招!”然后我就会使出我最擅长的那一招,将身边的小妖炸的七零八落。这一招,我们百试百灵,配合的亲密无间。
有时候妖女也会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逛荡一圈之后发现惹的妖怪多了,结果我们俩一起被大小妖怪群殴。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不说,还常常被削进阴曹地府,身上那点银子被孟婆那婆娘搜刮去不少,才得以重返城市。
每一次我灰头土脸从地府里爬出来之后,都会咬牙切齿的对妖女说,“你 丫下回不能少招惹点?老子被你害惨了!”
彦锐一脸媚笑,“丫头,你不但打妖怪打得猛,说话也越来越猛了。我有点怀疑,你是女人么?”
“去去去,老娘在游戏里就是爷!不服咱单挑!”说完,自己扑哧一声笑了。
完鸟完鸟,这回真成女爷们鸟!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升到一定的级别,彦锐开始拉着我去和别人组队进入大的场景杀怪。最初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跟着彦锐身后瞎转悠。他说,“削他丫的!”,俺立马冲上去一顿狂踢乱打;他喊,“快跑!”,俺马上抱住头撒开丫子往出奔。说白了,他就是我的指挥官,他指哪儿我打哪儿,绝对服从命令。
我和彦锐存了一小笔钱,彦锐用它买了一只大雕来骑。虽然说这大雕只会扇乎着翅膀蹦着走,但从行进速度上来讲,好歹比我这两条小短腿来回倒腾得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能更好的杀敌,彦锐又给我换了一套装备,把原来那杆破枪拿去当铺换了几个大钱,然后重新买了一杆拉风的长枪。最初的时候,我还有些舍不得,使那个有感情了,咋能说扔就扔了。彦锐笑我小农意识,教育我道,“傻妞儿,武器好了,才能更好的打仗啊!”我想了想,连声称是。
后来,有段日子彦锐特忙,顾不上玩游戏。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瞎转悠,打些零散的小怪,打的无聊透顶,也没什么挑战性,于是心里痒痒的去那城外聚集处转悠。由于级别还算不赖,常常被人招募到队伍里,一来二去,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每次相约一起行动。
在武侠世界里,有一个门派很特别,这就是峨眉派。爱看武侠的兄弟们都知道,这个派别里都是美女,个顶个都长的跟仙女似的。在这个游戏里,峨眉派的仙女们除了长得好看武功也不错之外,还有一本事,就是能给人加血甚至让人起死回生。这是个什么概念,在现实世界里那就是医生啊,甚至比医生还高级,她们能把死人鼓弄活了,谁有她们牛叉?
拥有这样神奇本事的门派,注定是吃香的。组队的时候,谁都知道,宁可少个武夫,也不能少个医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也关乎全队人马的战斗力。和一群哥们打大boss的时候,总有人一边打一边叫唤,“峨眉,加血!!”“峨眉,快点!”每当看到峨眉小妹娇喝一声,扬起春葱一般的小手轻轻一挥,就立刻让身边的人充满力量时,我那个羡慕呦。
我这个现实世界里的正牌医生,怎么就没想到在游戏里回归老本行呢?救死扶伤乃医之职责,甭管在现实中还是游戏里,只要群众需要,那俺是责无旁贷啊。
其实私下里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我曾听彦锐提起,这游戏里,要讲最厉害的那就是峨眉,而且到了一定级别之后,坐骑都是凤凰,能在天上灰来灰去的那种。明教弟子再厉害,也只能骑着狮子在地上耀武扬威,但怎么也窜不到天上去。
我闭上眼睛,幻想着自己身穿白衣,骑着五彩凤凰,无比仙女的在天上灰来灰去。哈,那一定美呆了!
游心这个大侠就留给彦锐玩吧,本小姐暂时回归,尝试一把做仙女的滋味去!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201)
摇身一变,我成了峨眉女侠,芳名“明瞳”。
没错,明亮的“明”,双瞳的“瞳”,明瞳。游戏里的坏小子们常常问我,美女是不是有双漂亮的大眼睛?我说是啊,我还有根长舌头呢,百发百中,不然怎么捉你们这些害虫?
我找出那一年临别时,彦锐送给我的红色胶皮印章,放在手心里来回端详。默默的想,既然把它送给了我,那这名字也一同送与我吧。
没人知道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地位,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我用这名字,彦锐没有表示任何惊讶或者异议,很自然的接受了。既然如此,索性一同将qq的名字也改成了“明瞳”,甚至很多论坛里也用这个名字来注册。我对它着了魔,一如我当年对彦锐的迷恋。又或者,这迷恋从不曾终止过。
终于恢复了女儿身,初初之时,还有些不适应。眉目清秀,兰质蕙心,藕裙款款,莲步轻摇。长枪换成了碧剑,马靴成了绣花鞋。一举一动,十足的淑女范儿。站在峨眉山脚,梅花树下,仿佛闻到梅花的清香。游戏内外,哪一个是真的我,程昱和明瞳,也不知,到底是谁在操纵谁?
明瞳在这个世界里还仅仅是一张白纸,弱小的还不如一只蚂蚁。为了能短时间内迅速壮大,我不惜在她身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时候午休的时间也要上来做一会任务。我把明瞳当成了自己,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也许,心底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期望,希望有一天,在这个武侠世界里,能和游心一起并肩而行,双宿双飞。
玩的猛了,也会吐血。有些任务,怎么也完不成的时候,就去找彦锐撒娇,让他帮我。彦锐玩这个比我在行,总能三下五除二的帮我解决难题。当我用游心的身份,懒洋洋的站在一旁看着彦锐再一次拧着小腰跑来跑去的时候,内心无比欢畅!在虚拟的世界里,我再也不用伪装成大女人事事亲力亲为,而是得心应手的用撒娇耍赖及软磨硬泡等小女人惯用的伎俩来达成我的目的,并且,从头到尾,我都十分享受这一过程。
“征服世界?留给男人去做吧。女人,只要征服男人就够了。”想起女性杂志上的一句话,我不觉莞尔。这话看上去俗,道理却一点都不俗。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无论横着看竖着看,都极其精辟。
而我,完全没有野心去征服什么世界,只一心盼望着守着游戏里抑或游戏外的那个男人,做一回柔情似水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 观镜下世界,几癫几陶然; 赏粉蓝画卷,几醉几成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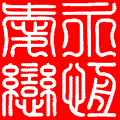




 妹妹越写越精彩,越来越厉害
妹妹越写越精彩,越来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