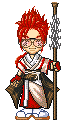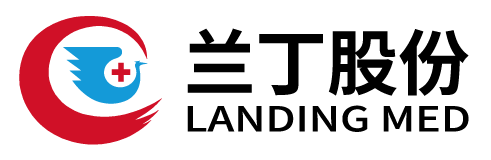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A History of Pathology

最近,我的一位老师沈士亮教授读到了一本1928年版、美国人Esmond R Long主编的病理学史著作!
在进入分子病理时代的当下,其实,读一读这样的著作、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专业的历史,很有必要!
因此,沈教授和他的助手将该书翻译了出来!
我有幸拜读了!
经沈教授同意,我来发在网站,和大家共享!
(因为沈教授工作繁忙,所以译文分别进行发送,请大家耐心等待……)
译者简介
邱晶: 201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4年取得英国邓迪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三年医学专业翻译经验。2014年5月任康圣环球医学特检集团病理部助理。
沈士亮: 毕业于皖南医学院,1982-1988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获得病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89年至90年代初分别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的Loyola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做博士后,从事肾超微病理诊断和研究工作;1994-2010年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遗传学和病理学系从事中枢神经元损伤后再生、中枢神经变性疾病发病机理的研究;2011年-201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Brigham Women’s医院内科病理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4月起担任中国康圣环球医学特检集团病理部总监。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09-30 08:59:43 编辑
第一章 古代的病理学
疾病指的是机体失去了正常的健康状态,病理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努力去理解疾病本质的一门学科。第一位病理学家就是最早脱离蒙昧、尽力寻找自身疾病原因的人。随着人类的群居生活和劳动力的自然分工,一种专门探究疾病成因及可能治疗方法的职业逐渐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些专家从有历史记载时即已出现,而当今我们仍然可通过原始民族部落的生活情况观察到他们早期的面貌。
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史前民族对体表疾病大体特征的观察记录。在古代,医术与神学活动密切相关,病人朝拜神庙以求消除病痛;如果祷告之后他们身体康复,或自以为康复,他们常在祠庙中留下描绘疾病部位的小型人体雕刻或模塑,以示他们对天赐恩惠铭感于心。因此,表现疝气、乳腺肿瘤、腹水、肥胖、静脉曲张、皮肤溃疡以及其他外伤的精致大理石与陶土模型被保留了下来,见证了远古时代人类对解剖学的认知和观点。
古埃及医学科学由两类受过教育的人主导,分别是医学僧侣和专业医师。僧侣学习炼金术,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引领医学思想的发展。在古埃及,早期僧侣医学对疾病的解释带有鬼神论的色彩,驱逐魔鬼是医学活动最重要的程序之一,这点在希伯来人的文字中多有记载, 当时希伯来人经常被埃及人抓捕而沦为奴隶,而他们从埃及人那里汲取了不少知识概念。
然而,古老的巫术纸草文中已存在疾病客观分析的痕迹,其中一部提到一种特定的病魔,将它形容为“血之兄弟、脓之同伴、恶性肿胀之父”。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人类早期对炎症某些特征的关注,自古到今的每一时期,炎症都是病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此外,由于疾病具有明显的好发部位,如眼炎、痢疾和多种皮肤病,因此人类必然将疾病与解剖结构关联起来。对于医学解剖学的发展,早期的埃及人显然比王朝后期的继承者们更具有开拓精神。根据史学家马涅托(Manetho,约前3世纪)的记载,早在公元前4000年,那时候还没有金字塔,埃及王朝开国大帝美尼斯(Menes,约前3100年)的儿子及继承人阿托悌斯(Athothis,约前3050年)就撰写了医学著作,第一次论及解剖学。而在文字记录能够保留的很久以前,已有一种传统的解剖学供埃及的医学生和僧侣学习,这一解剖学对人体结构的阐述表现出奇特的对称性,但凡涉及内部器官都不具实用价值,不准确程度可见一斑。血管系统及其异常受到最多的关注,古埃及人注意到了如今称为动脉瘤的疾病并对其进行了评论,医学文献也显示出对炎症部位充血现象的关注。而用系统解剖学的方法,即从头部及其功能障碍开始,系统化地向下进行分析,则是古埃及人对解剖学的不朽贡献。
古埃及医学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由德国籍的埃及学家埃伯斯(G. Ebers,1837-1893年)译解的埃伯斯医学纸草文(Papyrus Ebers,约前1550年),和更古老的史密斯外科纸草文 (Edwin Smith Papyrus)。史密斯纸草文是一部外科著作,记录了始自公元前17世纪的病例,由布雷斯特德教授(J. Breasted,1865-1935年)翻译。从这些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创伤性与自发性骨损伤,沙眼等现在还在尼罗河流域肆虐的眼疾,可能是癌症的溃烂性肿块,脂肪肿瘤,肠道寄生虫和痢疾,钩虫,截肢术,取石术,绷带包扎术,拔火罐,静脉切开术,包皮环切术和阉割,以及数量惊人的药物处方。这些药方正是“化学 (chemistry)”一词的来源,意为Chemi——古埃及黑土地上的神奇科学。
尽管如此,史密斯纸草文的十六英尺长卷、埃伯斯纸草文的一百一十栏象形文字,还有柏林及其他纸草文中关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片段,所有这些文献中包含的病理解剖学信息,对于埃及这个得天独厚的民族来说,仍甚显微薄。在阿拉伯人横扫尼罗河岸之前、埃及朝代更替的五千年间,有十亿带着人类可能罹患的各种疾病的人类尸体,约四分之三经过埃及敛尸官的检查,并对其中的大部分尸体进行解剖探查。由地位低下的“paraschites”对尸体进行初始切割,随之由受人尊重“taricheutes”摘除内脏,他们必定在这十分庄重的过程中观察、处理、封存或丢弃无数病变的心脏,萎缩、脓肿或患结核的肺脏,硬化的肝脏,肿大或萎缩的脾脏,受感染的肾脏和大肠,硬化的动脉和栓塞的静脉。如果从这五十个世纪单调、粗暴而简陋的解剖过程中获得病理知识,也一定是偶然的,因为流传至今的文字记录显然微乎其微。
当今解剖学家仍需提供有力证据,以证明公元前四十世纪的人体内部组织与现在的一样容易受到感染。艾略特史密斯 (Elliot Smith) 和马克鲁费尔 (Marc Ruffer) 对古埃及木乃伊的杰出研究,让我们知道那时候同样有骨肿瘤和脊椎结核,骨髓炎和关节畸形相当普遍,钙盐沉积型的老年人动脉粥样硬化发生频率至少与现在一样、可能更高;而法老和阿蒙神的祭司也难逃肺炎、矽肺病、胸膜炎、肾萎缩或脓肿、脾肿大和胆结石的折磨,甚至被它们夺去生命,病变组织的宏观和微观变化与二十世纪的人体并没有什么区别。
直到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的希腊人来到埃及和周围区域,尼罗河流域的文明才在解剖学和病理学上有了长足发展。诚然,远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约前370年)时期以前,希腊学生游历到孟菲斯 (Memphis) 和赫里奥波里斯 (Heliopolis) 并带回了许多医学知识,但这并不是希腊人后来所了解的病理学,亦不是我们今天所知晓的病理学。信奉多神论的希腊人对超自然现象持怀疑态度,高度推理性的埃及鬼神论病理学对他们并不具太多吸引力,而来源不明、可能源自东方的体液学说虽同样带有推测成分,但相对理性,最终为他们所取。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病理学的贡献比埃及更少。虽然《汉莫拉比法典》(约前2200年)和尼尼微(Nineveh,古亚述首都)的亚述巴比伦泥板文库(约前650年)提供了不少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医学及外科信息,但看得出这些民族甘心于将原因不明的疾病归咎于恶魔作祟。
古希伯来人对医学卫生学有独到贡献,在疾病的本质上则接受了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神学观念。公元二三世纪才完成的《塔木德》 (The Talmud) 吸收了已发展成熟的希腊科学的长处,其中关于浅表病理解剖结构的记录映射了希腊人的观点。《塔木德》甚至还包含了实验病理学领域的观察记录,如子宫和脾脏切除。对肉类仔细地管理使犹太人十分了解患病动物的病理状况,毫无疑问,这潜移默化发展出病理解剖学传统。
亚述人、巴比伦人、犹太人和埃及人无一例外被米提亚人和波斯人击败。而在伊斯兰统治时期对医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波斯人,其史前时代的医学却来源于外族。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76—前530年)和他的女婿——征服欧亚、从印度河打到多瑙河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58—前486年),都曾从埃及和希腊将医生招来波斯王朝。希罗多德(Herodotus,古希腊历史学家,约前484─前425年)甚至证明,克罗托那 (Crotona) 的迪莫塞迪斯(Democedes,古希腊医生,前520年),雅典一所医学院的建立者,曾经治好了大流士之妻、居鲁士之女阿托莎 (Atossa) 的乳腺癌。尽管这一叙述的准确性有待考证,此案例仍作为第一个有记录的肿瘤病理学病例而受到当今病理学家的关注。
波斯统治衰落之后,希腊文化迎来了繁盛时期,传统上记于科斯 (Cos) 的希波克拉底名下的著作即产生于此时。希波克拉底本人极可能是个虚构人物,但一直以来都被尊为“医学之父”。科斯医学院伟大作品的著作权存疑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必赘述。当代学术界逐渐倾向于将希波克拉底个人的“真实”作品与科恩 (Coan) 学派其他大量的医学著作分开,但遵照传统的规则,我们还是将全部作品纳入《希波克拉底文集》。
自希波克拉底学派始,医学逐渐与鬼神论分离,开始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世俗的祈愿者认为他们的病痛源于超自然的力量,因而将癌变乳房和曲张静脉的泥塑供奉于神坛。而希波克拉底学派则提出了疾病的发生机理概念,这套学说很快在整个医学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
(插图I 古希腊祈愿塑像(溃烂的乳腺肿瘤)。梅耶施泰因格教授 (Theodor Meyer-Steineg) 惠赠。)
这就是体液病理学。其古代理论基础的起源已无从知晓,但很可能经由巴比伦传入希腊。体液学说简而言之就是将疾病归因于身体内液体的异常,并以这种形式流传至今,现在的外行人仍倾向于将疖子看作血液清除内部杂质的一种反应。而这一学说的博大精深之处,即便是富于逻辑思维的当代史学家的综合分析,也难解释其奥妙之处。
科斯学院的体液病理学遵循同时代的其他领域的哲学范例,将体液分为四种,与希腊哲学的四元素——气、水、火、土,和四种性质——湿、冷、热、干,分别对应:血液温而湿对应于气,黏液冷而湿对应于水,黄胆汁温而干对应于火,黑胆汁冷而干对应于土。他们定义的四体液来源则与真实情况颇为接近:血液来自心脏,黏液来自大脑,黄胆汁来自肝脏,黑胆汁来自脾脏。
四体液按比例混合适当 (ευκρασία) 则为健康,否则 (δυσκρασία) 则发生疾病。例如,来自头部的黏液在任何部位积累过多都将导致疾病,在肺部则出现肺痨的典型症状,在腹部则发生腹水,在肠道发生痢疾,在直肠则为痔疮等等。“卡他”和遍布全身的黏液在希氏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古人相信黑胆汁携带的病魔最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希波克拉底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医学史命名为“黑胆汁 (atra bilis) 时期”。
疾病的性质由体液失调的类型决定,而后者又或多或少受环境与气候的影响。因此黏液失调常见于冬季,血液过剩多发于春季,黄胆汁异常见于夏季,而黑胆汁异常则在秋季比较普遍。这就是“时疫 (epidemics)”一词的来历,其本意指某种特定疾病在特定地点或时间的易发性,而不是现在所偏重的传染性。希氏认为,疾病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熟期又称煎煮期,这一时期体液温度上升;最后是危机转折期,多余或混合不当的体液自体内排出。
根据这一学说,以及希波克拉底学派坚信的身体自我痊愈倾向,疾病的某些症状,如发烧,代表身体正通过消化或加热异常体液来维系生命,而诸如咳嗽、呕吐、腹泻、出汗和溃疡等,则代表消化期产生的废液到了排出体外的紧要关头。如果身体不能完成消化或无法承受排泄期的风险,病人就可能死亡。
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恐怕很难理解这些,正如两千年之后的人们大概也会认为我们现在的医学和生理学的观点不可理喻。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病理学并不仅限于凭空揣测,当中也包含许多关于疾病过程的明确认知,作为医学实践的理性基础。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者对创伤、产后败血症、咽炎等疾病中的炎症反应进行了精确地描写,他们已经知悉患有化脓性感染的病人伴随着寒战和发热。可以肯定他们认为血液加热到一定程度腐烂而形成脓液。
他们对浅表器官的肿瘤相当熟悉,并提出了术语“καρκίνος”和“καρκίνομα”,前者 (carcinos) 指一种难愈的溃疡,甚至痔疮,后者 (carcinoma) 则表示恶性肿瘤。硬性肿瘤“σκίρρος”则与开放的恶性溃疡或肿瘤相区别,与我们如今所称的“硬癌 (scirrhus) ”含义几乎一致。《女性疾病》 (Diseases of Women) 一书中提到了宫颈癌硬化,以及一种并不形成溃疡的乳房肿块 (φυματα),后者可能指良性肿瘤。
古人所说的皮肤肿块 (phymata),早在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前719—前633年)时期即已提到,显然包括了脓疮、结节和现代意义上的肿瘤。由于该词在肺结核的描述中频繁出现,因此弗利克(L. Flick,美国医生,1856—1938)认为,希波克拉底学者在尸体上看到了结节并将之与肺病联系了起来。罗马人将这个词译为“结节 (tubercle)”。
从临床角度看,希氏对疟疾的陈述十分经典,对可能指伤寒热和流感的病症描写则不甚清晰,对腮腺炎描述得当。他们对肺炎有正确的认识,将其与胸膜炎进行了区分并因此被赞许有加,但事实上他们所描写的胸膜炎很可能正是肺炎。对于脓胸、脓液从肋部的自发渗出以及肺衰竭都描写很完善。
然而,希氏文献通常仅包含对病症和病人外部变化的描述,除前面提到的少数几条观察结果,他们基本没有进入到内部病理解剖的领域。首先,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希腊人对正常解剖结构知之甚少。伦瓦尔 (Renouard) 评论说(贡梅格尼 (Comiegny) 译):“将希氏文献中关于人体结构的片段拼凑起来,是无法写出一篇常规或完整的解剖学论文的,因为除了骨骼之外,他们对任何有机器官的认知都十分有限且漏洞百出。他们将神经、韧带和肌腱混为一谈,对动脉和静脉分辨不清,肌肉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堆用来覆盖骨头的惰性物体,就相当于封皮或装饰品。一言以蔽之,他们对大脑、心脏、肝脏、肺、消化和生殖器官的结构与功能都只有粗劣的认识,因为他们向来无法致力于常规解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煞有介事地推导出对器官及其功能的种种非常肯定的观点,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验证或否定它们的真伪。”
为正确认识解剖病理学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古希腊人实行尸体火化。在他们的传统迷信观念中,如果不这样做,灵魂将永远在冥河岸边游荡,不得安息。
另一方面,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动物解剖倒是进行得如火如荼,动物内脏的位置和特征自然为人所熟知。这方面大概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贡献更大,这位伟大的学者,超群绝伦的哲学家、生理学家、胚胎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虽从未亲自解剖过人类尸体,却间接对解剖学有着巨大影响。他对动物及动物发育有着令人惊叹的深入研究,也因此成为动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被马其顿 (Macedon) 的腓力浦(Philip,约前380年)聘为顾问,也是腓力浦之子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年)的老师。这位年轻的帝国建立者建造了数个亚历山大里亚城池,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城一度成为世上第一座大都市。这位征服者英年早逝以后,亚历山大帝国瓦解。马其顿的托勒密(Ptolemy,约前320年)---曾是亚历山大最杰出的随从之一,主宰了这座城市和整个埃及。托勒密,本人也曾在腓力浦的朝廷里受到过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有感于他所接受的知识教育,托勒密建立了亚历山大博物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以及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他的继承者们紧接着对二者进行了大规模扩充。所有学科都在此得到发展,但要说最繁荣昌盛和举世闻名,非医学院莫属。在这里,解剖学第一次成为医学的基石;古文明时期的人体解剖也仅在此处才得以大规模进行。塞尔苏斯(Celsus,约前30—公元38年)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us,150—230年)甚至宣称,早期亚历山大解剖学家曾对罪犯进行活体解剖,不过其真实性是存疑的。据说托勒密王室成员曾亲赴解剖室并参与尸体研究,以王室之尊参与这一活动,至今一直被认为是亵渎行为。而亚历山大里亚则自此迎来四百年间世界上最前途无量的医学生。
(插图II 科尼利厄斯·塞尔苏斯)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医学家的著作遗失殆尽,关于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塞尔苏斯和亚历山大的学生,尤其是伽林(Galen,约公元130—200年)。托勒密王宫的医学家中,在解剖学上最负盛名的是希洛菲利(Herophilos,前335—前280)和爱拉吉斯拉特(Erasistratos,约前310—前250)。
“窦汇 (Toucular Herophili)”一词即是以希洛菲利的名字命名。这位解剖学家于公元前300年出生在博斯普鲁斯 (Bosphorus) 海峡边的凯尔西顿 (Chalcedon),后成为科斯学院普拉克撒哥拉斯(Praxagoras,约前340年生)的弟子。普拉克撒哥拉斯是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信徒,捍卫并发展了疾病的体液学说理论。而希洛菲利虽在疗法上追随希波克拉底学派,在理论体系上却与其分道扬镳,摒弃了基于推理的生物学而另行开发了他自己的生理学系统,认为生命的基础是四种力:一行滋养,位于肝脏和消化道;一行保温,位于心脏;一主精神,位于大脑;一主感觉,位于神经。
希洛菲利大概是第一个将解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钻研的解剖学家,但在专注于正常生理解剖之前,他曾多次尝试将解剖结构与疾病相关联,老普林尼(G. Pliny,公元23—79年)称他为通过人体解剖“第一个探索疾病成因的人”。然而我们已难以获悉他的所知所想,仅能从塞尔苏斯清晰的解剖学观点中猜测他的贡献,因为塞尔苏斯的病理解剖学信息大都来自希腊人,而这里所谓的“希腊人”指的应该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人。
同时代的爱拉吉斯拉特更多地则是作为生理学家被人们知晓,而非解剖学家。他生于喀俄斯岛 (Ceos) 上的卢里斯 (Iulis),父亲是医生,老师是迈特罗多鲁斯 (Metrodorus),迈特罗多鲁斯又是克吕西波(Chrysippos,前3世纪)的学生。克吕西波是当时科斯学院的竞争对手——尼多斯 (Cnidos) 医学院的著名人物之一,并不像科斯学院那样热衷于抽象推理。我们无从知晓爱拉吉斯拉特在亚历山大里亚生活了多久,他一度是塞琉古 (Seleucid) 王朝首都安提俄克 (Antioch) 的御医,塞琉古王朝是亚力山大帝国瓦解后建立的另一独立强国。
爱拉吉斯拉特实为病理学的创始者之一,但他的基本观念则被弃置已久。他自己根据一个显著的科学错误建立了一套生理学体系,误导了许多古人。爱拉吉斯拉特和他的同伴在解剖时看到的动脉都是塌陷的,里面仅包含空气。 现在我们知道,死亡后富有弹性的动脉壁会将血液推送到毛细血管,而在尸体解剖时血管无可避免会被打开,空气便会进入。但爱拉吉斯拉特当时并不知道毛细血管的存在,因此认为有两种循环,分别是来自心脏的血液循环和来自肺的空气循环;血液和空气是生命延续所需的两种重要物质,分别供应营养和能量。他将通过血管输送到器官的物质称为“实质 (parenchyma)”,这个词现在的含义有别于当时。当器官过分充盈,营养物质无法充分消化,就会出现“多血症”。
围绕着“多血症”,爱拉吉斯拉特建立起他的整个病理学系统,疾病定位依据解剖学,疾病解释则依据他所发明的这套营养说。他给这一体系找到一个典型例子——肝脏多血症,即他对腹腔积液和肝脏纤维性硬化的经典观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肝硬化伴腹水。尽管如今对这种常见积液的解释已经改变,但爱拉吉斯拉特明确地将腹水与肝脏疾病相联系,代表着敏锐的亚历山大里亚解剖学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为了阐述疾病发生的原因而进行解剖,这一成就光照古今。
爱拉吉斯拉特认为,炎症是血管末端血液填充过度的结果,发烧则被解释为动脉中“灵气”或空气过度充盈,他甚至于认为血液在动脉中的存在也是病态的,因为他认为正常情况下动脉应该充满空气。他的观点暗示了 “充血”这一现代概念,类似还有肺部炎症是肺动脉充血的结果,关节炎就是关节多血症。说到底,他犯了同时期及其后所有病理生物学家的通病——因果混淆。
希洛菲利和爱拉吉斯拉特的追随者们在聪明才智上仅稍逊于两位前辈,他们继续将生理和病理解剖学发扬光大,与科斯学派的黑胆汁学说 (atra bilists) 彻底分离。然而第一代托勒密王朝对医学的推动并没有持续很久,早在尤里乌斯凯撒吞并埃及之前,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已逐渐僵化、教条化而不复创造性。公元前48年,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凯撒的军队严重破坏。幸运的是,在这之前,亚历山大里亚古老的医学文献已有许多手抄副本被送到其他地方,包括罗马——百年之后,塞尔苏斯在这里撰写《论医学》(De Re Medicina),保存了文献精华。
从亚历山大到伽林之间这段时期,诸多持续不久的学派百花齐放,试图根据一些简单的原则系统地解释疾病。比提尼亚 (Bithynia) 的阿斯克来皮亚德(Asclepiades,约前128—前56)极力反对科斯(Cos)的体液病理学,同时也不屑亚历山大时代的学说。他所提出的发病机制的理论的中心思想包含于“strictum et laxum”(原子病理学说),这一理论基于身体具有无数的可以调节的微孔。他假设身体由原子构成,原子之间有管状空间,维系生命的体液经此流通。如果原子和毛孔大小协调,体液流动不受干扰,身体就保持健康;如果毛孔过度收缩或松弛,疾病就会发生,收缩时引起急性病,松弛时则发生慢性疾病。
劳迪西亚 (Laodicea) 的塞米松(Themison,前123—前43年)被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公元55—约127年)刻薄地评论为糊涂虫医生,他接受并发展了阿斯克来皮亚德的原子病理学说。他和阿斯克来皮亚德一样,根据毛孔的状态将疾病分为两种形式:(1)僵硬或紧张型,(2)松弛型,分别对应于排泄过度和不足。以此为基础,他创建了方法学派 (School of Methodism),后经他的学生他拉勒 (Tralles) 的塞萨洛斯 (Thessalos) 传承。该学派的信徒很多坚信治疗疾病不需要了解身体解剖结构及其病理变化,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与该学派最后的没落关系甚大。尽管如此,方法学派在伽林时代之前的两个世纪都是罗马具有统治地位的学派,在那之后仍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灵气学派 (Pneumatic School) 由西里西亚 (Cilicia) 的阿西纽斯(Athenaeus,约前70年)创立,提出体内的固体和液体均由一种气体精髓或称“灵气”支配,灵气的正常或异常决定了身体的健康或疾病。这一思想流派无甚贡献且很快没落,但其学说内涵却反复重现于伽林到现代的许多时期。而灵气作为生命力的象征和一种无形的力量则被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赫尔蒙特 (van Helmont) 和所有其他神秘主义者所倚重。
科尼利厄斯塞尔苏斯的《论医学》无疑是伽林之前病理学知识最伟大的汇编作品。塞尔苏斯是奥古斯都 (Augustus) 和提比略(Tiberius,约前30—公元38年)时期的罗马贵族,他显然不是一名医生,而是一个兴趣广泛且文学素养不俗的有闲之人。可能正因为他的非专业地位,塞尔苏斯并不被当时的医学界知晓或重视,当然也毫无影响力可言。他的作品偶被阅读,很快遗失或被遗忘在修道院,直到1443年撒占内 (Sarzanne) 的托马斯 (Thomas) 及后来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 (Pope Nicholas V) 在米兰的圣安布罗斯教堂意外发现一部古代手稿。这一发现在当时医学界掀起热潮,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论医学》问世之初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它清晰地勾画出公元前时代结束之际的医学从业人员的病理解剖学和生理学水准,这点对我们意义非凡。这部著作主要受到来自希波克拉底、阿斯克来皮亚德学派、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师解剖学家的启蒙,以及必然最更直接地受到其他今已佚失的医学作品的影响。它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永恒的纪念碑,在某种意义上,如纽伯格所说,取代了该学派遗失的文献。它比任何其他文献都更重视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解剖学上的巨大进步。
《论医学》八卷中的第四卷记载了当时病理学丰富的观察记录,并按照经典解剖学顺序,从头到胸、腹等对疾病进行排序和描述。胸膜肺炎被描述为一种整个肺部均受影响的疾病,显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炎。记录了肿大、坚硬且具有弹性的脾脏,这显然有部分是疟疾引起的。书中还提及一种疾病“位于大肠,主要累及前面提到的盲肠所在部位,伴随严重炎症和剧痛,尤其在右侧”;而直到1880年以后阑尾炎才被记入死亡档案!
卷三包含了炎症的经典定义“Notae vero inflammationis sunt quatuor, rubor et tumor, cum calore et dolore”——即今天每个医学生都知道的红、肿、热、痛。书中对发热进行了临床讨论,描述了一种“希腊人称为‘φθίσις’的最危险的痨病”并附有希波克拉底体液论的解释。显然塞尔苏斯和亚历山大人都无法完全脱离黏液和黑胆汁学派理论的影响。
卷五对伤口排出“血、腐液和脓”的记述堪称经典,对皮肤癌的绘图也相当准确。对淋巴结核的描写十分形象:“脓血凝结,形似小的腺体,主要在颈部生长,但也见于腋下、腹股沟及体侧”;对脓疮的描述也无可挑剔:“集结的小体倾向于化脓,形成通常所说的脓疮,起初发红、发热、质硬,红肿多时后化脓,变成白色”。
书中还记述了各部位的坏疽,一种“耳中流脓,导致精神错乱和死亡”的疾病(脑膜炎无疑),以及痛风、疝气、淋病、软性下疳、尿路结石等等,此处篇幅有限,无法提及更多。总之,《论医学》八册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病理学,一部近乎现代的著作,不像伽林的医书那样晦涩冗长,开此类作品之先河,在费尔内尔(Jean Fernel,1497—1558)的《病理学书目VII》 (Pathologiae Libri VII) 问世之前一枝独秀。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09-27 09:57:16 编辑
序言
酒好客自来,除非作者是外国人, 否则给有价值的书作序从来都是多此一举。这里我违背这一常规的唯一理由,是本作品第一次以英语对该主题进行确切的、系统性的阐述,且作者通过他卓尔不群的能力、难能可贵的勤勉和时刻准备纠错的态度成功完成了他的计划。郎博士(Dr.Long)师承威尔斯(Wells)与赫克通(Hektoen),作为芝加哥大学病理学教授,为助益他的学生而写下此书。他完全正确的认识到,要全面了解一门学科,学习它的发展历程是最有效的方法了。扑朔迷离的大量历史细节在时空的维度中得到最好的检验,现在呈现在医学各分科的学生面前,这一方法自奥斯勒在医院病房首次试用后即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当今高水平的医学教师,几乎没有人不将他们学科的发展史和里程碑、其成就与失败、道路与艰险纳入他们详尽的授课当中。对于这种实用型教学,微尔啸(Virchow, 1895)、基亚里(Chiari, 1903)这些大师的早期概述基本已不能满足需要,而埃德加•哥希米德(Edgar Goldschmid)的《病理学图谱史》(History of Pathological Illustration)(莱比锡,1925),虽赶上了形象化的新潮,实质上却不过是一本刻意模仿了舒朗(Choulant)的参考册子。
朗博士将他的研究整理成紧凑的十二章,讲述病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新趋势。如同众多其他的医学分支,病理学的发展并非连续而是断断续续取得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动能各不相同,古代的体液学说,中世纪司法尸检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现代解剖学(莱昂纳多,维萨里)(Leonardo, Vesalius)的兴起,解剖图例从钢笔画与木刻到钢基印版与照片的演化,十八世纪的系统化风潮,临床数据与尸检发现的关联(莫加尔尼)(Morgagni),实验法(约翰•亨特,马让迪)(John Hunter, Magendie),组织学的创建(比沙,亨勒)(Bichat, Henle),显微镜学,细胞学说(施旺,微尔啸)(Schwann, Virchow),神经学(沙尔科)(Charcot),细菌学(巴斯德,科赫)(Pasteur, Koch),血清学和免疫学(梅奇尼科夫,欧利希)(Metchnikoff, Ehrlich),内分泌学(布朗斯夸)(Brown-Séquard)以及生物化学(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的兴起。除了这些伟大的大师们,以下名字也是这个故事中熠熠闪光的珍宝——贝尼维耶尼(Benivieni),费尔内尔(Fernel),普拉特尔(Platter),科伊特(Coiter),多东斯(Dodoens),申克•冯•格雷芬伯格(Schenck von Grafenburg),塞韦里诺(Severino),蒂尔普(Tulp),皮埃特•波夫(Pieter Pauw),维普芬(Wepfer),博尼特(Bonet),克尔克林(Kerkring),布兰卡特(Blankaart),维厄桑斯(Vieussens),塞纳克(Senac),桑迪福特(Sandifort),高伯(Gaub),贝利(Baillie),贝尔(Bayle),洛布斯坦(Lobstein),克吕韦耶(Cruveilhier),拉耶(Rayer),卡斯韦尔(Carswell),霍纳(Horner),费特尔(Vetter),魏希瑟尔鲍姆(Weichselbaum),帕耳陶夫(Paltauf),基亚里(Chiari),帕努姆(Panum),雷克林豪森(Rechlinghausen),维尔曼(Villemin),斯特里克(Stricker),魏格特(Weigert),齐格勒(Ziegler),森克尔(Zenker),佩吉特(Paget),德拉菲尔德(Delafield),普鲁登(Prudden)——这份名单与一般医学历史主线中常见的标志性人物完全不同,正印证了苏德霍夫(Sudhoff)的观点:专业学科的历史只能由该领域的专家来撰写。随着细菌学的兴起(约1875-1900),大体与显微(描述性)病理学成为历史背景,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发挥作用。微尔啸及其学校与其弟子科赫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个体性的,而与当时对这一趋势的展望密切相关。假如瑙宁(Naunyn)是微尔啸的学生,那么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对他的憎恶可能就没那么强烈了。世界大战(译注:一战)期间,很难找到在必要时能够进行尸检解剖的军医。阿朔夫(Aschoff)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非凡组织能力给病理学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新的系统中,形态学(描述性)、生物化学与实验医学,换言之形式、物质与力,逐渐被认为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正如在物理和化学那样。“以发掘事物本质为天职的医生,应当避免仅仅关注静止不动的东西;恰恰相反,他是动力学的大师”(奥尔巴特)(Allbutt),他的研究领域是一种动态的物体。。
追寻更久远的病理学起点,探究它从何处发源、为何出现以及如何开始,这将要回到如何解答人类心灵的基本问题。奥斯勒(Osler)曾说:“东方人追求正义,西方人追求知识。”当乔达摩(Gautama)初次见识到衰弱的老人、可憎的疾病与腐烂的尸体,他策马冲进月光中,寻求修行教化之道。“是什么使人们遭受苦难与悲伤,疾病与死亡?”对这个沉重的问题,他所提出的解答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的基础。诚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也思考过这个压抑的问题,并作出了类似的道义方面的反应,但病床边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目睹着强盗骨骼的伽林(Galen)则同这位高贵的拉其普特(Rajput)王子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线。释迦牟尼(Sakiya Muni)在菩提树下的苦修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苦难与疾病的科学——病理学的目标和存在的原因。苏德霍夫(Sudhoff)巧妙而机智地回溯了原始初民的可能反应(或者可以这么推断)。病人的痛苦暗示着他的身体里藏有一只恶魔,而显而易见伴随着流血的常常是暴毙、经期不适、鼻出血、体内疾病(血尿与血便)以及各种创伤。“血从伤口,也从鼻子、眼皮、嘴、血管、生殖与排泄孔流出……实际上血液无处不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眼泪、唾液、耳垢、尿液、粪便、精液、月经、呕吐物、脓和粘液,这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体液学说,亚述巴比伦(Assyro-Babylonian)医书中suala、或称“粘液系列”疾病的部分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库赫勒)(Küchler)。从希腊传来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us)的数目哲学以及他的理论——宇宙由对立的元素组成,随之而来的是伊奥尼亚(Ionian)哲学家的观点——水、土、气与火是万物之根。在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残篇 中,这些有着显著物理性质(湿、干、冷、温)的元素正组合起来,由此产生了古老的物理化学和生理学:
“首先请听清,万物有四根:
……
学习会使你智力长增。
前面我已宣布讲话的目的,
且要述说一个双重的道理:
存在一时由众多生成单一,
一时则从单一分为众多,
火、水、土以及高高在上的气。
……………………………………
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存在都出于它们,
树木、男子和妇女,
走兽、飞禽和游鱼,
还有长生的神灵,享尽殊誉。
…………………………………
先从土里长出了有着笼统本性的形体,
它们分有了水和火气。
火把它们送往高处,
欲求达到那相同的东西。
各个肢体的可爱形相尚未显露,
无声音也无男子特有的器具。
……………………………………
种子进入洁净的孕育之地,
当它们遇冷,女孩将诞生;
当它们遇上火气,男孩将出世。
……………………………………
在第八个月的第十日,
血液变成白色脓汁。”
从干冷的土、湿冷的水、干热的火以及温润的气,到巴比伦人发现的各种体液——潮热的血液质、潮冷的粘液质、干热的(黄)胆液质和干冷的(黑)胆质——其实仅一步之遥。这样的排列组合产生了体液学说,后者直至十七世纪还影响着欧洲的医学实践,单单伊丽莎白(Elizabethan)时代、雅克比(Jacobian)时代和查理(Caroline)时代剧作家的无数篇章就可以证明。
本书主要为医学专业的学生而写,实际上却完全可以推荐给任何希望了解医学基本理论之起源与发展的医生。仅讲述的主题本身就已带有高度的启发性——正是这无数具有献身精神、不畏自我牺牲的劳动,使我们的学科蓬勃发展,在当今科学之林巍然屹立。
菲尔丁•哈德孙•加里森(F•H•GARRISON)
1928年8月9日
于陆军医学博物馆
注:诗歌部分, 英语译文来自威廉•埃勒里•伦纳德教授(William Ellery Leonard),芝加哥,1908年——作者注;中文译文部分摘自苗立田先生《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译注。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09-28 09:33:14 编辑
前言
写作本书主要是为了医科学生,医学课程日益繁重,学生需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如果他们不能对琐碎的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大量细节难免会令他们困惑不已。几年的病理学教学使我坚信,要认识一门学科,没有比学习它的发展历程更有效的了。
此外,要真实地向学生教授病理学,就需要经常向他们讲解一些细节的不确定性,而这很有可能打击学生的信心,除非他们能够明白,这门科学的整个发展史就是与这样的不确定性作斗争的历史。他们或许会感到惊讶,最伟大的病理学大师们竟也犯过最糟糕的错误,但转念一想他们就能从这项意外的发现中得到极大的激励。
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传记形式的,人类和他们所写的著作共同建立了病理学。而如果不能将学科的发展置于历史大局之中,结合重要的社会运动宏观考察,就不可能对任何学科的历史演化有一个真实的概念。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小书,已然精简得连许多与主题相关且有趣有料的细节都必须割舍,就更无法奢望能过多考虑历史全局了,这一点还需读者留心其他资源。
采用传记体例则难免会在对科学发现的价值评估上失之偏颇,毫无疑问本书也无法幸免于此。笔墨将集中于曾做出有伟大贡献的人和学院,即便那些发现只是时机成熟时的水到渠成。鉴于当代成就难以评价,因此我们对近期发现绝大多数未予置评。
拙作准备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多方的帮助。十分感谢约翰克勒拉图书馆 (John Crerar Library) 的工作人员为我提供的便利,让我不仅能轻松查阅图书馆丰富的资料,还能借阅珍贵藏本以复制其中片段。辛格(Singer)、鲁巴尔希 (Lubarsch) 和鲁文斯坦 (Loewenstein) 教授从国外给我寄来了插图材料。赫克通 (Hektoen) 教授提出了关于图解的宝贵建议并借给我有用的资料。其他同事和朋友帮助我完成原稿、修正错误,并提出了宝贵建议。
本书借鉴了大量医学史领域的优秀出版物,数量太多,恐怕无法分别致谢。令我受益尤多的是普施曼 (Puschmann) 的《医学史手册》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中汉斯基亚里 (Hanns Chiari) 所著《病理学史》 (History of Pathology) 一章,纽伯格 (Neuburger) 教授的《医学史》 (History of Medicine),以及最重要、对本书每一章都有宝贵指导作用的、加里森中校 (Fielding H. Garrison) 的《医学史简介》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中校本人也亲自关心了本书文字的修缮,令我获益匪浅。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和作品,我在此表达诚挚感谢。
埃斯蒙德雷朗 (E. R. L)
1928年6月1日
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芝加哥大学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11-03 10:33:40 编辑
公元初期,方法学派在罗马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疾病通常是身体所谓微孔的大小产生变化,即收缩或异常扩张而引起的。 希波克拉底及其追随者的体液病理学说此时黯然失色。 亚历山大里亚的解剖学家对疾病时体内脏器病变的具体而真实的观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不过有心阅读的学生仍能接触到由罗马文学家塞尔苏斯完成的精简汇编。当时的名医都是亚裔希腊人,他们接受了抽象哲学的培训,有很好的观察力,却无意通过严谨的试验来证实其推测。当时文明的希腊人不再进行人体解剖,因此病理解剖学停滞不前。
然而其他学派仍有众多信徒,比如灵气学派,他们既不接受体液病理理论也排斥方法学说。还有不少非传统的方法学派,他们基本上认同身体微孔的收缩和舒张理论,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对真理持开放态度,不论其来源。这些人也被称为折中学派,他们当中以索兰纳斯(Soranus,约公元100年)最为著名。 索兰纳斯生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 (Ephesus),后到亚历山大里亚医学院求学,最终在罗马成为一名医生,活跃于图拉真(Trajan,罗马皇帝,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时期。他主要以对妇产科做出的贡献闻名,事实上他很可能在医学其他分支有同等成就,只不过妇产科方面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更多而已。他对病理学的具体贡献集中在对女性生殖器官的研究上,描述了子宫炎症、硬癌和“硬结 (scleromata)”(可能指癌症及今天所说的良性“纤维”瘤),以及较平常的子宫移位、白带和经血过多。方法学派的汇编者与分类学家塞利乌斯•奥雷利安努斯(Caelius Aurelianus,约公元5世纪)的翻译显示,索兰纳斯的病理学理论主要属于方法学派范畴,强调身体所谓的整体状态以及特定部位的临床表现。例如,他认为肺炎是一种倾向于表现在肺部的全身性疾病。
以弗所的鲁弗斯 (Rufus) 与索兰纳斯是同时代的医生,也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接受教育。他精心描述了肆虐西方世界的大瘟疫——麻风和黑死病,也留下了有关丹毒的记录。其解剖学观点反映在他命名的小册子《论人体部位的命名》 (On the Naming of the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惋惜不能像前人那样进行人体解剖,只能局限于猴子,对此耿耿于怀。他描述了皮肤癌,但其中一些记录表明可能是黑色素瘤。
亚帕米亚 (Apameia) 的阿奇基斯 (Archigenes) 亦与索兰纳斯是同时期的医生,这名叙利亚人是当时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之一,现被认为是灵气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著述的具体内容现无法确定,但鉴于古人有大量引用他人论著而无致谢的陋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雷提乌斯(Aretaeus,公元1世纪)和艾修斯(Aëtius,502—575)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阿奇基斯。他似乎对乳房和子宫的癌症很有研究,注意到男性乳房也偶有癌症发生。他再次提起曾令早期希腊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类比——癌症的生长就像蟹爪,顽固的抓附于周围的组织,外科切除常常徒劳无功。他留下一种药膏,名为“阿奇基斯抗恶疮膏 (medicamenium archigenis ad cancros ulcerates)”,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的阿雷提乌斯是一位知识面很广泛的灵气学家,他的确切活动时间至今存疑。其经典著作《论急慢性疾病的成因和特征》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and Chronic Disease) 在生理和病理概论上依然遵循希波克拉底学说,但对解剖学细节的描述则要进步许多,每章均以对所论部位的简短解剖学描述开篇,对每种疾病都至少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剖学基础。他认为患痢疾的病人肠道存在溃疡;解释交叉性瘫痪的原因;发现腹水和伴随呼吸困难及心脏衰竭的全身性水肿之间有相互关系;描绘了“肺组织无溃烂,但充满体液和凝结物”的结核性病变,提到该病常伴有肠道末端松弛,并附以触目惊心的图像显示此病导致的消瘦,这些都反映他非常重视疾病解剖学。他对肺炎、糖尿病、麻风和白喉(ulcera Syriaca)的临床描述深受赞誉。威尔曼 (Wellmann) 称,阿雷提乌斯作品的许多信息来自阿奇基斯,但其中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原创。其著作仅引用希波克拉底学派的言论,体液病理学说的回归自此开启,并在伽林时期达到顶峰。
伽林(Claudis Galen,129—201年)生于小亚细亚富裕的文化城市帕加蒙 (Pergamus)。二十岁之前,他外出游历了当时文明世界的许多医学中心,而亚历山大里亚则是他的终极目标,也是后来他最多提及的地方。在亚历山大里亚期间,他在解剖学家马里诺斯 (Marinos) 创办的学校学习。马里诺斯十分善于教授著名前辈的学识,他宣称亲手证实了这些先人关于人体的所有发现。
(插图III 克劳迪亚斯-盖伦 (公元129—201年))
二十八岁时,伽林返回家乡帕加蒙,此时人们已经通过他的作品对他有所了解,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解剖学家被任命为角斗士医生,他在这项工作中积累了很多外科经验。然而,四年后这份差事逐渐变得枯燥乏味,伽林像当时小亚细亚许多有才华的年轻医生一样前往罗马。在罗马的五年,他一边行医,一边向上流阶层的听众发表解剖学演说。他十分受欢迎,但未曾有一刻荒废解剖学研究,这五年的罗马生活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同行的妒忌最终令伽林忍无可忍,他言辞犀利地批评了反对者,最后离开了罗马,但这恰好避开了公元166年的瘟疫。刚回到帕加蒙他就接到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安东尼纳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的传召,让他随自己和维鲁斯 (Verus) 出征去阿奎莱亚 (Aquileia),准备讨伐由马克曼尼人 (marcomanni) 和夸地人 (Quadi) 组成的日耳曼部落。虽然反感这个提议,但伽林还是服从了命令,却在经过色雷斯 (Thrace) 和马其顿 (Macedonia) 时发现这一军事项目被另一场大瘟疫彻底扰乱,维鲁斯也在这场瘟疫中丧生。伽林跟随安东尼纳斯回到罗马,明确表示自己十分厌恶战场,只适合在安静的环境下从事医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安东尼纳斯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他担任儿子康茂德 (Commodus) 的侍从医生。这一职位并不耗费伽林多少时间,于是从公元169年起,直至人生终点,历经安东尼纳斯、康茂德和塞普蒂默斯·塞维鲁 (Septimus Severus) 统治时期,这位勤勉的医生潜心科学工作和著书立说,产出丰厚,所涉领域不仅涉及医学的各方面,甚至还包括哲学和修辞学。
伽林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人物。他的著作在他辞世后统治欧洲医学界长达十三个世纪,其中不论真理还是谬误全被世人当作教条顶礼膜拜。为此他饱受诟病,但事实上这不是他的过错, 诚然他自视甚高,作品中充满强烈的自我陶醉和对意见相左之人毫不掩饰的否定。然而,这在公元二世纪并不是什么失礼的职业行为。
伽林的卓著成就主要有赖于他孜孜不倦的勤勉和洋洋大观的产出。他所犯错误和不恰当的类比并不能抵消他取得的进步,就像二十世纪科学文献每天发布的大量错误最终不能掩盖这个世纪的科学进步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势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留下大量确定的科学事实。维萨留斯 (Vesalius)、哥伦布 (Columbus)、法罗比奥 (Fallopius)、哈维 (Harvey)和莫干尼 (Morgagni) 也正是这样对待伽林的作品。
(插图IV 十四世纪的尸检场景。原稿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此复制品承蒙查尔斯∙辛格博士 (Charles Singer) 惠赠。)
插图IV是已知有关尸体解剖的最早图示之一,辛格博士推定其原稿年代在十四世纪上半叶。
这里我们不重点讨论伽林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观点与发现,只关注其与其病理学贡献相关的部分。他的病理学基本理论是希氏学派的体液学说,今已退出历史舞台,他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个自创的概念,称“引导之气”或“灵气”。必须承认的是,伽林超越了科斯学院最狂热的体液学家,是他而非希波克拉底学派,令中古十三个世纪的人们对黑胆汁畏惧不已。然而,是他对疾病大量特殊的认知,即他的病理学各论使得其全部著作——包括体液病理学打上了权威烙印。
须知伽林对身体病理变化的知识积累是在没有机会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完成的。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后他解剖的人体数不超过2-3例,虽然在短暂的随军期间,他或许观看了少数处死后被军医解剖的、可能正常的蛮族身体。在这样的条件下,伽林不得不抓住机会,通过病人认识疾病的解剖学基础;由于他深韵猿和猪的解剖结构及人体的外部损伤,于是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据此猜测特殊的内部异常。假如当时的罗马传统准许尸检,那么伽林所学到的知识将不可限量,他将会比任何人都能把握好机会,做得更好。
伽林的观点和病理学发现主要记录在他的以下著作中:《论疾病定位》 (Seats of Disease),《论异常肿瘤》(Abnormal Tumors),《论治疗方法——致格劳空》(Therapeutic Method—addressed to Glaucon),《论自然机能》(Natural Faculties) 以及《论各部位的疾病》 (Parts Affected)。其中第一部是关于各部位病理与诊断的大型论著;第二部关于肿瘤,简短但很重要;送给一位哲学家朋友的《论治疗方法——致格劳空》描述各疾病本质及其治疗方法,这部大型著作一度成为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教科书;《论自然机能》是一部生理学教科书,其中频繁提及生理异常;《论各部位的疾病》顾名思义,确是一部病理学各论和病理生理学的伟大参考书。
伽林关于疾病发生的理论大都基于他所提出的呈递 (πρóσθεσις) 和粘附 (πρóσφυσις) 的概念。当适量的正常液体到达某一特定器官,它们将粘附于该器官并被利用。肠道液体的正常消化与吸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呈递与粘附失衡,疾病就将发生。例如,如果消化道拒绝接受呈递到此的食物,即不允许粘附,呕吐就会发生。
伽林对局部和全身水肿的解释与此同出一辙。水肿是体腔和皮下组织充满液体的一种疾病,毫无疑问,伽林和我们一样对其大体和外部特征非常熟悉。他认为组织水分过多是因为呈递到这些部位的液体太稀,无法粘附而转变成一种组织内的液体,因此很容易从身体的实质部位流出。需说明的是,对水肿的解释直到今天也仍是推断性的。
伽林在反驳爱拉吉斯拉特对腹水或腹腔积液的解释时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爱拉吉斯拉特将这种疾病记录为肝脏木质性硬化(即今天所说的肝硬化)的结果(参见第一章)。显然伽林对待爱拉吉斯拉特的任何言论都像斗牛见了红布,非指责不可。在讨论腹水时,伽林写道,他经常发现只要简单地抑制(烧烙?)痔疮,腹部水肿就会发生,并补充说“肝脏当然跟这种水肿没关系”。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痔静脉扩张、肿胀不适的感觉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代偿了肝脏的部分功能,即建立肠道静脉系统向体循环系统的血液的流通。 痔静脉严重扩张可能为病变的肝脏提供充足的代偿,避免腹水的发生。而伽林对痔疮的“抑制”却却是破坏了这种代偿作用, 因此引起腹水。总之,因伽林对血液循环认知有误,所以对循环异常所致病变的解释只能是错上加错了。
伽林解释黄疸所依据的原理与水肿类似。他十分清楚黄疸是胆汁进入血液的结果,亦知当身体充满胆汁时,粪便的胆汁常常消失了。然而在解释黄疸产生的机理时他却忽略了这一联系,退回到古人对脾脏和胆汁关系的猜测中。不过不同的是,科斯学派相信黄疸是脾脏过度分泌胆汁的结果,而伽林提出的理论则认为是脾脏无法清除血液中已存在的黑胆汁。这又是呈递和粘附失衡——脾脏的作用是清除血液中的黑胆汁,但如果脾脏出了故障,例如像他所说的因内部化脓而膨胀,那么尽管呈递正常,粘附却不能发生,血液因此变色。这在公元二世纪称得上一个创意十足的理论,本质上不亚于二十世纪关于肝脏和甲状腺解毒功能的假说。毋庸置疑,这一理论的解剖学基础,是伽林观察到在脾脏病变、明显肿大时常常伴有黄疸的发生。
伽林研究炎症很有天分。他将炎症划归在异常肿胀或肿瘤一类,解释起来长篇大论、不辞劳苦,理解事实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总体上他认为疾病是体液或调控体液的灵气变化所致,与此相对应,炎症的成因即是这些体液在特定部位的过度累积。当体液持续瘀滞,四种主要症状:红、肿、痛、热就会出现,另外他还添加了第五种症状——搏动。然后就是浆液 (ίχωρ) 渗出和化脓,接下来可能发生溃烂 (σηψις)。他认为坏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炎症,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在腿部的坏疽中,动脉是非渗透性的。
如果伽林到此为止,结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他坚持在体液学说上一门心思深入,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在这件事情上,他对前辈希波克拉底过于盲从,极力强调“煎煮 (coction)”或化脓是伤口愈合的重要环节,以至于后来他那些迂腐的信徒,尤其是阿拉伯人,在愈合的过程中过度地促使伤口化脓,而不再像希波克拉底和伽林那样在这方面顺其自然。他们提出“值得赞许的脓液”这一恶名昭著的概念,在医学史上留下一笔浓重的污点。
另一方面,伽林依据内部炎症的外在表现所展开的推理时常精彩绝伦。他不仅能够检测出尿中的脓液,还能根据它的状态巧妙地推断它的来源。他断定,如果脓液呈粗粒悬浮或膜片状则来源于膀胱,事实很可能正是如此;如果脓液与尿液密切混合,则来自于肾脏或输尿管。
通过对活体动物肾脏进行的巧妙实验,伽林了解了泌尿过程的大致情况。他未能明确区分导致尿量增加和减少的肾脏炎症 (νεφρîτις),但对伴有结石的肾炎则比较熟悉。他知道膀胱中的石头常常来自于肾,且在经过输尿管时可引起剧痛,还意识到尿路结石和关节中的痛风沉积二者存在某种相似性。
在肺病理学方面伽林他著述很多,但取得的进步较少。他十分了解支气管炎;也掌握了古代有关脓胸的全部的知识,把它包括在病态肿胀一类。他循序古人惯例,按传统将胸膜肺炎和胸膜炎区别开来,过分强调胸膜炎的存在。在肺结核方面,他沿用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理论,遗憾的是他只字不提该病在罗马的流行,只简单陈述女性患病比男性更普遍。关于肺结核的发生原因,他认为是毒性黏液从大脑流下——老旧的希氏观点;或更常见的由肺出血引起——永远的因果混淆。他认为出血是肺部血管创伤性破裂或局部溃疡的结果。他还注意到肺部的慢性溃疡,伴随偶尔咳嗽甚至咳出肺部碎片或小的碎石;如还伴有严重消瘦则该病为肺结核,否则应考虑其它疾病。
在皮肤肿块或结节方面伽林沿袭了希腊人的观点。 显然他并未亲眼看见和理解这些病况,但他自认为有资格解释它们,将其原因归结为汁液凝结、过于浓稠而无法通过血管。他对结核病的概念因此模糊而混乱不堪,表现出无法通过尸检来理解病情的深深绝望。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肺结核的认知也并无更多进展,这种状况直到西尔维于斯∙德勒博阿 (Sylvius de la Boë) 研究痨病患者的尸体后才有所改善——这已经是15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伽林按症状对发热进行了详细分类,为此提出了一套豪无用处的、揣测性的体液病因论。他很好地区分了稽留热和间歇热,认为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在每日、隔日和四日间歇(或疟疾)热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罗马的沼泽想必为他的疟疾临床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伽林对肿瘤进行了分类,其拉丁译文直到文艺复兴后很久仍被人们奉行,这一点令人格外感兴趣。他一共分了三大类:tumores secundum maturam,包括所有正常生理肿胀,如青春期的乳房和妊娠期的子宫;tumores supra naturam,即创伤后的生长过程,如骨折愈合时结缔组织增生;以及tumores preater naturam,这一类十分庞杂,包括肿瘤、以及众多炎性病变、局部性水肿、坏疽、囊肿和其他一些伽林无法确定其本质的感染。他重新提及古希腊人关于硬癌、无溃疡和溃疡性癌的概念,或多或少地依据溃疡是否发生来确定其恶性程度。他认为黑胆汁是所有癌症的成因。伽林声称,他多次观察到忧郁质的女性比多血质的更易患癌,且他所认为的黑胆汁富集的部位,即面部、嘴唇和乳房,最易发生肿瘤。烈性胆汁导致恶性溃疡型癌症,较温和的胆汁则引起隐性癌,即没有溃疡的癌症。他对身体内部癌症一无所知,也从未怀疑过癌症转移的现象。希波克拉底关于癌症与螃蟹的类比曾是“καρκίνος”和“cancer”二词的由来,这一类比被伽林再次提出:“正如螃蟹的脚从身体各个地方伸出来,此病中扩张的血管亦形成一幅类似的画面。”他不知道淋巴管的存在,今已揭晓为肿瘤向淋巴管的延伸在他看来是向血管的生长,以形成肿块与黑胆汁的有效连接。肿大部位附近的扩张血管组成“蟹状”肿瘤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独领风骚一千年的伽林病理学概况。 这位伟大的帕加蒙智者敲响了方法论的丧钟,复活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疾病解剖学观点,还原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病因学理论并将之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使他长期占据医学统治地位的并不是这些成就,更多是因为他敢于和基本成功地创建一种统一的生物科学,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各分支。其中病理学以各种“气质”为基础,每种“气质”都有其基本“πáθος”影响其生命过程。他的生理学中心思想“目的论”清楚地反映在他的不朽生理学著作《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 (On the Use of Parts) 中,表达了自然设计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与方兴未艾的一神论完美契合,基督教和穆斯林都趋之若鹜。
伽林之后,医学进入了一段很长的停滞期。罗马人除了赛尔苏斯之外没有给医学进步作出任何贡献。随着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城的日益动荡,小亚细亚和附近岛上的希腊医生对这座西方都城越来越失望,认为它不再是学术繁衍的沃土。甚至在相对安宁的东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探索求真的精神也堕于沉寂,最优秀的希腊学者满足于编辑和修订古人的作品,包括希波克拉底、阿奇基斯、安提勒斯 (Antyllus)、索兰纳斯、伽林等等。
在这段拜占庭的汇编时期,以下四位成绩斐然,他们是奥利巴锡阿斯 (Oribasius)、艾修斯 (Aëtius)、他拉勒 (Tralles) 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和埃伊纳 (Aegina) 的保罗 (Paul)。奥利巴锡阿斯(325—403)出生于帕加蒙,是伽林的同乡,后来给以叛教者 (Apostate) 冠名的皇帝朱理安 (Julian) 当医生,在这期间拥有闲暇与机会来研究和更新前人作品。他的著作原本共70部,现仅存25部,其一大功绩在于注明了引用文献的原作者。通过奥利巴锡阿斯的作品,阿奇基斯、安提勒斯及其他人的著述得以流传后世。
亚米大 (Amida) 的艾修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是皇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的医生。他的汇编作品主要取材于以弗所的鲁弗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利奥尼兹 (Leonides) 以及索兰纳斯和阿奇基斯。他对子宫肿瘤有极好的描述,区分了发生溃疡和不发生溃疡的两种形式。他写道:肿瘤常常发生在宫颈,触感硬实、有弹性且不均匀;颜色泛红,接近铅色;有稀薄红黄色水样渗出;基本上是不治之症。这些认知很可能来自于阿奇基斯。根据沃尔夫 (Wolff) 的说法,艾修斯还描述了肛门区域的裂缝、结节和湿疣,这些记录可能指示直肠癌。加里森认为他对眼、耳、鼻、喉、和牙齿的疾病描写是古代最好的。然而,除了外科,艾修斯在其他方面基本没有独创性或新发现,因此不能说他给病理学添加了值得圈点的内容。
他拉勒的亚历山大(525—605)曾在多地求学,在罗马和拜占庭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其突出成就在于建立了体检和病理解剖之间的联系。他分别通过叩诊、点按和扪诊来诊断腹水、水肿和脾肿大,奥尔巴特 (Allbutt) 指出,这是当时医学界流行的诊断方法。此现象也说明,尽管体液病因学说仍占主导地位,但解剖学基础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埃伊纳的保罗(625—690)所著《论医学》 (Epitome) 对奥利巴锡阿斯的作品有极大拓展,尤其在外科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其中有多少来自保罗本人的观察难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从伽林到后来的亚历山大和保罗这期间,人们已经意识到身体内部癌症的存在。亚历山大提到过肝癌,保罗也曾说“身体每一部位均可发生癌症 (In omni corporis parte cancer nasci solet)”。但保罗是个忠实的黑胆汁学家,对病理学理论并无贡献。拜占庭医学的活跃期到保罗这里宣告终结,甚至在汇编领域也再无成果,医学的未来寄望于阿拉伯人。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七世纪早期,阿拉伯沙漠的一支游牧民族,继而是宁静的沙漠城市麦地那 (Medina) 和麦加 (Mecca),迎来了一位新的先知。之后随着世界战争格局的再次变迁,征战在美索不达比亚和尼罗河流域间的军队日渐松散。在先知信徒的带领下,穆斯林士兵迅速攻占叙利亚、拜占庭的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和波斯。埃及望风而降,萨拉森 (Saracen) 铁骑如潮水般席卷北非。最后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克西班牙,一直打到比利牛斯山 (Pyrenees),甚至继续往法国推进。直到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一个世纪后的一年,他们遇上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经历了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惨败。局势逆转,南征北讨的萨拉森人再也没能越过比利牛斯山。但东起突厥斯坦 (Turkestan) 以东、西抵西班牙、横穿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整片区域依然是穆斯林势力范围。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四处攻击、劫掠和制造破坏的伊斯兰教徒中竟出现了一个爱好和平的部落,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祥和的学者。连广受歧视、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惶惶不安、没有未来的犹太人,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获得庇护与发挥才能的机会。正是这部分穆斯林和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为医学的发展增光添彩。
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时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思想。 波斯有一所伟大的医学院,由景教 (Nestorian) 的希腊人建立,这是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教教派,当初被查士丁尼皇帝驱逐出拜占庭的家园。通过这一奇特的连接,君士坦丁堡的医学领袖地位转移到巴格达 (Bagdad)。
伊斯兰时期最伟大的医学作家中有两位波斯人,他们是拉齐斯 (Rhazes) 和阿维森纳 (Avicenna)。拉齐斯(860—932)在巴格达接受医学教育,著有《医学集成》 (Continens) 和《说疫》 (Almansur)。《医学集成》是一部阿拉伯语的综合著作。《说疫》较为简短,是关于天花和麻疹的论著,首次包含了这两种疾病的确切描述。在思想和实践上,拉齐斯是伽林和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
另一位波斯人,布哈拉 (Bokhara) 和巴格达的阿维森纳(980—1036),是一位名医。他闲游浪荡但十分聪明,主要作品《医典》 (Canon) 几乎取代了不可超越的伽林,直到十五世纪仍是最优秀的医学单本。然而总体上它也仅是一部汇编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伽林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原创部分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在斑疹伤寒领域,与拉齐斯类似。
阿维森纳对天花在人群中的普遍发生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在他看来几乎全民患病,因此他认为天花是人类的宿命,每个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会感染。作为一个传统的体液学家,他认为出疹是生命之力在协助排出恶质液体。
伊斯兰帝国西部的阿文祖尔 (Avenzoar,1070—1162)是一位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犹太医生,出生于塞维利亚 (Seville) 附近的书香门第,在哥多华 (Cordova) 的朝廷行医。他因对食道癌和胃癌的记录而引起当今病理学界的浓厚兴趣。他对胃癌(verruca ventriculi,胃部的疣)有着清晰的临床描述,奇怪的是这一常见疾病的解剖结构直到本尼维耶尼 (Benivieni) 时期才被人们所了解。他非常正确的描写了食道癌的临床发展过程:“始于轻微疼痛和吞咽困难,逐渐发展为完全无法吞咽”。阿尔祖文使用银质探条对食道癌进行探查,对胃癌和食道癌使用营养性钡餐。他还描述了浆液性心包炎,并首次提及疥螨,加里森称他为他拉勒的亚历山大之后的寄生虫学第一人。
然而总体上阿拉伯学派和拜占庭时期的抄写员一样,除了临床诊断外,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或病理学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从我们的角度看,《可兰经》对尸体解剖或其他检查的禁令断然遏制了穆斯林医学的发展,而这一禁令对比先前阿拉伯入侵者对活人的残害,则显得可笑而自相矛盾。阿拉伯人在药学领域取得很大的进步,可谓是成就卓著,而药学的日臻上乘则对原始化学科学产生了长远助益。
阿拉伯医学在十字军东征后没落,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成为希腊医学的主要传承者。这样修道士成为医生,但不是外科医生;他们当中有一些对当时喧闹的热门军事职业不感兴趣的性格安静的人,致力于抄录和注解古人的文稿,尤其是伽林的著作。尘封已久的塞尔苏斯的作品也重见天日。这本是医学发展的停滞期,但后来大学逐渐兴盛,包括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学院、巴黎学院,特别是意大利的萨勒诺 (Salerno)、博洛尼亚 (Bologna) 和帕多瓦 (Paduo) 学院。萨勒诺在医学上与十字军有着独特关联,渐渐在实用外科上领先,而在博洛尼亚,解剖和病理解剖这两门基础科学展现出了新的生机。
1260年,博洛尼亚学院出了一个塔代奥∙迪∙阿尔德奥托 (Taddeo di Alderotto),此时学院规模已经很大,拥有10,000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塔代奥的影响得益于博洛尼亚医学一直以来的领先地位。他似乎是第一个将人体解剖学纳入大学常规教程的人,对此我们并无确切证据,但他的学生巴尔托洛梅奥∙达∙瓦利尼昂(Bartolomeo da Varignana,死于1318年)、亨利∙德∙蒙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死于1320年)和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死于1326年)的作品中都谈及解剖,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辛格曾充分引证,这一时期的人体解剖一开始是为发现病因或出于法律原因而进行的尸检,并不是以获得结构信息为目的的常规解剖。在意大利大学文艺复兴的过程中,病理解剖学研究比常规解剖学先一步开始,并最终带动了后者的发展。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原因其实很简单——人们认为常规解剖学已然存在于盖世无双的伽林和才华横溢的编著者阿维森纳的作品中,后者的《医典》当时刚被译成拉丁文。
根据莫尔加尼的说法,早在六世纪的拜占庭,人们已常常通过验尸来确定瘟疫的缘由,但这些验尸结果并未流传下来。关于合法尸检的最早记录之一,是一位名为阿佐利诺 (Azzolino) 的贵族的尸检报告。这位贵族死于1302年,死因疑为中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对猝死做出这种猜测通常再合理不过。此案法庭要求进行尸检,由塔代奥的学生巴尔托洛梅奥∙达∙瓦利尼昂带领一个委员会执行。他们当时做出的决定现不得而知,但通过保存了下来尸检报告,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打开了尸体并进行检查。
萨利切托 (Saliceto) 的威廉(William,约1201—1280)也曾进行法医解剖。威廉与塔代奥同时代,是博洛尼亚一名能干的外科医生,似乎对病理解剖学兴趣浓厚。他进行尸检研究显然并非偶然,著名的“硬结肾 (durities renum)”可能就出自他的解剖观察,这一陈述被认为是现存关于布莱特氏病 (Bright’s disease) 最早的病理解剖记录,出现在他的《概要文集》(Summa Conservationum,1275)中。著作第一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病理学各论,论及从头到脚所有器官的异常情况。关于“硬结肾”的记载十分含糊,并无太大意义,但他将肾病与水肿的发生联系起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关于尸体解剖的神学禁令和解禁一直以来争议颇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十字军战士、自封的耶路撒冷 (Jerusalem) 国王以及那不勒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aples) 的创办者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是当时最开明的人之一,现在认为是他颁布了第一条准许人体解剖的法律。然而直到十四世纪之后很久,尸体解剖亵渎亡灵的观念在大部分欧洲人的脑海里很可能仍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Pope Boniface VIII) 著名的“一圣通谕”(de Sepultris,1300)须承担主要责任,其中写道“解剖尸体,并将其残忍烹煮,使骨骼与肌肉分离,以运回本国安葬;有此行为者将逐出教会。”然而,后来对这一训谕的解释是:最初它的颁布只是单纯地针对当时十字军的一种普遍行为---许多著名骑士的遗体通过这种方式回到欧洲。
尽管如此,尸体解剖是否有罪的问题最终仍需教会权威予以决断。鉴于解剖案例的增长引来颇多怨声,1556年,查理五世 (Charles V) 将争端摆在了在萨拉曼卡大学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神学教授面前。这些智慧而开明的神学家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定论“尸体解剖起有益于医学发展,因此准许天主教教会的基督徒们开展这项工作”,这一决定可能在其后数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意大利大学的兴起,抗议禁令、支持解剖的声音渐渐响起。起初,学习解剖所需要的尸体是由不守礼法的医学生暗地里盗墓获得,官方对这种不法行为最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360年之后,市政立法者懂得支持尸体解剖的好处,就像他们推行能提高地方声誉的其他科学或任何事一样, 因此决定被处决的罪犯尸体可以用于解剖,这样对他们人身权利的剥夺延长到死亡以后。
回到塔代奥学派。我们发现他的学生蒙迪诺(Mondino,1275—1326)渐渐赶上伽林,成为解剖学权威。蒙迪诺接替他的老师做了博洛尼亚学院的首席解剖学家,并于1316年写下一本书。这本书基于伽林和阿拉伯人的学说以及他自己的几例解剖实践,之后两百年一直作为法定的标准教科书。书中记录了他在1315年解剖两具女尸的结果,他试图据此判定怀孕对子宫大小的影响。十六世纪早期,著名解剖学家马克∙安东尼奥∙德拉∙托尔 (Marc Antonio della Torre) 为了能在教学中使用伽林的原著而不用蒙迪诺的书,不得不向当局请愿。如非英年早逝,马克∙安东尼奥∙德拉∙托尔很可能在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协助下,先于维萨留斯实现解剖学的伟大变革。
外科医生亨利∙德∙蒙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约1250—1320)也是塔代奥的学生,当蒙迪诺占据博洛尼亚解剖学的第一把交椅时,他正在蒙彼利埃学院授课。亨利受到当今病理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格外关注,是因为他强调手术的清洁,反对将诱导化脓作为伤口愈合的辅助手段,而这在当时是外科的常见做法。他写有一本伟大的外科著作,但不久就被居伊∙德∙肖利亚克 (Guy de Chauliac) 著名的《外科全书》 (Magna Chirurgia) 取代。亨利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在理论上仍是伽林的信徒。例如,他将癌症在腺体的定位解释为“比之组织实体部位,忧郁物质更易进入海绵状区域”。
居伊∙德∙肖利亚克同样奉行伽林和阿维森纳的观点。与亨利不同的是,他信奉“脓汁有益”的概念,以及伤口在愈合时通过化脓来消化和排出恶质体液的传统观点。居伊遵循中世纪后期对“脓肿”的传统分类,与现代认知有一定相关性。脓肿被分为两种:(1)热型,如蜂窝织炎、脓疱、坏疽和炭疽;(2)冷型,如淋巴结核、水肿、鼓胀和癌症。这一术语因此涵盖了所有肿胀类型,但它将急性炎性肿胀划归为一个特殊类型,几乎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脓肿,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居伊在阿维尼翁 (Avignon) 做教皇的私人医生期间历经了黑死病的两次大流行,他本人也患上这种瘟疫,因此对该病做了准确的描述。他还详细阐述了当时蔓延整个欧洲的麻风病。至于癌症方面,居伊是个彻头彻尾的伽林学派。
整个十四和十五世纪,教授解剖学越来越普遍,但大都仅为证实伽林和蒙迪诺的学术观点。如果这些解剖课程能进行得从容一点,那么病理解剖学或许能够积累大量新知识。遗憾的是由于尸体腐烂迅速,这项工作通常赶在四节课的时间里草草完成。 助教指出身体各部位,而教授则单调地念出伽林的理论,并不多关注眼前桌面上的实物,基本上也没有时间研究各种异常;尽管如此,尸体解剖学的理念仍稳稳扎根。 偶尔也会有人对内部器官损伤发表评论,例如彼得罗∙迪∙蒙塔尼亚纳(Pietro di Montagnana,死于1460年),他声称在帕多瓦的十四次尸检解剖过程中发现了病变的心脏。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12-03 16:01:47 编辑
文艺复兴时期,复活的古老经典恰逢印刷术的春风,为克里斯多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路德 (Luther)、哥白尼 (Copernicus) 和维萨里 (Vesalius) 开启了新的世界,病理解剖学也作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开始了求索之路。
在十二到十五世纪的大学兴起阶段,我们就知道研究人体解剖学的价值;也了解如何在伽林的权威笼罩下归于沉寂。显而易见,解剖结构的变化与疾病息息相关,如今看来伽林对此的系统化已少有可取之处。然而除了外科方面,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变化却不甚关注;在疾病解释上,即使是新医学院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也满足于希波克拉底、伽林以及阿拉伯前辈的理论。
毫无疑问,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的思想家,而新的自由时代则能赋予他们机遇。在洛伦佐·德·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 和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百花齐放时代的佛罗伦萨城,医生安东尼奥·贝尼维耶尼(Antonio Benivieni,约1440—1502)成了开路先锋。他的成就或许完全倚仗印刷术的出现,但更可能是新生的思想者与热忱的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他的生平记录相当不详,显然是出生于佛罗伦萨并在那里行医愈三十载,但求学何处、师从何人却不得而知。事实上,若非他的兄弟杰罗姆在安东尼奥过世五年后的1507年, (Jerome) 整理出他细心保存的病例记录,并在他的老友、著名医生珍·罗莎托斯 (Jean Rosatus) 的鼓励下成书出版,我们将完全不知道这位先驱的存在。这本经典小书名为De abditis nonnullis ac mirandis morborum et sanationum causis。注意 “abditis” 一词,自爱拉吉斯拉特之时起,这是医生第一次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例行尸检来探求病症的“潜藏”或内部原因。书中的一百一十一章短篇记载包含了贝尼维耶尼或他的朋友所进行的二十例尸检的发现。
本书开篇描写的是高卢病 (Morbus Gallicus)。而与文艺复兴一同到来的还有梅毒,由于这一新的灾祸在欧洲快速蔓延,贝尼维耶尼的寿命也因此打了折扣,但在人生末年他显然对该病作了大量观察,并准确描述了它的临床症状,包括颅骨侵蚀——这一病症比现在似乎更加常见。
然而这本书的精华在于对尸检的观察,就目前所知,贝尼维耶尼是向病人亲属申请对病情不明的死者进行尸体解剖的第一个医生。 鉴于现下存在一种奇怪的错误倾向,即突然给每一门学科指定一位始祖,因此他常被称为病理解剖学之父。
但他终究没有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打下基础,并深受他的时代影响而迷信鬼神,对科学权威的引用亦未超出伽林的范畴。尽管许多人引述了他的文章,但不能说他对后人的科学思想产生多少影响。他最伟大和持久的贡献在于开创了通过尸检探求病因的先例。
书中的描述都十分简短,须知实际措辞可能部分是由杰罗姆·贝尼维耶尼(Jerome Benivieni)完成的。尸检完全是为了确定疾病所在部位, 或解释涉及某一特定器官或部位的症状。尸体被切割 (“incidere”) 而不是像后来的莫干尼 (Morgagni) 那样解剖 (“dissecare”),结果当然也相对粗略。
一些比较有趣的病例值得一提:
第36例:一位姻亲吐出全部饮食,无法进食或服药,逐渐消瘦,形销骨立,终致死亡。贝尼维耶尼“为了公众利益”进行解剖,发现其胃部硬结延伸至幽门,阻止食物通过。此例显然是梗阻性幽门癌。
第81例:“仅由风导致的死亡” (“ex solo vento mors subsequuta”)。此病例一切正常,只是内脏充满气体。半个世纪之后的多东斯 (Dodoens) 认为是肠道充气,即鼓胀症。这可能是一种麻痹性肠梗阻,但它究竟是原因不明的腹膜炎、肠系膜血管栓塞,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远隔四个世纪的今天已无法判断。
第83例:一名上了绞刑架的强盗,由于绞绳断裂死而复生,他因再次犯罪而被捕,这次被真正绞死。“震惊于此人之恶”,贝尼维耶尼写道,“他们(他的同伴)煞费苦心争取了一次尸检”,然后惊讶地看到一颗“塞满毛发的心脏 (cor pilis refertum)”。之前记录在医学文献中的一个病例使贝尼维耶尼和他的朋友们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与大奸大恶的品行有关,同时也是“罕见顽强意志的一种标志”。别忘了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此例毫无疑问是一种单纯的纤维素性心包炎,且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损伤被贝尼维耶尼的朋友们、尸检的执行者忽略了。
第93例:“一位名为蒂亚曼提斯 (Diamantes) 的贵族妇女,最近死于结石。”但这并不是贝尼维耶尼所熟悉的普通的胆囊结石,本例“结石并不如预期那样全部存在于胆囊,仅一颗黑色的、如同包在壳中的大栗子样的结石在胆囊中,其他都藏身于悬挂在肝脏外的囊膜中。”这些虽然不难发现, 但观察十分细致,描述如此准确实属不易,“如预期那样”这一表述显示贝尼维耶尼非常熟悉普通胆石病。
书中提及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一名病情不明的肠梗阻患者家属拒绝尸检,很明显,在劝服死者家属相信尸体解剖对于厘清病情的价值这件事情上,贝尼维耶尼往往是成功的。但这个病例还是令贝尼维耶尼沮丧不已 (“Sed nescio qua superstition versi negantibus cognatis”)。
并非所有描述都很清晰,如“存在于肠系膜静脉中并将其堵塞的结痂”。这种情况,他看到的可能是结核病或伤寒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这比少发的肠系膜血管栓塞更为常见。贝尼维耶尼所追随的古希腊人倾向于将增大的淋巴结或结节(皮肤肿块)看作凝固的体液阻塞了静脉(参见第二章的伽林)。
他必定常常把注意力放到明眼可见的现象上,而忽略了主要的损伤,多次将死后变化误认为病理损伤。他细心地观察到心脏“息肉”,如同其后将近三个世纪的病理学家一样,而这当然只是单纯的死后血液凝块。此处我们不再列举其它,而应该知道他对以下情况都有着精彩的描述:可能是结核性的髋关节脓疮;佛罗伦萨几位老绅士的腿部干性坏疽,“希腊人称为坏疽的黑色溃疡”;几种疝气;瘘管,包括膀胱直肠瘘;肋骨腐蚀;龋齿继发的颌骨溃疡;灼伤后的瘢痕;连体双胞胎;以及外科上感兴趣的许多其他损伤。他是一名优秀的手术医师;病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一样,都认为他的著作具有历史意义。诚然他对所观察到的病情解释完全基于陈旧的体液病理学,但他竭尽所能探索疾病所在的器官部位,却是往前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年纪稍轻的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约1460—1525)是与贝尼维耶尼同时代的人,普奇诺提 (Puccinotti) 称他是后者的学生。他是一位解剖学教授,同时是著名的帕多瓦解剖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后来的维萨里 (Vesalius)、哥伦布 (Columbus)、阿卡佩登特 (Aquapendente) 的法布里修 (Fabricius) 与他的学生哈维 (Harvey),以及更晚的莫干尼 (Morgagni) 都曾在这里任教,为这所研究所增光添彩。贝内代蒂 (Benedetti) 在克里特 (Crete) 任军医期间著有一书,书中富于原始记录,包括胆结石、心脏异位及其他病理学发现。后世的医学著作家们十分推崇贝内代蒂,他对病理解剖的贡献足与贝尼维耶尼相提并论。另外,他在鼠疫病毒的传播和梅毒的传染方面也有敏锐观察,并以此著称。
稍晚于贝尼维耶尼, 我们迎来了重量级人物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70—1550)。他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外科学教授,自诩解剖尸体过百,而根据奥尔巴特 (Allbutt) 的说法,这其中有些可能是猪的尸体;但是毋庸置疑贝伦加里奥也进行过人体解剖, 并对后者更加热心。他对蒙迪诺 (Mondino) 著作所写的评论是前维萨里时代解剖学的一部伟大作品,尤以其中插图最负盛名,书中提到了心脏扩大及其他身体异常。贝伦加里奥是本韦努托·切利尼 (Benevenuto Cellini) 的好朋友,后者直白地写道,达·卡尔皮是“一位声望极高的外科医生”,他“行医时处理了号称法国病的可怕病例”,当然收费甚高,“这种病好发于富有的牧师”。但在他离开罗马之后,诚实的切利尼(Cellini)补充道,“经他医治的所有病人都复发了,病情比他来之前严重百倍,如果他没有走,铁定已经被谋杀了”。 但机智的贝伦加里奥已踏上旅程,在强调人体解剖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了下去,如果不考虑他的治疗结果,那么就如拉耶 (Rayer) 所说,他以身作则促进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
同时期的吉罗拉莫·伏拉卡斯托罗 (Girolamo Fracastoro)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医生、诗人、宇宙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病理学方面, 他最受关注的是有关传染病的名著(《论传染与传染病》 (De contagion et contagiosis morbis et curatione))和对梅毒的深入探讨。作者参照斑疹伤寒和肺痨这两次大瘟疫的传染性本质,第一次给传染与传染病下了明确的定义。难能可贵地是他比巴斯德 (Pasteur) 早几个世纪指出了感染(他提到一种可传播的“病毒”)与酿酒发酵之间的相似之处。
然而,伏拉卡斯托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占星家,不可思议的是他开始竟将明显具有传染性的梅毒发病原因部分归结为行星尤其是火星和土星的恶性影响。当时梅毒是一种蔓延迅速的瘟疫,且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其性传播方式即使未被忽略,至少一度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该病起源于西班牙,由哥伦布的船员从美洲带回。后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围攻曾是阿拉贡 (Aragon) 王朝属地的西班牙城市那不勒斯 (Naples),他的军队中有西班牙雇佣兵,人们认为这是该病随后在意大利暴发的原因。法国人将这种新的疾病称为“那不勒斯病”,而那不勒斯人则以“高卢病”回敬之,后一称号显然流传更久。伏拉卡斯托罗在他的著名诗篇《西佛里斯──高卢病》 (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 中引入“syphilis”一词,该词是一位虚构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他因亵渎太阳神而染上此病。十六年后的1546年,伏拉卡斯托罗发表了一篇更为严谨的散文研究,在文中明确强调了梅毒的性传播来源,并准确描述了该病的临床过程,从最初的生殖器官病变到后期的口腔、咽部及骨骼损伤。这之前的1532年,威尼斯的尼古拉斯·马萨 (Nicholas Massa) 已描述过尸体中的梅毒瘤,称其为“白色粘稠物 (materiae albae viscosae)”。
伏拉卡斯托罗同贝尼维耶尼和其他许多杰出医生一样,详细推论了梅毒的来源,却并未解决实际问题,这在1495年是众所周知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多进展。除了在那不勒斯的流行,同年巴塞罗那 (Barcelona) 也有一次梅毒暴发,苏德霍夫 (Sudhoff) 则认为那不勒斯的那场瘟疫可能根本不是梅毒。鲁伊·迪亚兹·德·伊斯拉 (Ruy Díaz de Isla) 大概是第一个提出梅毒来源于美洲的人,这反映在他的一部作品中,该书完成于1510左右,但多年之后才出版。他声称曾为1493年从海地 (Hayti) 返回欧洲的哥伦布的船员治疗这种疾病。新大陆伟大的历史学家奥维耶多 (Oviedo) 和拉斯·卡萨斯 (Las Casas) 也都支持梅毒来自美洲的观点。
另一方面,很多医学史家认为他们在1495年以前的医学文献中找到了关于梅毒的记载。十六世纪中期的多东斯 (Dodoens) 坚称萨利切托 (Saliceto) 的威廉(William,1270)、伯纳德·戈东尼斯(Bernard Gordonius,十四世纪)以及塔兰塔 (Taranta) 的瓦勒斯卡斯(Valescus,1418)都曾描述过梅毒。但不论来源如何,这一疾病毫无疑问在十五世纪末期突然流行,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文明世界。梅毒引起的不同病变间具有非常大的异型性,这着实给病理学出了一道难题,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悬而未决。许多著名人物,包括费内尔 (Fernel)、巴累 (Paré)、巴拉塞尔萨斯 (Paracelsus)、朗契西 (Lancisi)、莫干尼、约翰·亨特 (John Hunter) 和微尔啸 (Virchow) 在解决梅毒的病因、发病机理和病理变化方面都做出了部分重要的贡献。
人们常将十六世纪称为解剖学的世纪,却普遍忽略了这个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仅仅稍逊风骚。解剖在整个欧洲各个大学的普及势必带来病理知识的稳步积累。
维萨里(Vesalius,1514 – 64)、哥伦布(Columbus,1516? – 1559)、法罗比奥(Fallopius,1532 – 62)和欧斯塔希乌斯(Eustachius,1524 – 74)都有新的病理学发现。维萨里非常了解主动脉瘤(该病最早的描述来自于蒙彼利埃的安托万·萨波塔(Antoine Saporta,逝于1573年),并于1555年在奥格斯堡 (Augsburg) 一位贵族病人的身上诊断出这种疾病,两年后奥格斯堡医生对该病人进行的尸检确认了这一诊断。维萨里也曾进行多次法医尸体解剖,据申克·冯·格拉芬贝格 (Schenck von Grafenberg) 称,他曾想将病理发现单独成册出版,或许已完成了手稿。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些手稿很可能在他前往西班牙之前被损毁。某次他情绪失控,焚毁了许多稿件。抱着这些手稿可能幸存的一丝希望,驻马德里 (Madrid) 的法国大使曾在1812年展开过一次搜寻,但豪无结果。维萨里的追随者欧斯塔希乌斯晚年被痛风折磨,在记录肾脏病变之际,他曾懊悔没有趁年轻力壮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病理解剖学研究,而仅仅关注了常规解剖学。
(插图V)让·费内尔(JEAN FERNEL ,1497 – 1558)
(插图VI)约翰·申克·冯·格拉芬贝格(JOHANN SCHENCK VON GRAFENBERG,1530 – 98)
诚然,一般解剖的对象多数是被处决的罪犯,行刑时身体健康,大都处在青壮年时期。这样的尸检来源难以提供大量的病理解剖实例,尽管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现,如贝尼维耶尼曾遇到过的(见上述第83例)。然而,需知秘密掘墓的解剖也并不稀少,死于“自然原因”即疾病的尸体,如果解剖者足够敏锐,就可能发现病理解剖学异常。总之贝尼维耶尼进行的这种尸检解剖,已经了解病人生命末期的临床信息。当时的佛罗伦萨人已成功获得尸检许可,提出申请即可获得保障,与现在完全一样,这显示名医的尸检研究不再被外行大众视为亵渎神明。事实上,如果有需要,教会高僧的尸体也会成为尸检的对象。1410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 (Alexander V) 在博洛尼亚离奇猝死,彼得罗·德阿格拉塔 (Pietro d’Argellata) 对其进行了尸检并把结果记录在他的《外科学》(Surgery)一书中。
总而言之,有关疾病引起的器质性变化,大量信息正不断累积,成为伽林理论的佐证和外科观察的补充。 第一位编纂这些新知识的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医学人物之一——亚眠 (Amiens) 的让·费内尔(Jean Fernel,1497 – 1558)。要展示这个世纪上半叶所取得的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比较贝尼维耶尼与费内尔的主要作品,若说前者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勇敢先锋,那么费内尔则已成长为一位知识全面的病理学家。
1479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出生于皮卡第 (Picardy),早年爱好哲学和古代语言,也曾一度致力于钻研数学,加里森 (Garrison) 认为这一训练毫无疑问与他后期的逻辑分类倾向密切相关。同时他也学习医学,1530年成为一名医生,1534年成为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他的高超医术很快为他带来了大量病人,包括法国宫廷的贵族。他是皇太子的情妇、普瓦捷的狄安娜 (Diana of Poitiers) 的私人医生,皇太子继承皇位成为亨利二世 (Henry Ⅱ) 后,他作为国王以及著名的凯瑟琳·德·梅迪茜 (Catherine de Medici) 王后的侍医,随侍这对王室夫妇的所有行程。
费内尔行医治病的工作已十分繁重,在此间隙他仍热忱而勤奋地收集整理希腊和阿拉伯前辈的医学知识,后果是他自身的健康不堪重负。他有时被称为法国的伽林,却又经常被引证为第一个试图摆脱伽林束缚的人。在医学史上,他率先脱离古人的体液、气质和灵气的教条,不但创建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病理学总论,而且所著病理学各论在编排架构上几乎达到了现代标准。他的著作《通用医学》(Universa Medicina,1554)分为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三部分,成为整个欧洲的医学标准。
费内尔将疾病分为一般与特殊两种,前者没有特定的发病部位,后者发生于某一器官或部位。发热属第一种,另又细分为单纯型、腐败型和瘟疫型。出于系统化目的他把特殊疾病分为三组:(1)影响横膈膜以上的部位,(2)影响横膈膜以下部位,及(3)外部疾病。关于疾病的亚型他分为(1)简单疾病,仅累及器官的一部分;(2)复合疾病,影响到整个器官:以及(3)复杂疾病,身体各部位之间的正常联系遭到破坏。
如我们现在一样,他将疾病的表现区分为症状和体征,并将脉搏和泌尿异常作为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有那么一段时期,呆板的庸医郑重其事地观察患者的一瓶尿液,并煞有介事地根据肉眼所见诊断一切疾病,从失恋到麻疹。费内尔这位数学家写有一篇主题为“尿量多寡之意义 (urinae copia et paucitas, quid indicet)”的章节,其中强调尿排出量变化的意义,已达到了现代水平。他注意到泌尿与排汗的互补关系,以及肿瘤和结石对泌尿道的阻塞作用。
费内尔的《病理学Ⅶ 》(Pathologiae Libri Ⅶ,1554)是第一部可被称作病理学教科书的医学著作,在最后三册中,他简明扼要地汇编了当时有关病变器官异常的知识精华,在此只能就该书的组织架构作简短介绍。在对脑部疾病的讨论中,他意识到髓质或脊髓受压迫可能是瘫痪的一个原因,尽管他对此的解释基于古代幻想的体液学说。他将肺部的空洞(“脓腔”)与脓肿混为一谈,可能是混淆了结核病与化脓的发病过程。但他的《医案》 (Consilia) 中却有一则简短的尸检草案, 清楚地描述了一例普通的慢性溃疡性结核病例。
胃部癌症被归到“脓肿”一类,该词在当时仍然是肿胀的通用名;肿瘤溃疡和腐蚀导致的胃溃疡也有提及。他按顺序分析了隔膜以下的疾病:胃,肝脏,胆囊,脾脏,肠系膜和“他们所谓的胰腺”,肠道,肾脏,子宫及其他生殖器官。最后一章讨论梅毒,对此费内尔可谓见多识广,事实上每个在男女关系混乱的法国宫廷行医的人都不会对这一疾病感到陌生。他将梅毒区分为四种类型,现代所划分的四个阶段可能就是据此而来。
书中某些描述有所偏差,提示他对病情的假设而非实际观察。他认为“阻塞,硬癌性炎症,脓疮和溃疡”是肝、肾常见的异常, 并且非常了解这两种器官的排出通道被结石堵塞的情况,而所述肝脏硬癌性炎症可能包括肝硬化,这点我们可以从“质地坚硬 (praeter naturam durus)”这一描述中判断。但是他对肾脏的类似情形似乎并未过多关注;虽然这种情况一次次被发现,却似乎总能从病理学家审慎的检查中遗漏,直到理查德·布莱特 (Richard Bright) 时代。费内尔认为“肾炎是十分罕见的”, 这种观点很可能直接来自伽林。得益于外科、产科以及尸检知识,他对子宫疾病的治疗近乎完美无暇。
1567年,他对一名九岁女孩进行尸检并将其病况描述为“肠梗阻”,其实毫无疑问这是一例阑尾炎,直到1711年海斯特 (Heister) 发现阑尾炎之前,这是该病的唯一明确记录。他率先研究动脉瘤,是最早提出某些动脉瘤来源于梅毒的人之一。在癌症方面,他是一名彻底的伽林派体液学家,但对内部器官癌症的发病率已有所了解。他将浅表的结节状新生物称为肉瘤 (“sarcoma carius”),包括多种损伤,如溃疡愈合过程中的慢性肉芽组织、鼻息肉以及被称为牙龈瘤的颌部肿瘤。 几百年来,“肉瘤”一词的使用一直都十分广泛。
总的来说他有着十分渊博的病理解剖学知识,虽然他热衷的关于灵气中毒或体液病因的说法现在看来是无稽之谈,但他将疾病定位于实质部位,极大地促进了解剖学观察向更加准确的方向发展。在系统化方面他远远超前于时代,其《病理学》作为当时的教科书并不逊色于两百多年后马修·贝利 (Matthew Baillie) 的版本。他的同辈及下一代的追随者大都满足于收集整理观察所得而并不将其系统化,这一点上费内尔可以说是鹤立鸡群。
当时最重要的具有竞争力的分类是巴塞尔 (Basel) 解剖学家菲利克斯·普莱特(Felix Plater,1536 – 1614)的版本。这位解剖学家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解剖尸体超过三百具,留下大量具有病理解剖学价值的发现。普莱特同时是一名执业医生,他也根据症状对疾病做了分类。他的病理学发现包括舌下结石、巨人症(身高九英尺的男性骨骼)、脑瘤,婴儿的胸腺肥大、肠道寄生虫,以及与终末期水肿有关的囊肿型肝脏和肾脏。他的著作被后世的汇编者大量引用。
同世纪的微尔啸·科伊特(Volcher Coiter,1534 – 约1590)热衷于通过病理解剖探寻疾病的原因。他生于格罗宁根 (Groningen),后在纽伦堡 (Nuremberg) 行医,是法罗比奥的学生,自身也是一位杰出的解剖学家,曾多次力劝当局全力支持对死于严重或疑难疾病的人进行尸检。他对病理解剖研究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为此放弃了私人诊所,做了一名军医,这为他的病理解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最突出的病理学成就在于对脑、脊髓膜炎的描述。
同时期的意大利人、曼图亚 (Mantua) 的马尔塞洛·多纳托(Marcello Donato,十六世纪下半叶)同样坚定地支持尸检解剖。其著作《可敬的医学史》(De medicina historia mirabili,曼图亚,1586)中有一段严肃的训诫,直白地陈述了病理学家长久以来的两个问题,值得在此一观,全文如下:“禁止尸检的人应认真反省其过错。当病因不明时,反对解剖即将被蠕虫吞噬的尸体对这个无生命的物质毫无意义,却对活着的人们造成严重损失;因为他们阻止医生获取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帮助医生找到方法,最终治愈患类似疾病的人或减轻他们的痛苦。出于懒惰或抵触而宁愿停留在无知的黑暗中、不愿努力探索真相的医生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这样的行为有愧于上帝、他们自身以及整个社会。”(摘自伦瓦尔 (Renouard) 所著《医学史》,贡梅格尼 (Comiegny) 译)。
这本书主要收集了其他人对异常情况的观察结果,包括贝尼维耶尼、维萨里、哥伦布、多东斯以及另外一些名气较小的人。这类汇编活动很快变得普遍。多纳托花了十一年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且特别沉迷于一些离奇的故事,如汗血和输尿管排出麦粒。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有价值的记录,这其中包括对直肠癌的第一次准确的病理解剖学描述。该病例见于一名严重便秘的老人,蜡烛无法通过其直肠,尸检发现在收缩严重的直肠上部区域有一块突出的腺状肿瘤。
我们已经看到病理解剖学这门新科学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发展,而荷兰的郎伯特·多东斯 (Rembert Dodoens) 和皮埃特·冯·弗瑞斯特 (Pieter van Foreest) 也参与其中。前者多半以对植物学的贡献闻名,他在莱顿 (Leyden) 任植物学教授,那时候尤其在荷兰(参见后文中勒伊斯 (Ruysch) 的部分),植物学和解剖学的教授职位通常是合并的,在职者同时行医。
多东斯(1517 – 1585)起初在卢万 (Louvain) 求学,后广游法意德,与当时最著名的医生沟通交流,深刻认识到尸检对于理解疾病的意义。在《罕见医学案例》 (Medicinalium observationum exempla rara) 一书的献词中,他提到希波克拉底和伽林并未享受到尸检带来的益处,并补充“后来者则有着极大的优势,可以打开人体,研究隐藏的疾患和潜在的病因”。这本书和多纳托的类似,是罕见案例的集合,区别在于来源为多东斯本人的实践。书中描述了五十四个病例,但其中很少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作品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报告方法仔细区分了主、客观内容。书中的五十四个案例仅少数包含尸检记录,而但凡有此记录,则病例报告方法一律如下:(1)临床病史;(2)尸检,严格以客观术语记叙;(3)分析,或多东斯对病例的主观解释,伴有文献引用和他认为有关的其他材料。
这些病例记录包括:犬咬三十七年后的患狂犬病患者(无尸检);扁桃体脓肿;伴有支气管咳痰纤维蛋白性支气管炎,最终死于肺出血(无尸检);肺部坏疽(米尔贝克 (Meerbeck) 认为是肺梗死,有尸检记录);一名六十岁女性的胃溃疡,患者上腹痛多年(有尸检记录,但描述溃疡出现在胃的外侧及相邻器官上,因此并不清楚);以及一个复杂病例,患者一只脚坏疽、恶病质、明显的晚期腹膜炎,这些可能是恶性肿瘤的继发症(有尸检记录,但报告过于简短,不便理解)。对这些实质部位损伤的解释,多东斯采用的自然也是体液理论的术语,例如,中风的原因是不受控制的黏液突然堵塞了脑室,这些黏液中常混有血液。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古代一直到卫普菲 (Wepfer) 的时代,人们对脑出血和脑膜炎始终有所混淆,他们对多血性和浆液性中风的区分就隐约体现了这一点。
代尔夫特 (Delft) 的皮埃特·冯·弗瑞斯特(1522 – 1597)有“荷兰的希波克拉底”之名,他对罕见病例不像当时其他人那样感兴趣,而更关心常见病。他出版了约一千例病例记录,表现出对病理解剖的关注,但整体上未能成功建立结构异常与生理紊乱之间的关联。
这段时期最伟大的汇编者当属约翰·申克·冯·格拉芬贝格(Johann Schenck von Grafenberg,1530 – 98)。他主要在古老的大学城宾根 (Tübingen) 完成学业,在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行医一段时间后定居弗莱堡 (Freiburg),做了一名城市医生,1598年病逝于当地。晚年(1584 – 97)他完成了伟大著作《医学罕见病例……共七册》(Observationum medicarum rararum . . . libri Ⅶ),该书在1665年以前曾多次再版。书中摘录了他一生所读医学文献中的观察发现,在此基础上他补充了本人及医学领域里亲朋的大量实践所得,书中许多引文是尸检发现的总结。 引用参考文献出处明确与索引编排有序是该书的两大显著优点。
全书多达900页,按惯例以当时医学界名人的赞美之词与美好祝愿开篇。然而,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引言中,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论证对情况不明的病例进行尸检所具有的教育意义,申克引述了古今许多大人物在这方面的言论,包括伽林、普林尼 (Pliny)、阿里桑德罗·贝内代蒂 (Alessandro Benedetti)、约翰·肯特曼(Johann Kentmann,1518 – 74,医生与矿物学家,对人体内的各种钙质沉积物极感兴趣)、微尔啸·科伊特和马尔塞洛·多纳托。该书采取了常用编辑方式,从头部开始,以涉及解剖学上某一部位的症状为基础进行记述,后来的博尼特 (Bonet) 等汇编者也都沿用了这种方式。
申克的著作为今人了解西尔维亚斯 (Sylvius)、维萨里和哥伦布的大量病理学发现提供了一条捷径,这些内容原本分散在他们本人的、更为严格意义上的解剖学著作中。该书的内容引用了自希波克拉底时代起的几乎全部医学作家的文献。书中提到阿文祖尔 (Avenzoar) 的“胃瘤”,甚至还记载了鲍安 (Bauhin) 看到的中风死者开颅时血流喷涌,以及盖尼鲁斯 (Garnerus) 在1578年的一次解剖中观察到重23磅的脾和11磅的肝脏——这很可能是一例脾肿大性髓性白血病;其引用的病理学发现涵盖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申克本人的观察中,关于肠道寄生虫的记录尤其值得称道。整体上,这部作品与现代病理学教科书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但它将病理学的发现以一种便于现代人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汇编著作。
外科医生拥有研究活体病理变化的特殊机会,自然也为病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这其中首推安布鲁瓦兹·巴累(Ambroise Paré,1510 – 90)。这位资深的法国医生在他的著作《外科学》 (Surgery) 的介绍提纲中用大众法语普及了维萨里的理论,从而通过解剖学的成果推动病理学进步。巴累出自理发师医生的阶层,无法使用拉丁语写成论文以进入圣·科姆 (St. Côme) 学院,是第一个敢于在科学论文中使用母语的人。因为他,我们第一次能够听到法语版的肿瘤 “tumors contre nature”而不是时人崇尚的拉丁说法“tumors praeter naturam”。虽然他对这些肿瘤的解释比之伽林并无丝毫进步,但留下了一些优秀的描述,显示他对内部癌症的了解。此外,从他强调乳腺癌患者腋淋巴结肿大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人们对癌症转移的现象正逐渐形成概念。在治疗枪伤时,他第一个免去刺激性的沸油冲洗,提示了后来的无菌操作,这个故事人们耳熟能详,此处不再赘述。巴累熟知动脉瘤,不仅外伤所致的类型,还包括内部动脉瘤,和费内尔一样认为梅毒是该病的一个诱因。
同时期的希尔登 (Hilden) 的威赫姆·法布里(Wilhelm Fabry或Fabricius Hildanus ,1560 – 1634)有“德国的安布鲁瓦兹·巴累”之名,也十分重视病理解剖学。他对常规解剖学颇有研究(甚至建议牧师和律师学习解剖学,以便刑讯罪犯时手段更加灵活有效),留下了有关先天异常的详细记录与绘图。他收集了许多骨折愈合的骨头。但他对病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关于烧伤的论著,经典地把烧伤分为三度;以及伟大作品《论热型和冷型坏疽》 (Gangrene, Hot and Cold),1593年首版后再版十次之多。遗憾的是,他坚定地奉行当时几乎普遍的做法,通过使用各种刺激物有意诱导伤口化脓,对此他的解释一如通常,即这一过程提供了 “恶性体液”得以排出的通道。
总之,十六世纪人们对于疾病在身体实质部位的定位认知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有关发病学的理论和当今一样停滞不前,很少有人具有勇气脱离伽林那些信心十足的言论,其体液和灵气病理学仍然盛行。 少数勇敢的革新者所提出的病理学理论大抵比原来的更加虚无缥缈, 1527年在巴塞尔公开烧毁伽林和阿维森纳作品的巴拉赛尔苏斯(Paracelsus,1493 – 1541)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医学改革家不但喜欢争论而且思想独立。他有占星术背景,将病因理论建立在一种神秘主义的、活力的基础上,认为疾病受一系列“统一体 (entia)”的主宰。但另一方面,关于结石和通风病的沉积物,他提出了沉淀形成设想,这一概念为现代化学病理学埋下了伏笔,他也是第一个将呆小症与地方性甲状腺肿联系在一起的人。
巴拉赛尔苏斯的信徒、比利时神秘主义者冯·海尔蒙特(van Helmont,1577 – 1644)是现代生物化学的又一先驱。他建立了一套现在看来十分荒诞的生理病理系统,对其坚信不疑,并在医学实践中加以应用。正如约翰·罗伯克维兹 (John Lobkowiz) 所说:“海尔蒙特敬业、博学又有名气,是伽林和亚里士多德的死对头。病人在他的治疗下从来不会长时间地受折磨,只需两三天,要么死亡要么痊愈。”1640年海尔蒙特生了一场重病,他成功拯救了自己——如果他本人的陈述可信的话——他是通过连续摄入牡鹿的生殖器官碎屑、少量山羊血,以及与螃蟹眼睛一起煮沸的尿液而治愈的,这一精准的药理组合几乎赶超了阿拉伯人。
海尔蒙特一直生活到了威廉·哈维 (William Harvey) 的时代,却并未受益于后者的名作《论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在他的生理学理论中,生命受胃、脾中的一种主元气 (head Archaeus) 与其他器官中的许多小元气 (archaeus) 调控,他还发现这些元气控制消化酵素的分布。主元气情绪爆发,扰乱酵素的正常分布,从而导致疾病。如果女性乳房受伤,冒犯了主元气,它一怒之下就会产生肿瘤。这种神秘主义的主元气显然就是黑胆汁的替代物,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海尔蒙特清晰地将癌症与其他损伤区别开来。在主元气概念衍生出的酵素领域,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实验者, 为现代生理学奠定了部分基础。 鉴于组织的自溶或自我消化的知识奠定了现代病理变性损伤的基础,化学病理学发展史中应当有海尔蒙特的荣誉之席。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虽出现了维萨里和众多解剖病理学家,但医学理论的权威仍掌握在伽林手中。事实上,由于维萨里以及其他人在某些领域多次支持伽林学说,这位帕加蒙大师对病理学理论的统治甚至更加牢不可破,直到哈维揭开新的一页。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5-12-31 10:33:43 编辑
第四章 十七世纪的病理学
十六世纪,解剖学取得革命性进展,为病变的精确定位奠定了牢固基础。常规解剖和以探测病变为目的的尸检都很普遍,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使这些解剖学的新发现成为人人开卷可及的知识。这些记录最初到处分散,掩埋在毫不相干的材料里,但很快出现了一批汇编者,他们收集这些尸检资料,常用它们来补充自己的观察发现;遗憾的是,这些人大都关注稀奇和罕见的病例,这无法用来构建一种系统性的病理解剖学。然而,也有少数人明智地抓住了重点,把注意力放在常见病上。让·费内尔(Jean Fernel)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杰出的医生编纂了一部《医学体系, System of Medicine》,其中的《病理学》是该学科第一本教科书,不过在病因和发病机理方面,仍然没有脱离伽林和阿拉伯的思想体系。
十七世纪,面临宗教冲突、三十年战争和英国革命的混乱,科学与文学依然得到蓬勃发展。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 – 1657)的著作《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1628)问世,对普通病理学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要真正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果人们继续对血液循环一无所知,信奉动静脉系统简单的往返运行,他们将永远无法发现或理解致命性出血、被动充血、水肿与全身浮肿、栓塞、梗死、脓血症、粟粒性肺结核与肿瘤生长等重要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异常。有史以来任何其他发现大概都不及此项成就对病理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哈维对病理学发展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发现血液循环,在同一领域他另有特殊功劳。他准确地描述了一例心脏肥大病例,这一情况应当是主动脉瓣功能不全造成的,因为按照哈维的记录,该病例主动脉严重扩张;他还描绘了患者死前的症状。此外,他描述了一例心脏破裂病例,患者左心室有一指宽的撕裂性损伤。
任查理一世 (Charles I) 常任御医期间,哈维受国王之命解剖托马斯·帕尔 (Thomas Parr) 的尸体,这位奇人活了足有152岁。对于帕尔的真正死因,哈维的表述十分谨慎,但他表示,如果帕尔来到伦敦后仍同往常一样注意饮食,他可以活得更久。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何种饮食令帕尔如此高寿。
十六世纪,印刷术的出现助益了新兴病理学的发展,维萨里在《人体之构造》 (Fabrica)一书中引入了扬·卡尔卡 (Jan Calcar) 的精美插图;在距此近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我们首次看到了病理损伤的图谱。外科医生马尔科·奥雷里奥·塞维里诺(Marco Aurelio Severino,1580 – 1656)是最先通过图解辅助文字描述病理损伤的人之一。塞维里诺是萨勒诺 (Salerno) 学院后期的一名学生,后来成为那不勒斯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在那里长期居住并最终死于瘟疫。有时他被认为是意大利外科学的改革者,他的伟大著作《论脓肿之本质》(De Recondita Abscessuum Natura ,1632)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本外科病理学教科书。
这是一本关于肿胀 (swelling) 的专著,但仍使用“脓疮 (abscess)”一词,如果排除任何特定的“肿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脓肿。他最擅长的大概就是肿瘤病理学,描述了两性的生殖器官肿瘤以及可能是骨肉瘤的巨型肿瘤。他将乳腺肿瘤划分为四类,其中关于乳腺瘤(Mammarum strumae,区别于硬癌)的记录是对该器官良、恶性肿瘤最好的早期讨论之一。
和当时的所有作者一样,塞维里诺对梅毒进行了大量描述,引用了贝尼维耶尼、费内尔和劳伦·尤本图斯关于内部梅毒的文献,并谈及自身的食道与气管溃疡,以及肺部和肝脏脓肿。他描述了在那不勒斯解剖的一具尸体,病变已从原发部位扩散,破坏了左输精管和内部腺体,在腹股沟形成一个大的溃疡。但这一病例很可能不是梅毒而是淋病或软性下疳,其他溃疡和脓包也不像是梅毒引起的。毫无疑问,关于“梅毒 (lues venerea)”的许多早期描述实际并不是真的梅毒,当时人们把最坏的事都归罪于这种新型瘟疫,这些错误的诊断,是其早期毒性被过度夸大的根源。
西班牙的政权在血腥中倾覆,荷兰共和国崛起,十七世纪本已名声在外的荷兰医学院更加繁荣昌盛。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的尼古拉·特尔普(Nicolaas Tulp,1593 – 1674)率先享受了这场自由的甘霖。这位杰出人物师从彼得·保尔 (Pieter Pauw),后成为解剖学教授,作为伦布兰特 (Rembrandt) 名画《尼古拉·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School of Anatomy) 的中心人物而被人们熟知。他还是一位名医,是首位在民主的阿姆斯特丹乘马车出访病人的医生。特尔普在市政活动中声望也很高,当过几任市长,现普遍认为他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支持医学院的科学发展。在解剖学方面,他以发现回盲瓣(与鲍欣Bauhin共享这一殊荣)及对乳糜管的精彩描述著称。此外,他出版了阿姆斯特丹第一部药典。
特尔普对病理学的贡献亦毫不逊色。他对肿瘤和结石十分感兴趣,留有许多关于恶性肿瘤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对膀胱癌的首次清晰描述:病人生前从直肠排出尿液,据此诊断其患有膀胱肠道瘘;死后尸检发现膀胱肿瘤,且膀胱穿孔到结肠。他描述了几例乳腺癌,并相信该病具有传染性,举例称一名女仆因长期不离不弃地照顾患有乳腺癌的女主人而患上同一疾病。他切除了一名年轻妇女的股骨肿瘤,重十六磅,无疑是一例肉瘤,但病人仍死于复发。另一记录显然是食道癌:“肿块类似癌症”,致食道狭窄,探针几乎无法穿过。此外,他准确描述了葡萄胎:“不成形的带血囊块,一点一点脱落,足有一整桶”,与另一名阿姆斯特丹医生兰姆斯维德(Lamzweerde)分享了首次描述这种肿瘤的荣耀。总而言之,他在肿瘤病理学方面见多识广,经验丰富。
特尔普的伟大著作《医学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1641)与塞维里诺的一样,内附插图。这些木版画内容包括:鼻息肉,纤维蛋白性支气管炎的气管内赘生物(与伽林类似,他认为这是血管的产物,“integra vena a pulmone rejecta”),肺坏疽咳出的肺部碎片(描述很好),绦虫,肾和膀胱结石,脊柱裂(描述极好),连体婴,脐瘘,以及双角子宫积水,但可能是两侧卵巢囊肿(最后两幅亦是封面图片)。
书中还描述了脑积水、眼部肿瘤、上颚溃疡、创伤、骨折、患脚气病的印度人(特尔普与邦提尔斯 (Bontius) 是最早描述此病的人)、腿部坏疽(并未找出病因),以及死亡后不可避免的心脏“息肉”——特尔普似乎觉察到不妥,但仍在插图中画出了这种常见的变化(见插图VIII)。
弗朗西斯·德·勒·波伊·希尔维厄斯(Franciscus de le Boë Sylvius,1614 – 1672)在荷兰医学界地位更加崇高。他出生于德国汉诺威 (Hanover),主要在巴塞尔 (Basel) 接受教育,从1648年开始直到过世,一直担任荷兰莱顿 (Leyden) 大学教授。在医学方面,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建立了医用化学 (iatrochemical) 学派和教授结核病的病理解剖学。
医用化学的基础是一种新的体液病理学,后来的威利斯 (Willis) 和布尔哈弗 (Boerhaave) 都是该学派的追随者。希尔维厄斯精通现代无机化学,大概也很熟悉格劳伯 (Glauber) 关于盐的性质的发现,他深信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冯·海尔蒙特提出的体内发酵理论也给他深刻印象。基于这些,他建立了自己的生理学和疾病发生学说。
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循环血中的酸性和碱性是平衡的,这点相当正确,但他怀疑酵素可能干扰这种平衡。近三个世纪之后,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希尔维厄斯已清晰地阐述了酸中毒和碱中毒的概念,而我们有时还天真地认为这是现代的发明。遗憾的是,他犯了同时代许多人所犯的一个错误,试图依靠一种适用性有限的学说来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他区分了因碱或酸过量而导致的疾病,但与现代概念毫不相关,治疗病人所依据的当然也是关于他的化学指征的观点。对他而言,发酵的本质实际上就等同于碳酸盐遇酸时的产生的发泡反应,这显然是空想出来的。拉耶评论说,希尔维厄斯将观察所得当作系统的关键,却没有意识到,在构建体系时,他本人是最不注意联系实际的。然而他在世时的声望和影响仍不容小觑,且他的观点虽有误,却毋庸置疑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化学的发展。
希尔维厄斯不仅仅是一名理论家,他也曾解剖过数量惊人的尸体,并首次清晰无误地发现结节与结核病之间的关联,这一成就将令他永垂史册。关于结核病,古人对其临床表现已经有了很好的描述,也模糊地辨认出“皮肤肿块”这种伴随症状,但在希尔维厄斯之前却从未有人发现这种特定的、典型的损伤。希尔维厄斯观察到痨病患者肺部的结节,并描述了它们转变为腔洞的过程。将他的记录去芜存精,也许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结核病病理解剖学,但这种改编很可能造成误解,并掩盖在此领域贡献更大的雷奈克 (Laënnec) 的功绩。希尔维厄斯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发现了纵隔、颈部和肠系膜的淋巴结核,但他对此感到困惑,有时似乎认为这些结节是一种异常生长于不同组织的腺体。不过他的陈述中也包含如下巧妙且正确的推论:“正常状态下,肠系膜和颈部两侧的这种腺体极小,但生病时它们的体积和硬度都会急剧增加。”他总结,正常情况下身体中也可能存在这种腺体,但由于体积太小而无法检测到。
病因学方面,他引证了古人的所有观点(参见伽林,第二章),但也补充了自己关于异常液体的化学体液病理学,并认为体液异常是遗传引起的。
在希尔维厄斯建立新的生理学说并将其整合到医学系统中时,一位同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哥本哈根 (Copenhagen) 的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 – 1680),主导了快速发展的解剖学。巴托林的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和学者,他自己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与本国大部分著名医生有联系,他们当中许多与丹麦王宫关系密切。巴托林花了九年时间在莱顿、巴黎、蒙彼利埃、帕多瓦和巴塞尔学习和教授哲学、伦理学、神学、数学,最后是医学。在莱顿期间他再版了父亲的《解剖学》 (Anatomy),这一新版本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数种语言,被欧洲医生奉为解剖学教材达五十年。
最后他回到哥本哈根,取得位列医学系三大教职之一的解剖学教授职位,在那里极受欢迎,连国王都是他的听众。他对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直接贡献在淋巴方面。然而教学非他所好,1656年他退休回到位于哈捷斯提戈德 (Hagestedgaard) 的乡村庄园,然而仍保持与学术界和司法界的联系,余生致力于写作和通信。在这段退休期间,他出版了《医学哲学报》(Acta medica philosophica,1673 – 1680),这是由巴托林编辑众多杰出科学人物的系列论文,,实际上已形成一家医学期刊,走在了时代前列。经过重印和翻译,期刊拥有众多的读者。此外,他还出版了几卷与科学界泰斗的个人通讯。
如此,巴托林做了许多工作来搭建交流出版的桥梁,这对科学进步至关重要。他天才的编辑能力和流畅的笔触比他的个人研究成就更加出色,奠定了他在医学界的永久地位。他个人不修边幅,是个博学的古代学家,可是不加批判地轻信离奇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女妖、长角的女人、山羊所生的男人及各种奇人怪物充斥着他的书页,与准确的学术描写内容共存,这些包括颅骨骨折后的脑部脓肿、糖尿病(多尿症)患者的胰腺肿瘤和其他损伤,以及尿路结石——这种情况在当时肯定比现在普遍得多。
这些观察有些来自巴托林解剖室技巧娴熟的解剖员,有些出自他本人之手,更多则是他在莱顿、帕多瓦、罗马分别与希尔维厄斯、韦斯林 (Vesling)、他勒斯 (Trullus) 一起做研究时的个人尸检记录。退居哈捷斯提戈德(Hagestedgaard)静养时,他本有许多机会将这些零散的记录整合成一个体系,遗憾的是巴托林并不擅长于此,他重复彼得·保尔(1564 – 1614)的错误,将观察到的“心室衰竭所产生的大量黄色胸、腹腔积液”当作一件孤立的奇怪现象,完全没有认识到他描写的是病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病理解剖学的发展正快速赶超常规解剖学,一直以来吸引古人争相猜测的中风症的谜团也在这一时期有所破解。这一发现主要归功于沙夫豪森 (Shaffhausen) 的约翰·雅各布·卫普菲(Johann Jakob Wepfer,1620 – 1695),他是十七世纪最著名的医生之一,对头部疾病尤其感兴趣。与贝尼维耶尼类似,当他遇到致命性的病例时,也总是竭尽全力取得尸检许可,如果失败则深深感到遗憾,例如他曾请求对一名脑积水死者进行尸检,但任凭他祈祷或行贿,都徒劳无功 (“sed nec prece nec pretio quicquam a defuncti uxore et affinibus impetrare valui”)。
目前认为卫普菲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脑出血与某种类型中风之间的关联,以及发现小血管的动脉瘤易感性。不久之后,布伦纳 (Brunner)也描述了这些小动脉瘤,但正如莫干尼所说,“在这个问题上,卫普菲的描述更为清楚”,他通过尸检非常准确地揭晓了这些损伤和临床的相关性。他作品中的优秀观察记录还包括脸部和头部肿瘤、淋巴结核,以及一名男性的硬腭梅毒性溃疡,该病人六年前曾出现过严重的梅毒初始症状。
卫普菲自己晚年所患的疾病很好地展示了那段时期的医学智慧,这场疾病由他的亲人描述,记录在《纪念卫普菲》 (Memoria Wepferiana) 一文中,该文是卫普菲著作《论头部疾病》身后版的前言,记录了他的生平、游历,社会地位和最后的疾病,文章以一张这位伟人的主动脉干从半月瓣到股动脉的图片结束(见下图)。临床上该病属于心源性哮喘 (“non nisi erectus respirare potuit”),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尸检“按惯例”执行,时间是1695年1月28日,由拥有荣誉头衔 (Clarissimus) 的普菲斯特博士 (Dr. D. Pfister) 主持,他是一位“极其熟练的内外科医生”,细致而准确地检查并记录了所有器官的情况。按照他的记录,逝者心脏扩大,靠近肺动脉口存在一处骨样物质;主动脉内含骨样斑块,在腹腔动脉和肾动脉附近尤为突出并难以切割,这种情况现称老年性硬化。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距离常被誉为病理解剖学开端的莫干尼 (Morgagni) 的《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 (Seats and Causes of Disease) 一书问世尚有近七十五年之久。
当欧洲大陆解剖学快步前进之时,在英格兰,特定器官的解剖学知识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主要归功于格里森和威利斯。伦敦的弗朗西斯·格里森(Francis Glisson,1597 – 1677)被布尔哈夫 (Boerhaave) 称为“有史以来最精确的解剖学家”,他进行肝脏研究获取了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为准确了解该器官病理学打下了必要基础。他还是一名优秀的骨科医生,是最早清晰描述佝偻病的人之一。此外,他认识到组织的应激性,这对病理学意义尤其重大,该学说后来主要由哈勒 (Haller) 开拓和发展。
伦敦的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 – 1675)因发现“威利斯氏环”而名垂青史,他的科学关注点同样并不局限在常规解剖学。威利斯是一位杰出的临床医生,也是一名科研人员,勤奋地研究与疾病相关的解剖学损伤。然而,在病因方面,他过分信奉体液理论,并倾向医用化学学说。他显得古怪无礼,既有仰慕者,也有势如水火的诋毁者,许多观察发现的原创性都曾引起不少争议。他生活在战乱时期,是一名坚定的保皇派,在克伦威尔 (Cromwell) 政权下经受了巨大的风险。王政复辟后他获得回报,成为一名教授,这使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追求他的科学爱好。
他不遗余力地研究神经系统的常规解剖学,在病理学方面最重要的观察大都与该系统相关。他确认了卫普菲对中风出血本质的判断,并发表了关于抽搐症的专著。对抽搐症病因的讨论中涉及一些不够清晰的描述,但或可理解为脑膜炎。
他在肺结核方面工作也很有价值,他认为胸部任何轻微的疾病都可能导致肺结核,“如同涓涓之流汇成湖海”。他反对时下将肺结核看作“肺部溃疡损耗整个身体”的观点,指出溃疡并非总是存在,并记录了一个病例,“结节或沙状物质的结石散乱分布在肺部各区域”,可能是一例慢性粟粒性肺结核。
威利斯著有一本有价值的坏血病论著。他对“流行性痢疾”的记录可认为是伤寒症的早期描述,他表示有些年这种疾病比鼠疫更为严重,且由于“某种感染作用于血液,和血液如此紧密的结合呈蒸汽状,或像真正的体液一样与血液充分混合而无法除去;于是它推进至肠道,在动脉上破开小口,形成小的溃疡、渗出或流血”。这一描述现在看来有些离奇,但在十七世纪则并非不可理喻。威利斯对他所看到的病理损伤总能有所解释,他的伟大作品“行医实践 (Practice of Physick)”基本上代表了他本人勤勉研究和原创的观点,而不是小图书馆一样的汇编集。
理查德·莫顿(Richard Morton,1635 – 1698)的《痨病学》(Phthisiologia,1689)是当时关于结核病的另一部伟大著作。 尽管这本书的描述显得重复而矛盾,对疾病的体液学解释也不切实际,但就当时来说,书中的临床描述是十分详尽的。从他对患结核的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分辨出干酪结节性、溃疡性和钙化干酪性三种类型的肺结核,以及干酪性和溃疡性两种肾结核。但总体上,和希尔维厄斯的结核病理学相比, 该作品并没有增加新的有价值的内容。
这一时期英国最伟大的医学人物当数托马斯·西登哈姆(Thomas Sydenham,1624 – 1689),这位伟人直到52岁大龄才拿到博士学位,这点想必能令如今的医学生大感欣慰,更有勇气面对愈加繁琐艰巨的学业要求。西姆哈登视希波克拉底为偶像,本人也是一位天才的简化思维的典范。他是一名体液学者,但并非理论家,只承认观察和实践经验,认为解剖学和生理学本身很有趣,而对于执业医生的训练并不是必须的。他十分简单地把疾病设想为 “旺盛的自然抵抗力祛除致病因素从而治愈病人”的过程。强调自然愈合力是他最伟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教义,但他也是一名活跃的治疗学家,采用超大剂量的汞治疗梅毒,并大量使用草药。他根据致病因素消除的速度和难易程度将疾病分为急性和慢性,大量记述了“血液中的炎症”,认为环境的未知影响对于疾病的起源有重要作用,但对病理学的实质进步并未做出什么贡献。
荷兰、丹麦、德国和英格兰的科学进步之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解剖学家的传统也延续了下来,教皇和国君们都热心地支持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病理解剖学开始被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罗马的乔瓦尼·里瓦(Giovanni Riva,1627 – 1677)是教皇克里蒙九世 (Pope Clement IX) 的医生,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为病理解剖学的讨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会,并与一家医院联合建立了一座病理标本博物馆。里瓦本人也有很多重要的病理学发现,尤其在主动脉瘤方面。
马尔切洛·马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1628 – 1694)大概是十七世纪意大利医学界最伟大的人物。他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从1656年开始任教于比萨 (Pisa),在比较解剖学和植物形态学这两个跨度极大的领域都很有作为。他还是一名具有说服力的作家,反对自然发生说。马尔皮基最显著的成就在于发现毛细血管和红细胞,以及在肾脏、肺和脾脏显微结构方面的精湛工作,因此他是组织学的创始人之一,把显微镜引入医学应用领域也有他的功劳。
复式显微镜发明权的归属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荷兰米德尔堡 (Middleburgh) 的汉斯 (Hans) 和扎卡里亚斯·詹森 (Zacharias Jannsen) 两兄弟是第一台的制造者,这台显微镜据说长一英尺半。荷兰阿尔克马尔 (Alkmaar) 的科尼利厄斯·德雷贝尔 (Cornelius Drebbel) 几乎同时制作了一台更好的,且该仪器的应用推广无疑是他的功劳。另一名荷兰人,来自代尔夫特 (Delft) 的勤奋无比的安东尼·冯·列文虎克(Antonj van Leeuwenhoek,1632 – 1723),使显微镜在多方面的应用成为现实,确认了马尔皮基发现的毛细血管和血细胞,并对各种微观生命形式进行了重要和深入的原始观察。而这之前,富尔达 (Fulda) 的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 – 1680)利用显微镜研究腐败作用,甚至试图通过检查瘟疫病人的血液找出瘟疫的起因。他进一步发展了伏拉卡斯托罗的理论,加林森(Garrison)认为是他首次清晰陈述了“活触染物 (contagium animatum)”是传染病病因这一学说。此外,阿姆斯特丹的扬·施旺麦丹(Jan Swammerdam,1637 – 1680)和伦敦的罗布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 – 1703)也都为这台价值无可估量的仪器在医学界的应用做出了贡献。
马尔皮基(Malpighi)对病理学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开创了它不可缺少的姊妹科学组织学,在宏观观察方面他也有重要发现,不仅在红衣主教博纳凯尔斯 (Cardinal Bonacairsi) 的尸检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主动脉硬化,还留有关于骨髓炎和疑似淋巴肉芽肿病的记录。他也犯了当时的常见错误,并写有一本《论心脏息肉》 (De polypo cordis) 的小册子。
马尔皮基死于1694年11月29日,早卫普菲两个月,死因是卫普菲曾详细描述过的中风。马尔皮基的尸检同卫普菲的一样,很好地展示了前莫干尼时代的验尸技术。尸检由巴利维 (Baglivi) 执行,在场的还有朗契西 (Lancisi) 和其他人,他们把尸检结果献给了当时正开始出版学报的伦敦皇家学会。死者心脏扩大,左心室异常增厚,无息肉;右肾萎缩,骨盆扩大,膀胱中有一颗结石;右脑室中有二盎司淤血,左脑室中有一盎司“黄色黏液”。
他们对出血的解释则反映了古老的体液病理学和新兴的医用化学派体液理论牢不可破的地位:尸检的发现“证明全身的成团的腺体向血液注入了一种酸性淋巴;而忧郁症肿大的腺体,尤其是肝脏中的那些,则注入了一种忧郁的体液;这两种体液被输送到脑血管,引起血液凝结;当它们侵蚀和突破了被膜,进入脑室,就必然导致死亡,回天乏术。”(麦克卡伦 (W. G. MacCallum) 译)。
但尸检的执行者乔吉奥·巴利维(Giorgio Baglivi,1669 – 1707)则尽一切努力冲破体液发病学说的束缚。巴利维是马尔皮基的学生,后成为罗马大学的教授,同格里森一样,他对组织的应激反应颇有研究,倾向于将疾病的原因定位于器官的实质部位而摒弃体液发病学说。由于强调机械生理学,他被认为是意大利医用物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将身体比作一台复杂的机器,牙齿像是剪刀,胃像一只瓶子,血管是运输的管道系统,而心脏是泵。
他使方法学派古老的固体病理学说焕发青春, 将疾病归因于固体部位紧张度的变化,其推测性的病理学概论被称为“青春的流失”(effusion of youth)。但他仍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解剖员,对不断增加的病理解剖学知识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描述了伤寒症特有的肠道变化和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称之为“肠系膜发热症 (Febris mesenterica)”,如果他和威利斯描述的是同一种疾病,那么巴利维的著述取得相当大的进步。
世纪末出现了一批新的尸检报告集 (spicilegia),目前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博尼特 (Bonet) 的《尸检实践》(Sepulchretum anatomicum sive anatomia practica,1679),这本书在病理学发展史中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刺激了莫干尼伟大著作的诞生。
泰奥菲尔·博尼特(THÉOPHILE BONET,1620 – 89)生于日内瓦,他受过很好的教育,1643年进入博洛尼亚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之后很快成为隆格维尔公爵 (Duc de Longueville) 的私人医生,从此行医治病,安居乐业,并有大量闲暇时间阅读学术文献。后来一场意外使他的听力受损,于是他在1675年左右退休。余生踌躇满志,致力于对过去两个世纪的医学以尸检发现为主进行庞大的编辑工作。
他似乎是个严瑾且一心为病人操劳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服务他人,其著作开篇写道:“此书耗费我精力甚巨,读者必将获益良多,但我仍希望人们对我心存感激,因为我拉开了此伟大事业之序幕。”作品本身是个大部头,标题累赘,有1700页。开头是沉闷的献词、冗长的前言和巨幅的作者索引,列出了从希波克拉底一直到当时的众多作者。接下来几页是同时期著名医生对他的礼貌赞词,巴托林、德林考特 (Drelincourt)、派尔 (Peyer)、卫普菲和其他人都有美言,有的甚至使用古典韵律;仿佛缺了这些十七世纪的工作就不曾正确开展。再接着是一系列交叉索引,最后是近三千例尸检草案,后附博尼特本人的评论及参考文献。这些草案按照解剖部位规范排列,即头部、胸腔、腹腔等。然后再全部按症状分类,着实像一间秩序井然的太平间。
作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系统化的推演。博尼特对疾病症状与器质性变化的相互关联非常感兴趣,但他坦诚自己没有能力总结出一般性结论,而将这一工作留给了别人。事实上,利用这部著作至少可以编纂一本综合的描述性病理解剖学,因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情形几乎都能在这一庞大的信息库中找到。当然,许多案例需要经过整理才能方便现代人理解,且数以百计的病例描述因过于简短或模糊而难以解析。
而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它重新发现和保存了其他人被遗忘的工作。当中许多章节,即使我们不被其条理分明的组织结构所折服,也必定由衷钦佩其中素材之丰富。书中有一节很值得注意,这部分介绍的疾病现在判断为肺结核,在该主题上此书显著优于莫干尼的作品,后者有意避开了这一疾病。《消瘦与肺病》 (De Tabe in genere et Pulmonari) 一节博尼特写了有一百页之多,围绕消瘦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汇编,其中引用的许多案例病史清晰,很明显是肺结核,尸检记录也能证明这一点。在一件件病例中,博尼特技巧性地重复了尸检发现的解剖学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临床特征就是Tabes,即严重的进行性消瘦,现在称痨病。这其中多少也混杂了一些别的疾病,如恶性肿瘤和其他使人衰弱的慢性病。在讨论肿瘤的章节(tumores praeter naturam,共四十页)中,他出乎意料地很少谈及内部癌症,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骨肿瘤上,甚至于贝尼维耶尼都能发现的胃癌此处也很少提到,倒是记录了穿透性胃溃疡。
腹部“肿瘤”的章节十分有趣,其中讨论的主要内容实际是腹水。博尼特引用了理查德·洛厄 (Richard Lower) 对腹水的解释,后者曾通过结扎静脉使不同的部位产生水肿(参见第十二章)。但他常将腹水归因为脾脏疾病,历朝历代的古人不知为何都喜欢在这上面发挥想象力。奇怪的是肝硬化反而没有得到重视。关于“肾炎”的记录不少,但大都是描写上行的化脓性肾炎,且常伴随结石。其中录入了一个来自提迈奥斯 (Timaeus) 的病例,病人肾脏“几乎比核桃还小”。
书中还能找到不少关于循环器官疾病的有价值的记录。引自理查德·洛厄的一个病例明显是三尖瓣心内膜炎;另一个来自帕多瓦的彼得罗·德·马尔凯蒂(Pietro de Marchetti,1593 – 1673)的记录则明确描述了一位56岁大学教授的主动脉瘤破裂,左胸腔内的异常搏动折磨了他十年之久。这可能是梅毒性动脉瘤,但博尼特并没有辨别出来,尽管费内尔和安布鲁瓦兹·巴累都曾暗示过这类损伤。博尼特本人对梅毒性病变的描述非常贫乏,只有四页,主要涉及骨损伤,尤其是颅骨蛀蚀,和“硬脑膜性梅毒瘤”。
此书对肺炎极不重视,莫干尼在这方面做得就好多了。博尼特满足于威利斯的观点:“胸膜肺炎常被界定为肺部炎症,症状包括急性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总体上该书并未详细描述急性感染, 而令人费解的是曾在过去两个世纪造成重大伤亡的鼠疫也很少提及。
总结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博尼特的著作是一部勤勉的奇迹,但作者对于病变损伤的分门别类缺少判断力,又不加批判地接受引文原作者的观点,这些瑕疵无可避免地损伤了作品的价值。它是病理学史上最伟大的汇编集,但在科学上却并没有比申克·冯·格拉芬贝格的著作更上一层楼。
这一时期另外两部重要汇编: 一是阿姆斯特丹的西欧多尔·克尔克林(Theodore Kerkring,1640 – 1693)的《解剖案例集》 (Spicilegium anatomicum),克尔克林是勒伊斯 (Ruysch) 早年的同僚;另一部是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史蒂文·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1650 – 1702)的《解剖实践》(Anatomia practica)。博尼特的三千病例中很少有自己的记录,而克尔克林和布兰卡特的书中病例数量虽较少,但都来自于本人的实践经验。克尔克林的记录约一百例,包括许多胎儿异常和一件幽门被异物阻塞的有趣案例。 他最大功绩之一在于发现“心脏息肉”只是一种无意义的死后现象,在此之前这一事实逃过了从贝尼维耶尼到博尼特的所有病理学家的检查。布兰卡特记录了他本人执行的两百例尸检,基亚里认为他对创伤、肺结核、子宫癌和卵巢皮样囊肿的描述都十分准确,但不可否认当中也有许多记录是错误的,有的地方匪夷所思。
以上就是1700年代医学人士可以获取的病理解剖学书籍。这个世纪,病理解剖学知识不断累积,但百年来却没有人将这些新知识系统化、形成一门科学,着实令人费解。材料在手,却没有一个伽林出现,将它们组织起来。罕见病例仍然比一般情形更能吸引病理学家的兴趣。回顾过去,费内尔的《病理学》仍是这一学科最具教育意义的书籍,但它已然过时,影响力逐渐减小,几近于无。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2-02 08:51:53 编辑
第五章 莫干尼与十八世纪
如前所述,十七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为病理解剖学科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专科病理学以大量的尸检为基础,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希尔维厄斯、莫顿和威利斯对结核病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卫普菲关于中风症方面的发现成就卓著;而在肿瘤、结石、水肿和其他常见病方面,有价值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外科病理学在塞维里诺和尼古拉·特尔普的引领下应运而生。显微镜的诞生对病理学发展的潜在价值无可估量。科学交流的新媒体,如新成立的科学学会的学报,以及托马斯·巴托林等出版的科学通讯,都极大地促进了重要科学信息的传播。
另一方面,病理学总论却被一群不切实际的简单体系的吹捧者引入歧途。希尔维厄斯·德·勒·波伊提出了一种新的体液病理学,但它和古老的希波克拉底学说一样,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疾病。青年才俊巴利维和其他人试图以简单的机械概念描述机体功能,但同样不足以归纳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
以博尼特《尸检实践》为首的大型汇编集反映出这一时期医学实践频繁求助于尸检调查的情况,其他记录则显示,通过验尸求证事实甚至在宫廷中也屡见不鲜。纳瓦拉 (Navarre) 的亨利国王 (Henry) 遇刺身亡,解剖学家仔细标注了他身上的刀伤痕迹;短命的痨病患者路易十三 (Louis XIII) 的尸检显示,他的痢疾根源是结核性溃疡,这也是皇室中最早的结核病记录之一。在英国朝廷,威廉·哈维本着一贯的原则——“研究一具死于长期疾病的尸体比解剖十个被绞死的犯人对医学更有意义”,恪尽职守地解剖了他那些贵族病患的尸体。
甚至于外行人也对病理解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桑迪福德讲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荷兰城市)的一位外科医生,名叫马克西米利亚诺·博曼诺 (Maximiliano Bouwmanno),他曾对一名地位显赫的布鲁塞尔 (Brussels) 市民的女儿进行尸检,她死于肾结石和其并发症;记录中提到她的尸体“在众多主妇的围观下被我解剖检查 (a me post mortem dissecta est in praesantia plurimarum matronarum)”,显然当地居民的妻子成群结伴地参加了这一活动。
然而,十七世纪大量的实质性成就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编纂整理。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些知识才在马修·贝利 (Matthew Baillie) 的著作和图谱中系统地呈现出来,才真正能够对医生有所帮助。而中间这些年病理学细节的范围不断拓宽,大概为这类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些知识细节大部分仍来自于大陆学院的解剖学系。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弗瑞德里克·鲁谢(Frederik Ruysch,1638 – 1731)继承了伟大的荷兰解剖学院的优良传统。鲁谢是希尔维厄斯的学生,学生时代即因淋巴管瓣方面的研究工作成名。后期主要成就则是他创造了向身体各部位注蜡的方法,这对微细结构的理解十分重要。
鲁谢对病理学的贡献在于他所收集的精致标本,他为此建立了一座病理解剖博物馆,并出版了许多铜版图谱以展示和讲解这些藏品。其中的骨骼藏品最为珍贵,这位看惯生命无常的荷兰老人为它们制作精美的版画,用以美化他的作品,画中骨骼姿势古雅,并配有哀伤的格言,如“生命之开端亦是死亡之起点 (nascentes morimur)”,这是每一位病理学家在日常观察中逃避不了的事实。
鲁谢的珍贵标本还包括慢性骨炎、骨肿瘤和其他异常,各种类型的结石,一个大的主动脉瘤(精美图片包含在《解剖学精要》中),狭窄性直肠肿瘤,肝硬化,胃癌,以及膀胱乳头状瘤(描述为“膀胱疥疮,有肉质腺状赘生物”)。
在法国,病理解剖学也同样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彼利埃的雷蒙德·德·维厄桑斯(Raymond de Vieussens,1641 – 1716)以“维厄桑斯瓣”及其他相关结构留名,他在丰富的尸检经验中取得了心脏病理学方面的重要发现(1715)。他清楚地描述了伴随尖瓣钙化和右心扩大的二尖瓣狭窄;记录了一个主动脉闭锁不全患者的准确临床症状,随后发现该患者主动脉瓣叶钙化。这两个病例他都强调了因阻塞导致的心脏血流瘀滞或被动充血。在第二个案例中,他还感觉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洪脉,“患者手臂动脉敲击我的指尖,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在震动”。这一发现启发了一个世纪后的科里根 (Corrigan)。
蒙彼利埃学院另一位著名毕业生,让·阿斯特吕克(Jean Astruc,1684 – 1766),是巴黎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历任法国和波兰国王的私人医生。他著有肿瘤和性病方面的重要论文,一部内容庞杂的《管道病理学》 (Tractus Pathologicus),以及一本关于女性疾病的著作。阿斯特吕克细致地区分了肿瘤类型,认为硬癌 (scirrhus) 由淋巴发展而来,通过体液增稠而发展成为癌症 (cancer) 。他焚化了一块乳腺癌和一片普通牛排,发现两种灰分的尖锐程度和刺激性并无区别,因此他认为自己推翻了恶性肿瘤是体液特殊毒性的表现这一古老理论。他区分了真正的肿瘤和囊肿,认为后者只是扩张了的淋巴。
当时的人们过分强调淋巴系统与癌症的关系,以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 – 1650)为首的一批人强调淋巴的热凝固性,淋巴自发凝固可导致癌症的观点盛行一时。为了支持淋巴理论,伟大的法国外科医生让·路易斯·帕蒂德(Jean-Louis Petit,1674 – 1750)呼吁人们特别关注癌症中的局部淋巴结增大,安东尼·路易斯(Antoine Louis,1723 – 1792)甚至根据淋巴凝结的方式区分癌症类型。同为巴黎外科医生的亨利·弗朗索瓦·勒·德朗(Henri Francois Le Dran,1685 – 1770)在癌症方面尤其有研究,他认为,不论多么仔细地切除肿瘤,癌症还是有复发的趋势,这是淋巴在根源上存在异常的有力证据。
阿斯特吕克关于性病的著作(1754)以对梅毒历史的论述著称,他将梅毒的起源追溯至美洲。书中对梅毒接触传染性的阐释非常精彩,关于硬下疳和疾病第二阶段的描述也十分详尽。他意识到后期的病变可发展至骨骼并可能涉及睾丸,却遗漏了主动脉和肝脏的典型病损。另一方面,他将所有的小病小痛也都归咎于系统中所谓的梅毒病毒,而这些疾病大都是心力衰竭等一般原因引起的。
《论心脏的结构、活动与疾病》(On the Structure of the Heart, and its Action and Diseases,1749)是当时最好的专著之一,作者是巴黎的让·巴蒂斯特·塞纳克(Jean-Baptiste Senac of Paris,1693 – 1770),路易十五 (Louise XV) 的医生。他注意到心脏病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认为心脏增大是一种最常见的小病。他使用了心脏动脉瘤一词,但并未区分心脏增大与肥大。他准确描述了心包炎,将其与肺部和纵隔膜的炎症联系起来,并意识到胸腹积水是循环障碍的表现。塞纳克对文献中记载的“绒毛心”、心脏中的石头和虫子等内容表示怀疑,认为心脏息肉形成于死亡当时。他考虑到脓液可从外部溃疡处回流进血液,这一观点实则包含了现代败血症概念的雏形,莫干尼却对此不以为然。
约瑟夫·吕托(Joseph Lieutaud,1703 – 1780)是巴黎学院的另一颗明星。他是普罗旺斯 (Provence) 人,求学于蒙彼利埃,1750年受塞纳克之邀来到凡尔赛宫,后来侍奉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 (Louis XVI) 两位国王。来到巴黎之前,他在常规解剖学研究方面已大有建树,在巴黎,他又根据自己的喜好展开病理解剖学研究。他将自己最有趣的解剖案例纳入著作《解剖学史》(Historia anatomica medica,1767)中,这部煌煌之作收集了过去文献中大量的尸检发现,可与博尼特的汇编相媲美。书中描述客观,但因过于简短而不具有效性;作为评论者的吕托相当缺乏批判精神,也没有考虑病因学。它是一座纸上博物馆,收集了三个世纪的材料,也是众多此类作品的最后一部。经波特尔 (Portal) 整理再版后,大概是今人了解十六到十八世纪尸检信息的最好来源。出于教学目的,吕托将疾病的症状与他认为常见的病理解剖基础并排列出(如中风-脑中液体),但过分的简化破坏了这一关联的实用价值。这是一部不朽著作,但在出版之日已然过时,因为莫干尼的《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已经问世了。
此时的意大利学院渐成强弩之末,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罗马的乔瓦尼·马里亚·朗契西(Giovanni Maria Lancisi,1654 – 1720)已与世长辞,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解剖学、病理学、医学和卫生学等多个领域的科学进步。他的两部著作,《论猝死》(On Sudden Death,1707)和《论心脏运动与动脉瘤》(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on Aneurysms,发行于1728年),为人们真正理解心脏病理学打下了基础。他区分了心脏肥大与扩张(“心脏动脉瘤”);形容增厚的瓣尖硬如软骨;第一次准确描述了瓣尖的疣状赘生物;将心脏扩张与梅毒联系起来(“高卢动脉瘤”);并认识到心脏变化与瓣膜狭窄及慢性肺部病变之间的关系。
朗契西也是一位优秀的流行病学家,他的同胞、同时期的贝尔纳迪诺·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1633 – 1714)在此领域同样成就卓著。拉马齐尼尤其关注工业中的危害,是最早呼吁人们注意职业粉尘对肺部有害作用的人之一。
而这一时期最无与伦比的伟大人物则是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干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1682 – 1771),自古以来,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宝座上群星璀璨,莫干尼则达到了这条星光大道的顶峰。莫干尼的老师是安东尼·马里亚·瓦尔萨尔瓦(Antonia Maria Valsalva,1666 – 1723),也是一位伟大的博洛尼亚解剖学家。可以绝对公正地说,莫干尼能够大有作为,成名成家,离不开瓦尔萨尔瓦本人对病理解剖学的准确诠释。莫干尼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对瓦尔萨尔瓦著作的编选也显示出对恩师的深挚敬意。在《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中,莫干尼坚持以瓦尔萨尔瓦的尸检案例开篇,而事实上,其中多例他都参与其中。
莫干尼生于罗马尼亚 (Romagna) 的福尔利 (Forli),毕业于博洛尼亚医学系,师从阿尔贝蒂尼 (Albertini) 与瓦尔萨尔瓦,后者迁往帕尔马 (Parma) 后,莫干尼继任博洛尼亚的解剖演示员。第一部重要作品《解剖学实录》 (Adversaria Anatomica) 出版后,他锋芒初现,于1712年调往帕多瓦大学,不久接任解剖研究室主任,在学校具有崇高的地位。任教、行政管理愈半世纪,他是最受欢迎的教师和备受崇敬的医学顾问,是贵族和威尼斯参议员的朋友、教皇的至交,获得了欧洲各国许多的科学荣誉。
伟大著作《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出版于莫干尼七十九岁高龄之时(1761年),是作者六十年充分观察与从容思考之集大成者。莫干尼一直活到九十岁,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它的数次重印。
早年学生时期,莫干尼就将临床症状与器官变化进行关联研究,这种思维方式保持下来,令他终身受益。泰奥菲尔·博尼特的伟大著作《尸检实践》是当时这方面的标准参考书,然而,莫干尼越深入研读越感到不满意,以至于最后他决定写出自己的观察以对它进行补充。意料之外的是,他抱着这样一种谦逊意愿写下的作品,结果却令《尸检实践》从此淡出历史舞台。这部著作以书信形式写就,对象是一位朋友,在他的激励下,莫干尼一共写了七十封信,在主题相关的各个方面,建立起常见疾病的症状与内在病理解剖特征之间的关联。后来这些信件被送还给莫干尼,经修整后出版,共计五册。
莫干尼是一名卓绝的拉丁语学家,语言风格引人入胜,即便写作科学内容也毫不失文采。他采用轻松有趣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报告主题,如“某个诚实的市民”、“一名善良而虔诚的处女”、“一位权势倾朝的国君”等等,读来妙趣横生;商人、律师、小偷、拦路的抢匪、牧师和修女、主教和王公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十分生动。但另一方面,他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即便在解剖室也坚守种姓差别,只有遇到十分特殊的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例如,他的书中记有如下案例:“帕多瓦妇女雅各巴 (Jacoba),安吉洛·扎纳尔迪 (Angelo Zanardi) 之妻。两边各十三条肋骨,我询问并记录了她的名字,对平民我一般是不会这么做的。”
而这部作品问世,立即使之前所有病理解剖学论著都黯然失色,关键在于它非常全面地建立了临床细节与尸检发现的关联。书中长篇累牍地记述病史,而不再只是点到即止;尸检结果的所有细节,作者都从容不迫地一一记录,丝毫不怕挑战读者的耐性。丰富的参考文献则显示出作者在该主题上的巨大阅读量。
现代病理学从莫干尼开始,这无可非议,但认为《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是一部现代化的作品却是错误的。它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病理学书籍,而是一部对病症进行相应解剖学解释的临床著作。其编排方式十分古老,按身体部位及其病症归类排列,同一患者的肾脏与胃部症状分别讨论,前后相隔百页。如需获取肿瘤病理学方面的信息,读者需要找遍书的每一节。显然这不见得是一个缺陷,然而莫干尼和他那些前辈一样容易犯错,他忽略了许多记录的重要意义,所强调的现象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关键病变却只是顺带提及。
在专科病理学方面,莫干尼的突出贡献是对血管系统病损的阐述。他的描述充满戏剧性,十分生动,读起来趣味无穷。中风显然是作者最感兴趣的主题。莫干尼的老师瓦尔萨尔瓦 (Valsalva)、瓦尔萨尔瓦的老师马尔皮基 (Malpighi),以及莫干尼的朋友拉马齐尼 (Ramazzini) 全都死于中风。他认同卫普菲和布伦纳所描述的脑血管小动脉瘤的影响,同时倾向于将脑室内出血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到脉络丛。他保留了浆液性和多血性中风的古老分类,前者的相关描述中可能包括了脑梗死、脑膜炎和尿毒症。书中有一个病例很明显是贫血性脑软化(“与腐烂的差别仅在于没有难闻的气味”),病变对侧身体麻痹。在他之前,瓦尔萨尔瓦对这种情形已有相当的了解。
动脉瘤的部分写得十分出色。莫干尼对这方面已有的大量文献了如指掌,客观描述上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他注意到古人不了解主动脉瘤的存在,“这种疾病直到十六世纪才为人所知”。他描写了数例因动脉瘤破裂导致的猝死,其中一例是一名妓女,她的主动脉“有的地方发白,这是骨化的先兆;有的地方出现小孔;还有的地方出现平行的纵纹”。半月瓣上方一英寸半处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动脉瘤,破裂后进入心包腔。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患升主动脉大动脉瘤的患者出现的各种心衰症状,包括咳嗽、呼吸困难、垂直的睡姿、心绞痛及其他。他声称,这些动脉瘤在向导、御马手和其他经常骑马的人群中最常发生,但另一方面他也同许多前辈一样,多次提及动脉瘤与梅毒之间的可能联系,这一联系现已得到普遍认可。
书中还描写了心脏破裂,但并未探讨其诱因。增殖性心内膜炎的描述非常精彩,其中一例是致命性淋病的并发症,记录十分详细。莫干尼相当关注性病,却没有从病原上区分淋病和梅毒。他也犯了一个常见错误,认为梅毒就是该病患者所有病损的罪魁祸首,声称“长期受梅毒折磨的患者,他们的肺、主动脉、肾脏及其附属器官,四部分都有损伤”。在另一段小结中,他断言:“如前所述,梅毒患者的肺常常受损,主动脉有时也受到侵害,扩张形成动脉瘤。”这里描写的肺部损伤有的显然是动脉瘤压迫主支气管造成的,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迁延性支气管肺炎。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断莫干尼有力地确定了梅毒是主动脉囊状动脉瘤的根源,或他认为梅毒是唯一甚至常见的诱因。世纪下半叶,科维沙 (Corvisart)、贝利和霍奇森 (Hodgson) 写下的关于心脏与主动脉病变的著作中,梅毒这一病因并未受到很多关注。
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到莫干尼的时代,大叶性肺炎这种常见病仍被人忽视,诊断不清。是莫干尼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某些病史的描述有的十分精湛,例如,一名帕多瓦修女“晚上突然发烧,先是寒战,全身冰冷,继而发热。间隔二十四小时后,除发烧外,另出现一侧胸痛、干咳及心跳加快。第七日患者死亡”。莫干尼非常有把握地认为:“尸体解剖将肯定能发现肺部呈肝脏样的实质性病变。”尸检的结果显示两肺重量增加而且质地变硬,外覆一层厚重的白膜,肺的切面呈现像肝脏组织一样的致密物质,充分证明了莫干尼的结论:“她的死因是肺部炎症。”(引用语来自本杰明·亚历山大 (Benjamin Alexander) 的翻译,伦敦,1769)。自此“肝样变”就成了描述这一解剖学画面的常用术语。
这部著作几乎谈及肉眼观察范围内病理解剖学的方方面面,且书中文本通常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就能转化为现代术语。 出版的记录中涵盖了约七百例尸检,多数出自莫干尼本人之手,其余来自瓦尔萨尔瓦及其他朋友。需要说明的是,莫干尼已掌握了传染的概念,极其小心的避免在感染环境中不必要的暴露。一名羊毛梳刷者的症状看起来很像肺炭疽,莫干尼克强制自己没有去打开他的胸腔;他坚持妓女的尸体必须放置一定时间后才能解剖;此外,与瓦尔萨尔瓦一样,他有意回避痨病死者的尸体。 相应地,肺结核的讨论成了这部作品的一块短板。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他曾无意中打开过肺结核死者的尸体,而至少有一个记录为肺结核的病例其实是转移瘤。与肺结核有关的材料大部分包含在“论咳血”一节中。
书中肿瘤病理学记录分散,但对胃癌、直肠癌和胰腺癌有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解释了胰腺癌难以在生前被发现的原因,并称赞了瓦尔萨尔瓦能够通过病史识别直肠癌的过人才智。书中提到了肾上腺 (“ren succenturiatus”) 肿瘤,另有些记录则可能指前列腺癌和食道癌。莫干尼并没有癌症转移的概念,但他描述的肝脏结节明显是继发性肿瘤。伴随腹水的卵巢囊肿描述也不少。他似乎见识过所有常见肿瘤。
书中其他的优秀描述包括:肝硬化,肾结石(当时肯定极其普遍),肾萎缩,输尿管狭窄导致的肾盂积水,以及确定无疑的伤寒热(“盲肠附近溃疡达两掌宽,局部淋巴腺肿大,脾脏肿大为正常大小的三倍。”他还补充:“我也经常见到其他的发热导致脾肿大”)。然而他对这些病变的解释有许多完全是依据体液学说空想出来的,从现代角度看常常匪夷所思。病因学一直都是病理学最薄弱的部分,在这方面莫干尼也未能继往开来,有所突破。
他对病理学无可估量的贡献在于强调细节和完整性,从不仓促做出结论。他未曾引进任何新方法,也几乎没有全新的发现,不像比沙和微尔啸那样给病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却在所能触及的每个领域完善了现有知识。莫干尼为病理解剖学建立的新标准如此之高,后来者再也不能马虎对待,草率行事了。
摩德纳 (Modena) 和帕维亚 (Pavia) 的安东尼奥·斯卡帕(Antonio Scarpa,1747 – 1832)是莫干尼最杰出的学生,他的股三角概念至今仍令医学新生头痛不已。在病理学上,他最显著的成就是动脉硬化方面的研究及对真假动脉瘤的区分(1804)。其他重要贡献涉及骨病理学与会阴疝。大约同时,约翰·亨特 (John Hunter)、哈勒 (Haller) 和桑迪福德 (Sandifort) 也都致力于阐明复杂的腹股沟疝,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坎珀(Pieter Camper,1722 – 89)则描述了坐骨疝。
另一名荷兰人,莱顿的爱德华·桑迪福德(Eduard Sandifort,1742 – 1814),在病理解剖学观察的广度上几乎可与莫干尼并列。他是伟大的解剖学插画家、莱顿的伯纳德·齐格弗里德·阿比努斯(Bernard Siegfried Albinus,1697 – 1770)的学生和接班人,将老师的方法运用到病理解剖学中,为莱顿博物馆增加了大量病理标本,并出版了一部内含精美插图的作品《病理解剖学观察》 (Observationes anatomicae-pathologicae)。其中的优秀记录包括溃疡性大动脉心内膜炎,心室间隔缺损,肾结石,几种疝气,骨关节强直及先天畸形。克吕韦耶 (Cruveilhier) 称他为“病理学图解之父”。他的同胞,阿姆斯特丹的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安德里亚斯·波恩(Andreas Bonn,1738 – 1818)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骨病理学专著,亦很有价值。
这段时期,解剖病理学基于大量的解剖学基础,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病理学的理论体系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就了一段灿烂而短暂的繁荣。这当中最著名的是哈雷 (Halle) 的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n,1660 – 1742)提出的“强直性”学说。在此理论中,原始的紧张与放松状态学说与新兴的医用物理哲学相结合,又加入了一种自脑膜开始循环的“神经力量”的特殊概念,维持人体机器的正常运行。缺少这种运动,身体就会腐化,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神经和血管系统的痉挛性收缩造成发热。该学说认为,这些异常状态许多都是由消化道最初的功能紊乱间接引起的,受这一假说激励,肠胃疾病成为研究热点,产生了不少具有永久价值的研究成果。
同样流行的另一个系统来自霍夫曼在哈雷大学的同事格奥尔格·斯塔尔(Georg Stahl,1660 – 1734),他的体系与冯·海尔蒙特的相似,其中的灵魂就相当于海尔蒙特的主元气。根据斯塔尔的理论,疾病的症状是灵魂保护身体对抗疾病的表现。当血液化脓的自然趋势发展到危及身体的程度,灵魂就会迅速提高循环和排泄速率,这个过程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发热。如果适当的循环不能实现,多血症就会发生,导致痛风、结石、黄疸等等。斯塔尔的“活力论 (Animism)”与霍夫曼的思想水火不容,两人难以和谐共处,最终斯塔尔去了柏林(1716),做了一名宫廷医生,直到人生终点。
这个世纪医学理论的泰斗是莱顿的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1668 – 1738),哈勒称他为“全欧洲的老师”。他的学生包括哈勒、高波 (Gaub),以及“老维也纳学院”的伟大领袖冯·施维腾 (van Swieten) 与德·哈恩 (de Haen)。布尔哈夫本人对科学的贡献当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提出的“化学亲和力”,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
与此同时,他也完全认可尸检的意义,并留有两例很有价值的验尸记录,都出自他本人的实践经历(Atrocis nec descripti prius morbi historia, 1723,与Atrocis rarissimique morbi historia altera, 1727)。两位患者都是贵族,所患疾病令人困惑,布尔哈夫反复强调只有通过尸检才有可能解开谜题,而他本人的崇高地位显然帮他轻易取得了死者家属的允许。第一例患者是瓦森纳男爵(Baron de Wassenaer,1723),尸检发现其食管破裂,开口进入两侧胸膜腔。第二例患者是圣奥尔本侯爵 (Marquis de St. Alban),他死于纵膈肿瘤,生前并未发现。
他的学生和在莱顿大学的继任者,杰罗姆·大卫·高波(Jerome David Gaub,1705 – 80)与他相似,以化学家的身份闻名,但同时也是《病理学总论》 (Institutiones Pathologiae Medicinalis) 的作者,对欧洲医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书当时的医学生几乎人手一本,读者数量大概一度远远超过了莫干尼的《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高波像注重疾病的体征一样关心“健康的征兆”,认为疾病是一种物质实体,每一种特定疾病都有其独特的诱发状态,他称之为“致病的种子”。如此高度揣测性的前提自然无法成为进步的基石,盛行一时的高波病理学总论在他死后很快被人们遗忘。
这个时候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世纪前,加里森曾提出重视的应激现象在生理学中的重要地位。莱顿学院最著名的学生,伯尔尼 (Bern) 的阿尔布雷赫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 – 1777),以他在哥廷根 (Göttingen) 深入而详细的实验工作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肌肉应激与神经刺激的现代概念。在哥廷根的这些年也是他科学工作的黄金阶段。这位杰出的生理学家在植物学和解剖学领域几乎同样著名,他没有因工作的繁重而舍弃病理解剖学研究,这个世纪其他许多伟大的系统医学家也都如此。哈勒的观察结果包含在他的《小歌剧》 (Opera minora) 和《病理学小品》 (Opuscula Pathologica) 中。《小歌剧》中的《妖怪》 (De Monstris) 一篇包含了畸形学的很多优秀内容;《病理学小品》则简要客观地记录了他本人进行的有意思的尸检,作品覆盖的病理解剖学范围很广,但基本没有为该学科增加新内容。
应激现象并未得到深入钻研,但却成为苏格兰医生约翰·布朗(John Brown,1735 – 1788)医学哲学的基础。布朗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是一名自大的天才,他肆无忌惮的行为在本国遭到冷遇,在国外却得到惊人的赏识。在美国,本杰明·拉什 (Benjamin Rush) 信奉他的体系;在法国,他的理论受到国民公会的关注;在德国和奥地利,“布朗主义”都有大批追随者。布朗医学体系非常简单,不考虑医学细节的体系其实都有此倾向。简言之,“兴奋性”是生命的控制因素,适度的兴奋意味着健康,过多或不足则导致疾病,应相应地针对具体情况调节兴奋刺激物予以治疗。 如果刺激过于强烈而丧失兴奋性,或太微弱而无法激起兴奋,则个体死亡。这个系统就这样包罗了健康和疾病的所有问题,虽然现在看来异想天开,经不起事实考验,不值得认真对待,在当时却极度盛行,自提出后经过一代时间仍具有重要影响力,以至于布鲁赛 (Broussais) 将它翻新重塑,推向了荒谬的新高度。
这些就是莫干尼在欧洲医学界的竞争者,必须承认这些肤浅的理论家在当时其实更受欢迎。一直到唯物主义的法国大革命之后,病理解剖学得到迅速发展,莫干尼留下的宝藏才发挥出巨大的价值。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2-23 08:33:49 编辑
十八世纪伟大的荷兰与意大利学院的解剖学已到达巅峰。大体解剖学的工作已基本完成,而宏观病理学则保持全速前进,任重道远。然而,已有病理专家崭露头角,两个法国人维厄桑斯 (Vieussens) 和塞纳克 (Senac)、以及意大利的朗契西 (Lancisi) 都出版了心脏疾病方面的重要专著。首先应该提及的是这个世纪的重要人物莫干尼,他的经验涉及病理解剖学的各个领域。这些经验被他记录下来,公之于众,成为医学界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另一方面,医学理论仍局限在推测性的模式里,霍夫曼 (Hoffmann)、斯塔尔 (Stahl)、高波 (Gaub) 和布朗 (Brown) 等人的学说昙花一现;布尔哈夫 (Boerhaave) 与哈勒 (Haller) 的体系较为成功,但也仅仅接触到真实世界的一角。
法国大革命革故鼎新,旧的医学院被废除,教员被遣散,“自由”的医学协会替代了饱受谴责的“皇家”学会。新的、坚定的唯物主义强调分析性观察,坚决主张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很快带领法国走到了科学世界的前沿。在所有科学当中,疾病研究受到了最大的推动,法国接替意大利,成为克吕韦耶 (Cruveilhier) 所说的“病理解剖学的沃土”。
在传染病横行的时代,医院里的高死亡率为病理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巴黎最古老的主宫医院 (Hôtel Dieu) 成了疫病的温床,1788年雅各布斯·勒内·特农 (Jacobus-René Tenon) 出版了关于巴黎医院的报告,指出医院里拥挤得无法描述,大多数患者四到六人挤在一张床上,另有成百的病人就躺在过道里肮脏的草垫子上。外科和产科病房散发着脓液和坏疽肉的恶臭,传染病患者未能得到适当隔离,丹毒在各医院疯狂蔓延。
基于这种情况,到十九世纪初,即使不能说疾病的理解已达到新的高度,至少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症状与内在的器官变化之间的关联。整个医学教育界呈现出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场景。天刚破晓,老师和学生已出现在病房;深夜,学生仍继续着一天的工作,在卧室里解剖白天尸检取得的难闻标本。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临床教师担负着照顾病人、临床教学与细致的尸检三项重任,在高强度的研究中透支着自己的精力。以这种方式引领病理学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弗朗科斯·泽维尔·比沙 (François-Xavier Bichat) 和勒内·泰奥菲尔·亚森特·雷奈克 (René-Théophile-Hyacinthe Laënnec),两人的寿命加起来只有七十六岁。
他们的老师分别是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 – 1826)和让·尼古拉斯·科维沙(Jean-Nicolas Corvisart,1755 – 1821),两位都是十八世纪后期巴黎学院的伟大教师。皮内尔是一位杰出的分类学家,他的《疾病分类哲学论》 (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 当时极受欢迎,如今的名望则主要来源于他对精神病患者治疗方法的改革。他将内部疾病有条理地标注为六大类,涵盖了二十一个目和八十四个属。这一分类存在的时间很短,它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启发了比沙,若非如此,它恐怕难以流传至今。皮内尔将炎症按组织类型分为(1)皮肤,(2)黏膜,(3)浆膜,(4)结缔组织,及(5)肌肉和关节炎症。这是人们首次尝试说明特定组织类型所患疾病的相似性,以此为开端,比沙开创了组织病理学,籍以和大体解剖学相区别。
科维沙作为临床教师更加了不起,拥有更多优秀的嫡系学生,其中以雷奈克最为著名。科维沙将物理诊断作为医学实践的基石,他的教学和示范将奥恩布鲁格 (Auenbrugger) 与雷奈克连接了起来:前者关于叩诊法的书是他翻译的,而后者使胸部病损的物理诊断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除译作外,科维沙本人出版的作品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论心脏与大血管的疾病和器质性损伤》(Essay on the Diseases and Organic Lesions of the Heart and Great Vessels,1806)。在这本书中,他将心脏“动脉瘤”分为“主动”性扩张伴肥大,和“被动”性的扩张无肥大两种。他深入讨论了主动脉瘤及其成因,却未提到梅毒;而另一方面,他认为梅毒对心脏瓣膜疣状赘生物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1793年,大革命的一段小插曲将马里亚·弗朗科斯·泽维尔·比沙(1771 – 1802)带到了巴黎,在首都的八年,他将组织学应用到病理学领域,这期间的工作确立了他在病理学中的地位,使他与莫干尼和微尔啸并称现代病理学的三大创始人。比沙生于法国图瓦雷特 (Thoirette),1791年开始在里昂 (Lyons) 跟随马克·安东尼·帕蒂德 (Marc Antoine Petit) 学习医学,很快就成为他的助手。1793年,因为大革命的缘故比沙开始服兵役,但由于厌烦一名多事的军官,他仓促离家,不久即放弃当兵,来到巴黎,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皮埃尔·约瑟夫·德索(Pierre-Joseph Desault,1744 – 95)最喜爱的学生、亲密的朋友、同事,最后继承了导师的学术衣钵。德索过世后,比沙虽然完成并编校了恩师尚未写完的外科论著,但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医学的基础分支——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上。
受皮内尔作品的启发,他开展研究,写下了著名的《论膜系统》(Treatise on Membranes,1799 – 1800),因为这部作品,他被今人视作组织学的创始人。比沙勤奋异常,他唯一的放松就是更换工作内容,即使疾病缠身也不曾懈怠。首批作品出版后,在肩负教学和行医双重重担的情况下,仍以极快的速度接连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其中《生命与死亡的生理学研究》(Physiological Researches on Life and Death,1800)与《论膜系统》同样闻名,巨著《大体解剖学》(General Anatomy,1801 – 1802)是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之一,《描述解剖学》 (Descriptive Anatomy) 在他过世后由他的同事完成。整个工作期间,比沙一直受结核病折磨,最终于1802年,在度过备受煎熬的一天后与世长辞,死因疑似某种类型的脑膜炎。贝克拉德 (Béclard) 称,解剖完一具极其令人作呕的标本后,比沙倒在主宫医院的台阶上,不省人事,“之后很快发生严重的头部感染、剧烈的胃部反应、频繁的昏迷和共济失调症状,比沙死于发病后第十四天”,享年三十一岁。他可能是结核性脑膜炎的受害者,这种疾病的解剖学基础直到1830年帕培凡尼 (Papavoine) 发现结核性蛛网膜炎 (arachnitis tuberculeuse) 才被人们所知。
值得庆幸的是,他已将信息传达给了科学界。他毫不犹豫地将解剖结构的理念运用到病理学中,并清楚地认识到它将对科学界产生的影响。他宣告,“我们越多地研究人体,就越会相信,我们不应从复合器官的角度来考虑局部疾病,而应从它们的不同结构出发,因为器官很少整体受损,不同的组织结构几乎总是出现不同的病变。”
这种关于身体组织结构的划分令比沙名流千古,这一伟大的创举部分来自于化学的独创性类比。他在《大体解剖学》中写道:“所有的动物都是不同器官的组合体,这些器官各自行使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以维持整体的运行。器官又由多种不同的组织构成,这些组织才是器官的真正组成元素。就像化学中的简单元素结合形成化合物,解剖学中也有简单组织,它们组合起来构成器官。”接着他继续区分了二十一种组织,包括神经、“多孔”或结缔组织(该组织遇空气膨胀,形成多孔结构,由此得名)、血管、肌肉、骨、软骨、吸收性组织、腺体、皮肤及其他组织。整个分类过程中他并未使用显微镜,只是用精微的工具手工解剖,或如他所说,“通过各种化学试剂或方法处理组织,如热、空气、水、酸、碱、盐、干燥、浸渍、腐化、煮沸等,精确固定每种器官的组织。”
他的所有概念以功能为基础,依托于一个宏大的活力论体系。与巴拉塞瑟苏斯和冯·海尔蒙特不同,比沙并不是一名在黑暗中摸索的神秘主义者,他为他所界定的每一种组织赋予特定的活性或不同的活力,认为它们有各自的敏感性和收缩性。这些活力要素维系生命和健康,如果衰竭则导致疾病和死亡:“La vie est l’ensemble des propriétés vitals qui resistant aux propriétés physiques, ou bien est l’ensemble des functions qui résistent à la mort.”
《描述解剖学》前言中比沙的箴言令人难忘,或许恰好可以充当他的墓志铭:“解剖之于解剖学,犹如实验之于生理学,追踪疾病的过程和尸检之于医学;如果不经过这三重路径,就无法成就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医生。”
比沙最后讲授的一门课程是病理解剖学,与此相关的记录来自他的忠实信徒、解剖学家贝克拉德的手稿,而这一手稿大概又是由该课程一名学生的笔记转录而来。这些课程对病理解剖学已有知识的描述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至今仍能令人眼前一亮,但辗转誊抄的记录并不能代表比沙本人,《大体解剖学》的广博知识与思想精髓在粗糙的转录过程中遗失,学生的笔记本无法再现大师当年的风采。手稿内容显示出对多种病理损伤的理解,但比沙的专科病理学毫无疑问远比这些内容更加丰富和准确。这本书尽管细节严重不足,好在能够反映比沙对该主题的整体构思,从这个角度来说仍颇有价值。但我们终究不能以专科病理学来评判比沙的功绩,是他的组织与组织变化学说架起一座桥梁,将莫干尼和更早的前辈与今天的细胞病理学连接了起来。
专科病理学的主要问题当中,肺结核受到了法国学院的特殊关注。科维沙 (Corvisart) 的两名学生,加斯帕尔·劳伦·贝耳(Gaspard-Laurent Bayle,1774 – 1816)和雷奈克都极大地促进了该病的理解,两人本身都是痨病患者。贝耳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和尸检调查,选取了五十四个案例着重记录,在1810年出版了《肺结核研究》 (Investigations on Pulmonary Phthisis)。他区分了六种肺痨,其中慢性溃疡性结核明显最为普遍,其他五种肺病(及对应的现代名称)为:“颗粒型”(粟粒型肺结核),“黑变型”(煤肺病),“溃疡型”(肺脓肿与坏疽),“结石型”(包覆的钙化结核),以及“癌变型”(真性肿瘤)。他改进了之前关于结核结节及其与结核空洞之间关系的所有描述,并强调了慢性溃疡性肺结核与其他器官结核的相关性,如喉部、肠道与肠系膜淋巴结。当时人们普遍将肺结核看作斑疹伤寒、急性肺病、梅毒或心脏病的后遗症,但贝耳仍极力主张这是一种独立的病变,是个体对结核病的易感性的结果。
贝耳之后的勒内·泰奥菲尔·亚森特·雷奈克(1781 – 1826)在此领域更加声名显赫,他是著名的听诊器的发明者,不仅在结核病方面成就斐然,而且使整个肺病理学科焕然一新。雷奈克是不列塔尼 (Brittany) 人,十四岁即成为南斯大学 (Nantes) 的医学生,二十岁已是巴黎知名人士。当时巴黎最杰出的教师是夏里特医院 (Charité) 的科维沙和萨尔贝蒂耶医院 (Salpêtrière) 的皮内尔,雷奈克加入了科维沙和他的年轻助手贝耳的团队。他还学习了比沙的课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曾是解剖学家、外科医生迪皮特朗 (Dupuytren)的学生,但两人后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心脏二尖瓣的“骨化”,之后他继续把主要兴趣放在胸部疾病的研究方面,成为这方面公认的权威。1819年出版的伟大著作《间接听诊》 (Mediate Auscultation) 被称为最有影响力的诊断学书籍,该书不久后修订为《论胸部疾病》 (Treatise on Diseases of the Chest),这两部作品连同他发表在《医学词典》 (Dictionary of Medical Sciences) 上的论文,包含了他的大部分研究精华,确立了他在病理学中的永久地位。和比沙一样,他拒绝因为生病而放下工作,这样不知疲倦的辛劳终究不敌痨病的侵蚀,他在1826年与世长辞。雷奈克的一生是勤勉和奉献的一生,古往今来的医生都难以望其项背。
除了肺结核方面的卓越贡献,雷奈克对其他疾病也有精彩绝伦的描述,包括肺气肿、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水肿、肺坏疽与梗死(肺“中风”),以及肺包虫囊肿。其后的肺病理学与诊断中使用的大部分术语都来自于他,许多一直沿用到今天。在肺部癌症方面,他的教学是当时最先进的,虽然使用了“变性 (degeneration)”这一说法,但实际是指病理组织取代了正常组织。他在各个领域实践了比沙关于组织特异性的观念,指出前人十分重视的“硬”癌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坚硬癌症类型或早期癌症,而是多种因含有大量结缔组织而质地坚实的癌症。他沿用了贝耳对其他癌症中松软的脑样物质的命名---encephaloid, matière cérébriforme,这一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广泛使用。贝耳和雷奈克都认为两器官同时发生癌症,如胃部和肝脏,是癌症易发体质的证据。
雷奈克对病理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开了结核病之谜。他认同贝耳的观点,相信结核结节并非已经存在的炎症产生的后果,但认为贝耳依然没有或很少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雷奈克跟踪结节变化的各个阶段,从微小的灰色颗粒样病变,到较大的结节、经干酪样坏死,直至最后的空洞,证明了这些不同形态病变的相同本质。他在结核病中引入了单元的概念,即结节,并认识到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演化与分期。与贝耳类似,他认为结核病是先天体质缺陷的结果。
雷奈克关于心脏的论著是对科维沙工作的必要补充,同样很值得关注。他在详细研读以往文献后写下此书,透彻理解了博尼特、莫干尼、哈勒、派尔 (Peyer)、塞纳克及其他人对该主题的论述。需要注意的是,雷奈克也是一名学者和颇有造诣的医史学家。由于完全无法与梅毒的其他迹象建立联系,他并不接受科维沙关于心内膜炎疣状赘生物来源于性病的观点,认为它们是排列有序的“息肉”。他极好地描述了主动脉瘤,准确区分了主动脉弓的囊性瘤和腹主动脉扩张所形成的动脉瘤,但都未论及病因。
科维沙的另一名学生、雷奈克的仰慕者、伟大的皮埃尔·布雷托诺(Pierre Bretonneau,1771 – 1862)对白喉研究的贡献几乎等同于雷奈克在结核病方面的成就,该病现在的名称diphtheria也来自于他。之前对白喉描述最好的是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John Fothergill,1712 – 1780)。布雷托诺意识到白喉具有极大的毒性,评论“病变与其致命后果的不对等”是病理解剖学薄弱之处的反映。他在伤寒热 (dothienenteritis) 方面的贡献亦毫不逊色,将损伤定位于肠道集合淋巴结,并提出该病属传染性疾病。
但法国对伤寒热最有研究的当数临床医生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路易斯(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1787 – 1872),他和当时其他伟大的临床医生一样,多年来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大部分花费在病房和验尸房。通过他的美国学生,路易斯对美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城 (Philadelphia) 的格哈德(W. W. Gerhard of Philadelphia,1809 – 72)正是其中之一,他最终将伤寒热与具有相似症状的常见病斑疹伤寒区别开来。其大致观点是,两种疾病中的一种常有导致小肠溃疡的趋势,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格哈德跟随路易斯学习两年后返回费城,此时,路易斯已发表了不朽的系列论文《伤寒感染或伤寒热研究》(Researches on the Typhoid Affection or Fever,1828),格哈德在费城医院发现了多例同样的感染性疾病,随后他任职于此,并在三年后积极参与了1836年宾夕法尼亚州斑疹伤寒大流行的控制工作。在完成214个病例的研究之后,他确信他的研究对象与路易斯报告中导致肠道溃疡的疾病有很大不同,他的观点一经发表几乎立刻就在国外获得了认可。
路易斯引进了一种调查疾病的新方法,即大量病例的统计研究。很难相信这种价值不言而喻的方法最初竟因新颖而受到嘲讽。格哈德在一封信中写道,路易斯“结果推算过程的数学精确度不同寻常”,但又补充他“并不是个聪明人,智力上不如他在彼爱特医院 (La Pieté) 的同事安德拉 (Andral)”。在建立结核症状与尸检中发现的器官变化之间的联系时,路易斯尤其出色地运用了这种统计方法。
格哈德还用他精炼的笔触描写了当时巴黎医学界的泰斗弗朗西斯·约瑟夫·维克多·布鲁赛(Françis-Joseph-Victor Broussais,1772 – 1838),在格哈德笔下,布鲁赛是“巴黎最著名的医生,名满天下,对医学裨益极大,但作为讲师却令人难以忍受”。虽著有一本病理学概论,但因观点过于片面而影响式微。布鲁赛认为肠胃炎是所有发热和大多数其他疾病的根源,反对当时风头正劲的约翰·布朗的哲学,以临床观察为基础辩称一种疾病可以产生亢奋与虚弱两种状态。但在疗法上他的影响则完全是有害无益的,他的理论将放血和水蛭吸血法推向了空前绝后的盛行程度。
加布里埃尔·安德拉(Gabriel Andral,1797 – 1876)是布鲁赛之后巴黎大学普通病理学和治疗学主任教授职位的继任者,放血疗法的流行为他的血液成分研究创造了条件,这一研究意义非凡。与让·巴蒂斯特·杜马 (Jean-Baptiste Dumas) 和朱尔斯·加瓦利特 (Jules Gavarret) 两位化学家的交往为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援助。遵循杜马的方法和建议,安德拉和他的化学同事分析了多种不同病理状态的血液中细胞、纤维蛋白和血清固体的比例。他们的数据现已没有使用价值,不像理查德·布莱特 (Richard Bright) 的同事博斯托克 (Bostock) 早先发表的肾炎研究结果那样影响深远,但这一工作将贫血、包括原发性(自发)和继发性贫血与严重或持续出血区别开来,这一点特别重要。安德拉还发现铅中毒也是贫血的诱因之一。当时诊断贫血的依据是血细胞总体积的减小,而不是如今采用的细胞计数。
安德拉意识到发烧病人的血纤维蛋白含量通常是下降的,并认为这是发热状态下脾脏肿大和软化的原因,但他同时也强调了现已尽人皆知的现象,即肺炎患者血液的情况刚好相反。他注意到,有出血倾向的疾病患者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含量较低,如坏血病和斑疹伤寒。这一工作通过反复测量正常人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含量对这一研究实现了严格的对照,被誉为血液化学领域第一次重要的深入研究,尽管作者细心地引用了前人这方面的工作成果。安德拉并未将注意力局限于血液学,还著有许多被广泛使用的常规病理学教科书。
尽管巴黎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在病理解剖学上下的功夫更多,但第一个专门设置该学科教职的却是法国阿尔萨斯省 (Alsace) 的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任职者约翰·马丁·罗伯斯坦(Johann Martin Lobstein,1777 – 1835)是德国吉森 (Giessen) 人。他在解剖学和产科学上的成功及观点获得了伟大的法国比较解剖学家居维叶 (Cuvier) 的赏识,居维叶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本人所在的学科领域,他建议为罗伯斯坦设置病理解剖学教授一职。由此获得的资源使罗伯斯坦得以着手绘制一本富有个人观察的图谱,但最终未能完成。而更重要的是,他独创了一种新的病理损伤分类法,依据病变的解剖学特征而不是位置,这种方法令后来的罗基斯坦斯基 (Rokistansky) 深受启迪。
而巴黎病理解剖学教职的最终设立则要归功于能干但坏脾气的外科医生纪尧姆·迪皮特朗(Guillaume Dupuytren,1777 – 1835)的远见卓识。迪皮特朗是巴黎主宫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比沙的学生,同时也对病理学充满热情。他详细描述了骨折、脱位和挛缩,由此在外科病理学史上获得了突出地位。大量的行医实践令他累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其中一部分遗赠为病理学研究基金。
这一新的教职在1836年被授予迪皮特朗的学生、时任巴黎大学解剖学教授的让·克吕韦耶(Jean Cruveilhier ,1791 – 1873)。有趣的是,一生八十二年目睹了好几千例尸检的克吕韦耶在第一次见识到这一场景时被吓坏了,一度退出了才开始不久的医学学业,回到了最初爱好的教堂工作,甚至上了神学院以接受必要的培训。但他那做医生的父亲很快将他带回了医学界,之后他就没再当逃兵了。1816年他从巴黎大学毕业,论文题为《论大体病理解剖学与特定的器官变化及其结果》 (Essay on pathological anatomy in general, and organic transformations and productions in particular),这项研究对初学者来说算是雄心勃勃了。
1814年初他在主宫医院实习时正值拿破仑孤注一掷,倾法国之力与欧洲进行对抗的黑暗岁月。克吕韦耶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医院的情形。主宫医院挤满伤兵,他就在这里逐渐形成关于炎症的著名观点,虽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六个多月了,所有伤口无一例外全部发生坏疽,甚至最轻微和即将愈合的也未能幸免。”他补充了一个“显著的事实”,当坏疽肆虐外科病房时,斑疹伤寒横扫了整个医院,以至于他只能相信有某种毒瘴在蔓延。
行医几年并短暂担任蒙彼利埃大学的外科教授之后,他于1825年回到巴黎大学,接替贝克拉德成为系统解剖学教授。1836年他改任新设立的病理解剖学教授一职,同时担任数家医院的首席医生,包括妇产医院 (Maternité)、萨尔贝蒂耶医院和夏里特医院,在大量尸检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病理学理论。
巴黎任职早期,他着手进行的一项工作令他留名至今——精美的平版印刷图册出版了,如他所说:“为了填补学科空缺,让病理解剖学流行起来,使学生有一个可靠的参照标准。”第一册在1829到1835年间出版,第二册从1935到1942年。图册的平板印刷主要是沙扎尔 (Chazal) 的功劳,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常规解剖学插图画家,客观真实地再现了重要的、当时大概已被理解的细节,令这些图画直到现在仍具有价值。
克吕韦耶青年时期形成的病理学观念在他事业成熟后仍然起主导作用。这一观念是,组织本身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只是容易受到营养增减的影响,所有显著的组织结构器质性变化都仅仅是细胞组织间隙病态分泌的表现,这种病态分泌与正常分泌相对应,产生于异常亢奋的毛细血管床。1849至1864年间分五册出版的伟大著作《大体病理解剖学论》 (Treatise on General Pathological Anatomy) 最重要的部分大都建立在这一学说之上,也正是基于该学说,他成功提出炎症理论,一时受到热议,直至被微尔啸彻底推翻。
在他看来,炎症的特征是充血伴毛细血管瘀滞,以及毛细血管自身的病态分泌,分泌物可能是可凝性淋巴、脓汁、干酪样物质或其他。继发特征则包括炎症部位体积的增大及密度或粘稠度的明显变化。他认为炎症是最常见的病理变化,组织的炎性变化与生命状态密不可分。他声称:“受到刺激而不发生炎症反应的组织,不论内部还是外部,总而言之所有不易发炎的组织,都是没有生命的。”炎症的首发部位是毛细血管床,他认为这实际是静脉系统的一部分,而静脉的炎症,或静脉炎,在他的观念中是地位最重要的。1837年在《医学和实用外科学词典》 (Dictionary of Medicine and Practical Surgery) 上发表的关于该主题的文章中,他坦言“在某种程度上静脉炎主导了整个病理学 (La phlebite domine en quelque sorte la pathologie tout entière)”,认为它是“依靠直觉的古代体液学说和理性的现代体液学说之间的衔接点”。
尽管他区分了粘连性静脉炎(或血栓形成)和化脓性静脉炎(这种可怕的疾病伴随着他在主宫医院的楼阁间长大),却未能深入研究它的概念中包含的可能性,没有发现栓塞的存在,也没有对脓血症提出解释。他的学说总体上不可取,但它让克吕韦耶认识到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炎症,这一观点之前一直不被接受。而在癌症方面,他再次跑偏,提出了一种致癌液,它进入血液并渗透到不同器官的组织中。不过这可能是细胞病理学和栓塞学说出现以前对癌症转移现象的最好解释。
同时期也有很多优秀的专科病理学专著出版。皮埃尔·弗朗西斯·奥利弗·拉耶(Pierre-François-Olive Rayer,1793 – 1867)著有两部配有文本的重要图谱和一本著名的人鼻疽病专题论文。第一部图谱主题为皮肤病(1826 – 27),第二部配有三册肾病专论(1837 – 41),出版于布莱特(Bright)的经典著作问世十年之后,这部伟大作品首次强调了详细分析尿液对于肾病诊断的重要性,作者还十分关注沉积物以及脓液的显微镜检查。论文第三册讨论肾盂炎,拉耶对这一疾病的病因大都十分熟悉。著作大量引用了古人的作品和观点,反映出他强烈的史学天分。拉耶作为第一部《病理学史》 (History of Pathology) 的作者而被人们记住,这是他1815年的论文。
法国曾出现不少伟大的心脏病专著作者,包括维厄桑斯、塞纳克和科维沙,而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Bouillaud,1796 – 1881)不辱使命,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他认为发热的原因是心内膜炎,同雷奈克一样反对科维沙关于梅毒导致心脏瓣膜疣状赘生物的观点,发现这一症状在其他人群中比在梅毒患者中更常见。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愿意否认梅毒对大血管的影响”,谨慎小心地强调梅毒可能是主动脉炎的一个诱因。他很好地描述了心瓣膜口狭窄,但对病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认识到风湿病与心脏病之间的关联,这一发现在他的《关节风湿症及其与心脏炎症同时发生之规律的临床研究》(Clinical treatise on articular rheumatism and the law of coincidence of inflammations of the heart with this disease,1840)中首次报道。另外,他和另一名法国人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1824 – 80)同时最早提出了大脑额叶损伤是失语症的一个原因。
出生于美国的法国人菲利普·里考德(Philip Ricord,1799 – 1889)父母是巴尔地摩 (Baltimore) 居民,他在性病这一疑难问题的解决上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受约翰·亨特(John Hunter,下章介绍)误导,保守的欧洲医生几乎已经接受了淋菌性阴道炎与硬下疳是由同一病原菌引起的观点,尽管这两种病损并不一样。然而,永不满足的年轻人,尤其是一往无前的医学生仍然不辞劳苦地用亨特的方法互相接种淋病的浓汁和梅毒性下疳的血清,出于诊断目的或作为治疗方法,在梅毒和其他疾病研究中进行的下疳接种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理论是,这两种疾病可能“被迫融合”,然后通过梅毒的特殊汞剂疗法一起被迅速消除。在巴黎,勤奋异常又拥有敏锐观察力的里考德整合了这些试验的记录,辅以他本着科学的精神和对父母的担忧所进行的大量接种实践,终于无可争辩地分离了这两种疾病。同时,他根据再次接种遇到的困难建立了一些免疫学法则,而他的描述极大地促成了现在的梅毒三阶段的分类。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3-04 11:34:27 编辑
如上章所述,大革命后,法国病理学大踏步前进,而此时的英国也几乎独立地展开了病理学研究,成果同样丰硕。亨特(Hunter)兄弟建立了英国最早的病理学博物馆,他们的外甥马修·贝利 (Matthew Baillie) 出版了第一本图谱,时代的大幕自此拉开。
当然,在他们之前,塞缪尔·戈洛斯(Samuel Glossy,1763)和理查德·布朗·切斯顿(Richard Browne Cheston,1766)等少数医生已出版论述与疾病相关的病理解剖学变化的著作,约翰·福瑟吉尔 (John Fothergill) 第一个对白喉进行了权威的描述,而圣巴瑟洛缪医院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更是人才辈出,它的荣耀仅逊色于后来的盖伊医院 (Guy’s Hospital)。这其中有最早发表心绞痛临床描述(1768年)的威廉·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1710 – 1801),还有著名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Percival Pott,1714 – 88),由于他对脊柱强直性弯曲原创性研究的突出贡献(1779),这种疾病被称为“波特病(Pott’s disease)”。
事实上波特并未发现这一疾病的结核性本质,他对病变可能导致的麻痹和畸形的关注超过了对病变原因的研究。最终确定该病由结核引起的是蒙彼利埃的法国骨科医生雅克·马蒂厄·德尔佩什(Jacques-Mathieu Delpech,1777 – 1832)。波特的重要成就还包括直肠和睾丸疾病研究,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腓骨骨折,他本人也曾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
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1718 – 1783)生于格拉斯哥 (Glascow) 附近的拉纳克郡 (Lanarkshire),是门罗一世 (Monro primus) 的学生、威廉·卡伦 (William Cullen) 的挚友,在医学生涯之初就是一位技术娴熟、见多识广的解剖学家。他最开始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在伦敦行医,但很快专攻产科学,并最终在此领域扬名立万。当时伦敦还没有正式的医学院校,学生们参加名人开设的私人课程,亨特是当地的名师,桃李满天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亲弟弟约翰。约翰于1748年从拉纳克郡来到伦敦协助威廉。后来二人因共同作品的功劳归属问题产生争论并长期分离,令人唏嘘。兄弟俩的个性天差地别,威廉优雅内敛,约翰直率暴躁,在科学上却有着相同的品味。两人都是常规和病理解剖学名师,终生收集标本以作教学之用,且都建立了成为学界标准的病理解剖学博物馆。不同的是,约翰坚持以实验支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比他的哥哥更有造诣,常被誉为第一位伟大的实验病理学家。
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 – 93)是父亲老年所得之子,受母亲溺爱,从一开始就反对传统和常规教学。他自由发展,但并不游手好闲,迷上了收集博物学标本,这一爱好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二十岁时他来到伦敦,跟随哥哥威廉开始了医学工作,能力立刻便突显出来。不久他接管了威廉的解剖室,之后成为他的助手。他不时在切斯尔顿 (Cheselden) 和波特等顶尖的外科医生手下进行短期实习,为后来的外科实践打下了技术基础,也曾下功夫接受牛津的文化熏陶,但持续不长,高高在上的古典课程最终没能打动他那独立的、充满质疑精神的灵魂。
与威廉分开后,约翰分别在伦敦和乡下自立门户。他将除手术和会诊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收集标本上,城里的房子很快变成博物馆,而乡下的庄园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他对科学无比执着,看中的任何标本,不论死活,都必须尽收囊中。他从正在进行的葬礼中成功窃取了一位著名巨人的尸体,也曾自掏腰包资助北极探险队将他的海洋标本从格陵兰岛带回。1760年,他接受了七年战争中的一个职位,成为贝尔岛 (Belle Isle) 远征军中的外科医生。军队攻占堡垒期间,他抽时间写下了对炎症的看法,但至今没有发表,如他所料,这些观点被他教过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发明提了出来。贝尔岛战役为他提供了机会和材料,使他得以检验炎症方面的想法,并完成关于枪伤的著名论文。
相比于天赋的聪颖,亨特的巨大成就更多出自他无止尽的勤奋。他的日常安排简直令闻者心酸:六点起床,例行解剖到九点,早餐后在家看病到中午,之后外出会诊忙到四点才进正餐,休息一小时后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不辞劳苦地进行动物实验或写作,直到凌晨两点。就是在这样夜以继日的辛劳中,他完成了关于血液和炎症的两部重量级病理学论著和一部性病专著,前者经过完善后与他的枪伤研究一起出版为《论血液、炎症和枪伤》(A Treatise on the Blood, Inflammation and Gun-shot Wounds,1794,出版时作者已故),后者在1786年出版为《论性病》 (A Treatise on Venereal Disease)。
与达尔文之前的许多著名生物学家一样,亨特是一名狂热的目的论者,认为自然的演化几乎都是有意为之,这一观念对他的炎症研究影响深不可测。“血液之生命”的概念主导了他的整体思想,它的产生来自于血液显著的抗腐败作用和凝结能力,凝血作用常能有效控制出血,而经血为了实现特定的功能并不凝结的现象也没能逃过他的法眼。有人质疑他的理论,理由是将血液冷冻、破坏其“生命”后,它仍具有凝结能力,为此亨特特地冷冻了一块肌肉,并证明它仍能收缩以论证自己的理论。
他对炎症的看法也是这种观念的自然产物。亨特认为炎症从本质上看首先是一种防御机制,其次是一个修复过程。他将炎症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粘连型,并以胸膜炎为例说明了这类炎症对身体的益处:纤维性粘连将炎症包裹在局部,随后该部组织形成血管“为新生组织提供活动力”。亨特认为局部组织能够独立启动这种血管形成而不依赖整体循环,这一观点在细胞学蓬勃发展以前并未受到强烈反对。
如果粘连性炎症不能有效控制刺激性损伤,其他两种类型:化脓型和溃疡型——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将随之发生。亨特认为化脓都是具有炎性的,以此为基础,血管结构发生变化,血液中的物质通过一种类似于分泌的过程与血液分离,形成脓液。他假定这些组分在血液中原始状态的改变发生在穿过血管壁的过程中。这种毛细血管具有分泌能力的观念后来在克吕韦耶的静脉炎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炎症类型,即溃疡,是对化脓的补充,以达到清除死物质的目的。他对修复、一期愈合及再生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通过结扎雄鹿鹿角的主要供血动脉,亨特发现了侧支循环,这只是他数百巧妙实验中的一个,而这一发现立即就在他本人的外科手术中得到了实际应用。
出于无法遏制的好奇心,亨特为科学献身,亲身接种了性病病毒。他将蘸取了淋病病人分泌物的小刀刺入自己的皮肤,由此引入致病物质。很快,硬下疳、腹股沟淋巴结炎、扁桃体溃疡(在确凿无误地“探明它的本质之前”,他不打算对此进行治疗)、铜色皮疹,总而言之所有的梅毒症状都接连出现,他确信是淋病的脓液造成了这些梅毒损伤,两种疾病是相同的。里考德(Ricord)后来的实验证明,亨特当时肯定同时注射了这两种病毒。
亨特的学生人才荟萃,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继承亨特教学职位的约翰·阿伯内西 (John Abernethy)、阿斯特利·库柏 (Astley Cooper)、他的内弟及助手埃弗拉德·霍姆(Everard Home,因在亨特死后剽窃其成果而在后世留下污名),以及亨特病理学公认的最佳解释者、爱丁堡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son,1765 – 1846)。亨特擅长通过尸体进行教学,作为讲师则十分差劲,紧张地念着讲义,还需要服鸦片酊以保持镇定。1793年他死于心绞痛,该病第一次发作是在二十年前,霍姆作出的尸检报告显示其病因为冠状动脉硬化,与詹纳依据莫干尼的文献资料所预测的一致。他那价值不菲的博物馆曾深入影响了当时的病理解剖教学,也曾作为学术机构的典范接受国外最著名解剖学家的参观,最终转归皇家外科学院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一项捐赠基金在他过世后不久成立,即如今著名的亨特讲座基金 (Hunterian lectures)。
亨特兄弟为病理解剖学教学建立博物馆的的事业由他们的外甥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1761 – 1832)延续了下来,他出版了第一部综合的病理学图谱。贝利也从拉纳克郡来到伦敦协助威廉·亨特,两位舅舅的声望使他的事业从一开始便一帆风顺,名利双收。报酬丰厚的医学实践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他的主要兴趣仍是病理解剖。与亨特兄弟的往来以及博物馆的资源为他提供了必要材料,使他得以完成精美的铜版画,并出版了著作《人体某些重要部位的病理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1794年初版),图册正是对这部著作的补充说明。这本书是第一本通过系统的组织和设计、专门为病理解剖学所写的病理学书籍,它迅速而异常的风靡显示出这类书籍在当时的极度稀缺,由此而来的不断再版与翻译当然也不足为奇。这几乎是一本纯描述性的作品,对病因学的强调相对来说少之又少,但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病理学家来说似乎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而相关的功能变化受到的关注大概就更少了,尽管贝利在引言中强调后者才是理解病理解剖学的真正目的。
与法国人不久后出版的伟大专著相比,贝利这本书很少引用他人作品。亨特的另一名学生威廉·斯塔克(William Stark,1742 – 1771)曾对结核空洞和咳血原因做出很有价值的研究,显然贝利对他的结核病论著非常了解,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其中肺结核与淋巴结核章节的内容。而贝利这部著作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简洁明了,正因如此,所有常见的病理变化类型才得以尽数呈现,受到医学界的关注。不管从内容还是编排方面,它确实是一本考虑周全的出版物。
贝利的图谱出版四十多年后,伦敦大学学院的病理学教授、苏格兰人罗伯特·卡斯威尔(Robert Carswell,1793 – 1857)发表了《疾病的基本形态图解》(Illustrations of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Disease,1837)。这本对开平版印刷图册通过彩色达到了铜版画不可企及的效果。尽管某些图片着色稍微过度,但以下画面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可分辨为死后胃部自溶的现象;脚趾的干性坏疽,相关文字解释其病因是由纤维蛋白、纤维性物质或骨质的堆积导致的动脉闭塞;肝硬化,并明确表示之所以并发腹水是因为肝脏的血液循环受到收缩的组织阻碍;心内膜炎,卡斯威尔意图据此图像反驳布约 (Bouillaud) 的论点,即该病起源于炎症;以及肺部与肠道结核,其中的肺结核图优美地展现了干酪样坏死物的三叶草形排列方式,这种样式近期被定名为“腺泡结节样”。有趣的是卡斯威尔从未在心脏瓣膜的疣状赘生物中找到血管,“虽然,”如他所说,“有些病理学家声称用注射的方法已成功发现其存在。”胃癌和直肠癌的图片也很精致,而他对肝癌结节插图的注解则是细胞病理学诞生前对这一黑暗领域最成功的解释。肝脏结节显然是转移性肿瘤,他将其解释为肝脏物质因血液中的癌性分泌物沉积而发生的转化。这一解释本质上与后来克吕韦耶的观点相同(如前所述),在当时大概是十分先进的。 该主题的厘清尚待栓塞的发现和细胞病理学的发展,但总而言之,卡斯威尔的著作意义深远,而它的相对冷门和鲜为人知也暗示了它是超前于时代的。
同期英国的另一重要图谱出自安德拉的学生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1801 – 41)。这本书(1834)十分受欢迎,还出了几个外文版本,但其中的彩色图谱与卡斯威尔和克吕韦耶的相比要逊色许多。
另一部配有极精美版画图解的重要专著《论动脉和静脉疾病》 (Treatise on the Diseases on Arteries and Veins) 出版时间稍早(1815),作者约瑟夫·霍奇森(Joseph Hodgson,1788 – 1869)在伯明翰综合医院做了三十年的外科医生。这是一部博学之作,尤其在动脉瘤及其历史方面。霍奇森承认该病产生之初可能只是单纯扩张,但他坚持当其发展成熟时,动脉瘤的产生必定涉及一或多层动脉管壁的破坏。这本书在整个欧洲大受欢迎,在法国,动脉瘤从此被称为“霍奇森病 (maladie d’Hodgson)”。
至此我们迎来了英国医学最闪耀的一段进程,它的创造者是为数不多的被称为“盖伊群英 (the Great Men of Guy’s)”几位医生。1725年,在南海贸易公司发财致富的伦敦书商托马斯·盖伊 (Thomas Guy) 追加了对圣托马斯医院的捐款,为其成立了一间名为盖伊医院的附属机构,,遗憾的是医院开业时他已经去世一礼拜。 这两家机构一直和谐共处,由圣托马斯医院充当教学主体,直到著名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阿斯特利·库珀爵士(Astley Cooper,1768 – 1841)任命自己在圣托马斯医院的解剖学教学继承人失败时才产生了纷扰。此时盖伊医院的财务主管哈里森先生向他伸出援手,提出模仿圣托马斯医院建立一所学校。在阿斯特利·库珀爵士的带领下,这间新的医学院蓬勃发展,迅速繁荣起来。
这段繁荣极大地推动了病理学的发展。在旧的制度下,尸检是比较少见的,如果一名医生想验尸,他需要向医院主管打书面报告,小心措辞如下:“X号床病人已故,我申请对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因为该病例十分重要,可为医学研究提供许多有用信息。”而在后来的体系中,尸检逐渐常规化,病理学服务由指定人员负责,记录迅速累积,病理解剖学博物馆在常任馆长的管理下达到了空前繁盛。促成这一切的人、自称白天不解剖点什么晚上就无法安睡的阿斯特利·库珀,激励年轻人尽可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验尸房。
在这样的条件下,布赖特、艾迪生和何杰金成长起来,在医学史上烙下光辉的印记。理查德·布赖特(Richard Bright,1789 – 1858)出身优渥,拥有最便利的学习条件,能够经常外出游历,接触顶尖的医学人士。他在盖伊医院的活跃事业开始于1820年,之前也曾在此度过一段学生时代。没有人比他更加强调临床与尸检的联系。尽管他永载史册的成就是关于肾炎或“布赖特氏病”的发现,但实际上他并不仅仅注重肾脏,他的兴趣遍布病理学的各个方面。
他逐渐开始关注肾病是在发现其与水肿的关系之后。 全身水肿 (anasarca)、浮肿 (dropsy) 或一般性水肿 (generalized edema) 在当时仍或多或少被看作一种独立的疾病,与肝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受重视。水肿与可凝结性尿液的关联偶尔有人注意,但直到布赖特出现,肾病、水肿与“蛋白尿”之间的零碎线索才被拼凑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布赖特对该体系发病机制的系统阐述发表在他的《医学案例报告》(Report of Medical Cases,1827)中,报告记录了他十年研究的结果。
注意到肾病与水肿之间的密切联系后,他继续区分了其他原因导致的水肿,由此对循环衰竭与水肿之间的联系给出了如下清晰描述:“水肿性渗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是循环受阻,在全身或局部范围内阻止血液通过静脉系统回流的任何因素,都将导致不同程度的浆液渗出。”肝硬化堵塞门静脉从而产生腹水就是一个例子。他还发现急性腹膜炎和腹膜结核也可引起腹腔积液,但在这些情况下,尿液并不会受热凝结(他的常规试验是将尿液盛于匙中在蜡烛上煮沸),肾脏也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他所援引的病例显示,水肿常常与患病的肾脏有关,而其他器官正常。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这样的描述:“小肾,有分叶,硬度增加,质感如同软骨一半的程度”,继而出现“小粒突出斑块,颜色发白或发黄,中间区域呈红色,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观感及触感皆粗糙”,如果“对该肾脏进行纵切,所受阻力类似于切割硬癌性腺体;其管状部分距离表面比正常情况近很多,而皮质部分整个呈现明显的颗粒状”。
在其他产生急性症状的案例中,全身水肿与“大的白色肾脏”相关联。布赖特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把疾病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单纯的韧度下降及出现早期斑点;接着肾脏体积增大,皮质出现颗粒,一种不透明的白色物质在间质内异常地大量沉积,同时出现高度可凝结的尿液和显著的全身水肿;最终肾脏变得粗糙、坚硬并缩小,常伴发水肿。而事实上,尽管布赖特仔细区分了肾源性和因循环衰竭所致的水肿,但结合现代知识分析其记录仍将不可避免地发现,他精心挑选的某些病例其实是肥大的心脏代偿不全导致的心源性水肿,因被动充血而产生蛋白尿。他的记录中也提到水肿常同时发现有心脏扩大的情况。
布赖特强调,酗酒、寒冷及汗液滞留导致的湿气是肾脏损害的诱因。他的临床与尸检工作得到了约翰·保斯托(John Bostock,1773 – 1846)和后来其他化学家的大力支持。他们在协作中发现了血液中有尿素存留,由此产生了尿毒症的概念,当时的布赖特已非常熟悉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血液化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进步,布赖特的同事乔治·里斯(George Rees,1813 – 89)记录了现在著名的糖尿病高血糖症。
多年工作中,布赖特经常向盖伊医院院报投稿。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后来被整理结册为《关于腹部肿瘤与膨胀的临床报告》 (Clinical Memoirs on Abdominal Tumors and Intumescence),这是一部极其有趣、博学、新鲜而又生动的著作。开篇的“探索腹部”让人联想起雷奈克的诊断学。关于卵巢肿瘤和常随之而来的“卵巢水肿”的报告尤为出色。另一优秀章节讨论的是“无头包囊”或包虫囊,布赖特在伦敦和旅途中时常见到这种疾病,这其中就包括该病现在的多发地冰岛。书中还描述了许多其他的腹部肿胀,但作者并未试图发表该主题的完整专著。
布莱特逝于1858年,尸检发现他的主动脉瓣硬化严重,主动脉口极度狭窄。
布赖特在盖伊医院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名托马斯·艾迪生(Thomas Addison,1793 – 1860),这个名字与另一器官的疾病不可分割地系在了一起。其时伦敦学院尚在襁褓之中,艾迪生与同期的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24年他来到盖伊医院深造,1837年进入医生行列,多年来一直是这里的领军人物。随着病例的成倍增长,一种不寻常的“自发”贫血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查患者并无明显出血,除“某些器官脂肪沉积”外也没有典型的病理解剖特点。显然,他忽略了骨髓,这是恶性贫血,也常被称为“艾迪生贫血”以示对这一早期描述的赞誉。
在探求病因的过程中,一组同样起病隐匿的症候群吸引了他的注意,其特征包括贫血、疲倦、心脏活动无力、胃部亢奋以及皮肤变色,通常并发肾上腺疾病。他最初于1849年将两种疾病的观察结果递交给南伦敦医学会 (South London Medical Society),后于1855年增述,同时发表了十一例病例。艾迪生是一位擅长描写的皮肤病学家和病理学家,十分仔细地描述了皮肤的变化。十一个病例的主要病因不尽相同,足以支持他的结论:虽然肾上腺结核是常见病因,但腺体的恶性肿瘤或单纯萎缩也可能导致相同的临床症状。然而,对于这种疾病与前述自发性贫血的可能关系,他仍然困惑不已。他的这一重要发现一直未受重视,直到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被法国的特鲁索 (Trousseau) 重新发掘并命名为“艾迪生病”,当时内分泌生理学正在克劳德·伯纳德 (Claude Bernard) 的引领下发展起来。
艾迪生对肺炎的研究极有见地但却默默无闻,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正确地将肺实变的原因归结为肺腺泡积液,而不是普遍认为的间质组织积液,他并不认可间质组织的存在。然而,艾迪生没有机会感知到细胞病理学的曙光,含糊不清地提及肺的“蛋白化”以及“恢复到一种类似于蛋白物质的状态,这种物质是所有组织的组成基础”。他独立于罗基斯坦斯基 (Rokistansky) 明确区分了小叶性和大叶性肺炎,甚至认识到前者在本质上的多样性,(“阻塞与炎症的混合”),对肺不张的描述和理解超过了雷奈克。
在这济济一堂的英才中,盖伊医院的专业病理学家托马斯·何杰金(Thomas Hodgkin,1798 – 1866)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作为博物馆馆长和病理解剖学演示员,他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藏品,还通过建立准确的分类目录,提高了它们的适用性。他从组织的角度讨论病理变化,是英国第一个追随比沙先进思想的人,著有专题论文《浆膜与黏膜的病理解剖学》(Morbid Anatomy of the Serous and Mucous Membranes,1836 – 40)。盖伊医院后来的病理学家回顾何杰金时,都称他为先驱。
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学生如今仍会使用“何杰金氏病”这一称呼来表示一种以某些淋巴结群和脾脏增大为特征的疾病。而事实上,何杰金的两篇《论淋巴腺与脾脏的一些病理现象》(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the Spleen,1832年1月10日、24日)中记录的病例除了这种冠有他名字的疾病外,还可发现有结核病、白血病,可能包括继发性肿瘤。其中报告的七个病例有出自他本人的,也有来自布赖特、艾迪生和卡斯威尔的。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案例中并没有新发现,出版它们仅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迄今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一系列病理变化。
由于晋升失败,他于1837年从盖伊医院退休,这给病理学造成了巨大损失。他是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成员,天生的慈善家,后来参加远行前往东方援助犹太人,1866年因痢疾在雅法 (Joppa)病故。
1827年何杰金发表了一篇讨论主动脉瓣后翻与关闭不全的文章,这是他最优秀的论文之一。前面我们看到维厄桑斯 (Vieussens) 曾描述过这种情况,1815年霍奇森也留下了它的精美图画。然而,对于这一疾病的理解,当时的时机显然并不成熟,最终常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是科里根。多米尼克·约翰·科里根(Dominic John Corrigan,1812 – 1880)是伟大的都柏林学院的一员,这所学院的杰出临床医生还包括格拉夫 (Graves)、斯托克斯 (Stokes)、切恩 (Cheyne) 和亚当 (Adams)。1832年科里根发表论文《论主动脉口永久性开放或主动脉瓣闭锁不全》 (Permanent Patency of the Mouth of the Aorta or Inadequacy of the Aortic Valves),将该疾病与动脉瘤进行了区分,也提到二者常常相互关联。他发现了这一疾病的四种类型:(1)瓣叶穿孔,(2)瓣叶破裂,(3)瓣叶僵化,无法伸展覆盖整个主动脉孔,(4)主动脉孔整体扩张。其典型的水冲脉被他正确归因为瓣功能不全,自此被称为“科里根脉”。同时,他意识到与主动脉返流相关的心脏肥大不是疾病,而是心肌的一种代偿作用。
起初爱尔兰医师学会没有认识到科里根的特殊贡献,否决了他的会员申请,但他活到七十八岁,过世前连任了五届学会主席。
此处需要提到英国两项重要的血液学研究成果,尽管二者与更为详尽的德国的作品相比都相形见绌。其一是1842年发表的《血细胞、炎症及肺部结节的起源与状态》 (Blood Corpuscles, Inflammation and the Origin and Mode of Tubercle in the Lungs),作者威廉·艾迪生(William Addison,与托马斯没有亲戚关系)是一名执业医生,也是显微镜的早期爱好者。这篇文章在炎症的血管与白细胞反应的多个特征上领先孔海姆 (Cohnheim) 二十五年。威廉明确发现并区分了单核与多核白细胞,认为“脓细胞是变异的无色血细胞”,而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由发炎组织中的血液颗粒和分子演变而来。
另一重要成果是血液中白细胞过多现象的发现,记录在1845年发表的一篇论肝脾肿大的文章 (Hypertrophy of the Spleen and Liver) 中,作者约翰·休斯·班尼特(John Hughes Bennett,1812 – 1875)是爱丁堡皇家医院的病理学家,他将这种疾病区别于化脓,命名为“leucocythaemia(白血病)”。后来微尔啸也记录了同一疾病,称“leucaemia”,此后班尼特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疾病。
塞缪尔·威尔克斯(Samuel Wilks,1824 – 1911)是英国病理解剖学独立教学最伟大的拥护者,他是盖伊医院的病理学家,在长寿的一生中见证了该学科所有伟大的现代发展,而他对此领域的理解高屋建瓴, 也将这些迅疾但互不关联的进展统一了起来。 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理解盖伊群英的工作,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忧心学生常规病理学课程的不足。他本人在这一短期课程中的讲座异常受欢迎,于是他应学生之请将这些演讲整理为书籍,于1859年出版。遗憾的是他在编辑中采用了盖伊博物馆的大纲而不是一个逻辑性的结构。这些演讲基于他曾见过的两三千例尸检,而此时在他的带领下,盖伊医院每年也会开展约二百五十例尸体解剖。威尔克斯原创作品中最优秀的应该是《论内部器官的梅毒感染》(On the Syphilitic Affections of Internal Organs,1863),文中描述了肝脏和其他器官的梅毒瘤,人们最终能够认同常见的主动脉瘤是一种梅毒损伤,这篇论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英文病理学教科书当数塞缪尔·大卫·格罗斯(Samuel D. Gross,1805 – 1884)在1839年所著的版本。格罗斯是宾夕法尼亚人,先后担任路易斯维尔医学院和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外科学教授,是第一个在美国开设病理学常规课程的人。这本教科书的三个版次在国内外均好评如潮,甚至于挑剔的微尔啸也对其赞赏有加。然而,它几乎是一本孤立的作品,与优秀的霍乱研究者,费城人威廉·埃德蒙兹·霍纳(William Edmonds Horner,1793 – 1853)早些年出版的《病理解剖学论》 (Treatise on Pathological Anatomy) 一道,组成了这个国家仅有的国产病理解剖学教材。此时的美国病理学尚不能自立门户,希望接受病理解剖学训练的美国人多年里仍需远航欧洲,在宏伟的欧洲停尸房之间辗转奔波。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3-16 15:11:56 编辑
前面两章所描述的历史阶段中,普通和专科病理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国与英国平分秋色。法国的贡献毫无疑问以泽维尔·比沙 (Xavier Bichat) 开创的组织病理学为首,而雷奈克 (Laennec) 在专科病理学尤其是胸部疾病方面的成就,以及克吕韦耶 (Cruveilhier) 的教学图谱和书籍也都影响深远。在英国,约翰·亨特 (John Hunter) 建立了实验病理学,马修·贝利 (Matthew Baillie) 出版了系列版画和第一部现代的病理学教科书,盖伊医院 (Guy’ Hospital) 以布赖特 (Bright)、艾迪生 (Addison)和霍奇金 (Hodgkin)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在多个专科病理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而此时,知识增长的浪潮正向东涌动。法国和英国的[***]已过,中欧的发展方兴未艾,很快占据了病理解剖学的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为了了解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需要回到一个世纪以前,重拾一条被遗漏的线索。1745年,格哈德·冯·施威腾(Gerhard van Swieten,1700 – 72),布尔哈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受邀来到维也纳,成为玛丽娅·特蕾莎女王 (Queen Maria Theresa) 的私人医生。同期来到维也纳的还有海牙 (Hague) 的安东·德·哈恩(Anton de Haën,1704 – 76),两人的影响力使这座奥地利首都成为伟大的荷兰医学派最显赫的分支。施威腾的改革中包括建立医院、发展诊所和完善帝国图书馆。哈恩则首次在诊所为学生演示常规尸体解剖。
这支维也纳学派通常被称为老维也纳学派,以区别于罗基坦斯基时期辉煌许多的新维也纳学派。利奥波德·奥恩布鲁格(Leopold Auenbrugger,1722 – 1809)是老维也纳学派最出色的成员之一,他是圣三一医院 (Hospital of the Holy Trinity) 的首席医生,体检诊断中著名叩诊法的发现者,同年这一方法通过莫干尼的《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1761)传播开来。奥恩布鲁格将对结核、肺炎、胸腔积液等疾病患者活体的观察与尸检的发现进行对比,甚至在尸体上做实验,将液体注入胸腔后通过叩诊判断液位。他的重要观察大都来自痨病病人,但他对这种疾病本质的观点却完全是陈旧过时的,认为情绪的影响以及胸腔淋巴液的毒性仍然在发病机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作品受到同行的轻视,若不是巴黎的科维沙 (Corvisart) 搬出自己的大名把它复活,它恐怕早就被遗忘了。
1784年维也纳综合医院 (Allgemeines Krankenhaus) 成立,1795年伟大的公共卫生学家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1745 – 1821)就任该院院长,这标志着维也纳进入现代时期。他的任命让人们意识到病理解剖学黄金时期的到来,对尸体解剖的限制也基本上被排除。此时医院每年接待约14,000名病人。1796年,共2559弗罗林的款项被用于筹建停尸间、解剖室和解剖员住所。
阿洛伊斯·鲁道夫·维特尔(Alois Rudolf Vetter,1765 – 1806)担任了解剖员这一新职位。他是卡尔斯巴德人,在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受教育,因面对艰难困苦的卓越能力而受到约翰·彼得·弗兰克的赏识。在此之前,维特尔遭到了冯·施威腾的继任者安东·斯托尔克 (Anton Stoerck) 的憎恶,后者铁了心地反对他的解剖学和外科学研究。尽管如此,这名天资聪颖的年轻人仍然接连出版了一本解剖学手册(1788)和一本生理学教科书(1794)。然而,后一作品中某些科学发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令他陷入了困境。
弗兰克的任命将他从一些麻烦中暂时解救出来,尽管一开始没有薪水,但他终于得到了一直以来渴求的机会,能够不受阻碍地对人体进行疾病研究。三十八岁时他已经有几千例尸检的经验了。经他之手,病理学博物馆的标本由他任职之初的四五件增至超过四百件。1803年,他将自己的观察整理成一本《病理解剖学原理》 (Aphorisms from Pathological Anatomy),书中少有理论而富于优秀的客观描述,尤其在胃肠道损伤与肺结核方面。
如果能与临床合作,维特尔可能开启维也纳的伟大发展,彼时时机已然成熟,但他天性中的某些东西总是不断招来妒忌和憎恶。《原理》一书反响不佳,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便辞去了在维也纳的工作,放弃了这个令他深陷贫困、除了忧愁一无所获的职务,转而接受了克拉科夫 (Cracow) 的一个岗位。1805年他回到维也纳,在此终了。
这个职位在维特尔之后便没落了,1804年彼得·弗兰克离开医院,接替维特尔的人都比较无关紧要。1821年,新的管理制度带来了一段短暂的复兴。维也纳大学为医院的解剖演示员特设了一个教授职位,要求任职者处理法医病理学事务兼讲授规定课程。自1811年起就在原有体系中担任解剖员的洛伦兹·拜尔梅耶 (Lorenz Biermayer) 第一个体验了新制度。他一开始勤奋至极,但很快便陷入了和维特尔一样的困境,缺乏临床人员的配合协作。失望与反感让他渐渐失去了工作热情,继而酗酒、怠工、停职。复职后情况并未有所好转,1829年他的助手约翰内斯·瓦格纳(Johannes Wagner,1800 – 32)接替了他。瓦格纳在短暂任期中的表现无不预示着一片大好前途,然而,他对霍乱、内疝和其他肠道损伤的观察都因他的早逝而终结,不幸的维也纳综合医院解剖员之位又一次空缺了。低谷中,瓦格纳的助手卡尔·罗基坦斯基上任了。
卡尔·罗基坦斯基(Carl Rokitansky,1804 – 78)生于波西米亚的克尼格雷茨 (Königgrätz),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学医,1828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同年成为瓦格纳的病理解剖学助手。学生时代的罗基坦斯基深受马丁·罗伯斯坦 (Martin Lobstein)、加布里埃尔·安德拉 (Gabriel Andral) 及同时期伟大的法国学院其他人作品的影响,尤其是比较解剖学创始人之一的约翰·弗里德里希·梅克尔(Johann Friedrich Meckel,1781 – 1833)。梅克尔的胚胎学引导人们正确理解了当时病理学最迷茫的领域——先天畸形,破除了“怪物”和其他出生畸形起因于超自然力量的传统认知。这种早期的兴趣使罗基坦斯基与瓦格纳建立起联系,瓦格纳过世后,罗基坦斯基代理部门领导职务两年,之后正式继任。这一非正规的教授职位又持续了十年,直到罗基坦斯基声望越来越高,设立正式的病理解剖学教授已势在必行。在他的领导下,尸检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每年平均1500到1800例。罗基坦斯基在1827年10月23日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尸检报告,在1866年三月写下第三万份。
病理解剖学的发展如火如荼,临床方面,一场同样引人注目的变革也正在展开。这场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在约瑟夫·斯柯达(Josef Skoda,1805 – 1881)的推动下进行的。斯柯达也是波西米亚人,生于皮尔森 (Pilsen),出身卑微,大学毕业后进入医学领域,很快便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出人头地。斯柯达受科维沙与雷奈克作品的影响很深,他独创的分类更多地以尸检发现的器官真实状态为基础,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法国学院的经验主义。他本人的贡献主要在叩诊和听诊方面,他的名字因“斯柯达氏叩响” (Skoda’s resonance) 依然为当今学子所熟知。
与斯柯达和罗基坦斯基共同实现这一段伟大进程的还有希伯拉 (Hebra) 和波利策 (Politzer) 等著名专家,解剖学家约瑟夫·希尔特尔(Josef Hyrtl,1810 – 94),1849年后还有生理学家、约翰·缪勒 (Johannes Müller) 的学生威廉·冯·布吕克(Wilhelm von Brücke,1819 – 92)。凭借这种多学科的发展和法国与德国的文化刺激,加上个人的独立思想与创新精神,老维也纳学派日渐荒芜的土地上巍然立起一幢更加坚固的新大厦,短短数年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人们从未如此热切地发展医学的基础分支,也从未像这样忽视医学的既定目标——治疗与解救病人。在斯柯达的领导下,诊断是最重要的,余下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在尸检时对其进行确认,尸检详尽透彻,精细绝伦。
罗基坦斯基是一流的解剖学家,他对病理学的贡献却不仅限于所开发的尸检方法,这种方法在解剖的逻辑性和对细节的理解上确保了每次检查都能涉及到尸体的每个部位,当今中欧使用的许多尸检方法大多数如它们的发明者大方承认的那样,或多或少“由罗基坦斯基”的方法改进而来。他的程序兼顾了暴露检查的彻底性和结构连续性的保存,在这方面与后来流行的微尔啸的方法有所不同,微尔啸的检查同样彻底,但允许解剖学系统的更多分离。然而,单纯的解剖学描述远不足以令罗基坦斯基满足,他对病例的阐释还包括病因学和最终所见状态的形成过程、当中涉及的功能紊乱,甚至延伸到治疗方法,但这个部分并没有从他在临床方面的某些著名同事那里得到足够的关注。他致力于依据解剖学基础建立疾病类型,并考虑到所有不同的病因和症候学,在这方面的成就截至当时无人能及。在他之后,疾病的名称如肺炎和伤寒症,对于受过良好培训的医学毕业生来说不再只是一列复杂程度不等的症状,而是一幅解剖学的画面。这是罗基坦斯基对医学的不朽贡献。
考虑到他的任务之重,他像魏希瑟尔鲍姆 (Weichselbaum) 所说的那样“在寻求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产生了差错”就不足为奇了。虽不在维也纳出生,他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维也纳人,受到这座光辉的奥地利首都长久的熏陶,他的思想形成不可控制地被想象和戏剧性的本能影响。他是当时甚至所有时代最优秀的描述病理学家,却无法满足于目之所及的事实,呕心沥血建立了一座理论的空中楼阁。当冷静而现实、不那么富于想象的微尔啸残忍地摧毁了他的理论,那绝对是致命的一击。
这个不堪一击的学说就是著名的体质与恶性体质 (crases and dyscrases) 假说,它的建立源于当时最新的生理学理论“胚基”,或原始流动物质,有形成分都由此衍生而来。当时,施旺 (Schwann) 关于生命的细胞本质的新理论(见下章)业已问世,他却选择了错误的一半,进一步发展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错误尝试——恢复体液病理学——这个自维萨里第一次向伽林的理论提出反对就节节败退的学说。罗基坦斯基的观点发表在著作《病理解剖学手册》的第一册中,事实上这一册是该系列最后出版的一本(1846)。他在书中坦言:“体液病理学只是普通的现实意义上的需要;它一直都在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又在病理解剖学领域得到了新的依据和支持。”
罗基坦斯基的理论与我们今天的观念相去甚远,因此不可能用简单的形式描述。他的观点使人想起约翰·亨特的血液“生命”概念,贯穿始终的还有安德拉对不同疾病血纤蛋白的更偏向定量研究的痕迹。在最后的分析中,罗基坦斯基提出所有的疾病状态都来源于血液的异常,且局部疾病一旦发生,还能够进一步引起循环中的血液变性。他认为化学将最终解决病理学的大部分难题,并“敦促化学病理学家不懈研究”,尤其从定性的角度,他相信这将解释新组织在分泌、化脓和结构上的某些不同,而这些是他通过单纯的解剖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
他提出了特异性体质的概念,表示诉诸经验医学只是暂时的,并希望最终能得到化学方面的支持。这些体质都能追溯到最初的血液损伤,“血液整体的原始疾患”,分别对特定部位具有特异性亲和力,如“格鲁布性纤维蛋白体质”针对呼吸系统,表现为白喉和肺炎;“伤寒体质”针对回肠黏膜,表现为人们熟知的伤寒症;“发疹体质”则显示为常见的出疹性皮肤病。
他强调,导致这些器官疾病的恶性体质并不一定能在局部聚集,它们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引起后续的病变。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局部恶液质并不绝对能引发整体循环的连续恶质化,这种情况的发生要求吸收大量的病变、降解、腐败或产生其他变化的血浆。但总而言之,局部与整体恶性体质的表现仍是紧密相关的。
这套理论一旦开启,接着便是无穷无尽的精细分类。他把格鲁布性的纤维蛋白体质分为a、b 和g三型,还划分了特殊结节体质、癌症体质、伤寒体质甚至酒鬼体质,在此基础上又区分了急性和慢性的形式。他信心满满地谈到“结节的形成耗费了恶质结节纤维蛋白的每一个原子”,对脓毒症却一无所知,提出“血液整体的自发性原始脓毒症”以及同一体质导致的“局部化脓”;之前的亨特与克吕韦耶对脓毒症也都有心无力。最后再加上他费心构想出的体质互变的概念,他终于将整个学说打造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幻想。
这样的执着令人惊诧,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作者亦承认在著作的编写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偏倚”。也正是这种过分的造作刺激了年轻的微尔啸,令他火力全开,凭借让人无法反驳的逻辑在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抨击,称之为“荒诞的时代错误”,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此后罗基坦斯基重写了《手册》一书,面对着新的细胞病理学,他试图忘记自己曾为已逝的体液学说所作的徒劳争斗。该书后来又再版了两次。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罗基坦斯基的整个病理学系统因他的体质理论而全军覆没,微尔啸也承认罗基坦斯基是当时最伟大的描述病理学家,他对不同疾病病理形态的精彩阐述不会受理论错误的牵连而失色。按照罗伯斯坦和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城市)解剖学家阿道夫·威廉·奥托(Adolph Wilhelm Otto,1786 – 1845)的体系,他阐释了每种器官或组织因以下情况可能受到的损伤:(1)生长不足或过度,(2)大小偏差,(3)形状或位置偏差,(4)结构连续性中断,及(5)材质或实质异常,这个系统完全忽略了病因学,但在病因学尚未发展完善的时期实现了便捷的疾病分类。维也纳综合医院大量的材料保证了已知的几乎所有疾病种类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被囊括在内。
他将充血分为主动、被动和机械型,指导了该主题后来的教学,对主动充血的解释完全符合毛细血管神经支配的现代学说。他认为毛细血管的主动扩张是炎症的基本特征,直接决定了后续的重要继发现象-瘀滞和渗出。
他的期刊论文多数发表在《奥地利国家年鉴》、《维也纳医学会刊》和维也纳科学院的出版物上,但他的重要原始发现并没有全部包含在这些论文中,还有许多通过伟大著作《手册》公之于众,并无任何附加声明。
他最伟大的专题论文是《心脏间隔缺陷》 (The Defects in the Septum of the Heart),分次发表于1875年,临近他漫长而忙碌人生的终点。作者对此倾注了多年心血,以期完成1851年《最重要的动脉疾病选论》(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of the Arteries)中的一个研究。这两部著作中,先天畸形都占了很大的篇幅,从他对此领域明显的特殊兴趣中,伟大的畸形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梅克尔的深远影响也可见一斑。罗基坦斯基是一位优秀的胚胎学家,能够通过不同部位的胚胎学缺陷预测将会出现的发育障碍,就像化学家可以预言填补周期系的新元素的发现。他浩瀚的经验足以使他填满可预知的血管系统先天异常的所有空缺。此外,他也没有忽视后天损伤,他的动脉疾病图谱甚至描绘了结节性动脉周围炎这样的罕见病。
他对其他器官的病理学专论也毫不逊色。他深化了雷奈克对肺气肿的描述,完善了肺炎的现有知识,通过解析肺大叶类型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小叶性肺炎及其发展阶段,描述了急性黄色肝萎缩,将穿孔性胃溃疡界定为溃疡的一种特殊类型,还描述了甲状腺肿,多种内脏囊肿,脾、肝和肾的淀粉样变性(微尔啸所说的“amyloid”),心脏瓣膜的急慢性炎症,并详细论述了各种器官的肿瘤。由于信仰体液假说,在《手册》的初版中,他将肿瘤生长的原因归结为血流中的固体和液体胚基在局部变性,从固化的胚基以及液体胚基中的细胞性、核性与纤维性材质中生长出纤维性的基质。他在描述中使用了肉瘤 (sarcoma) 和癌 (carcinoma) 两词,因长期使用形成自己的独特用法,与今天和当时的含义均不同,分别等同于“良性”和“恶性”肿瘤。
至退休时,罗基坦斯基能够获取的尸检报告多达约七万份。在位于维也纳的属于他自己的研究所里,他享受了得到极大改善的工作条件。人生的最后二十五年,他已经是这座城市最杰出的医学人物,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病理学,还延伸到综合医学教育的基本原则与课程设置。他于1849年成为医学院院长,1850年成为学校校长。1874年,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全市人民都参与其中。他的退休声明明确表示,他已将病理解剖学发展为成果最为卓著的医学研究方向,是病理生理学和医学基本理论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而病理组织学、化学病理学和以活体动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病理学将是对病理解剖学的合理补充;病理学不仅有助于医学实践,从广义的层面,它给生物学本身带来了光明的前景。1878年7月23日,罗基坦斯基与世长辞。
罗基坦斯基之后,理查德·赫谢尔(Richard Heschl,1824 – 1881)接任病理解剖学教授,任期为1875至1881年。他的贡献主要在淀粉样变及其特殊染色性质、肺梗死及脑神经节细胞钙化等方面。他的继任者汉斯·昆德拉特(Hanns Kundrat,1845 – 1893)也曾是罗基坦斯基的助手,在先天畸形领域有重要贡献,还描述了淋巴肉瘤。
昆德拉特死后,罗基坦斯基的传承者在专业重点方向上有所分化。继任教授职位的是安东·魏希瑟尔鲍姆(Anton Weichselbaum,1845 – 1920),他把新兴的病因学理念带到了严格意义上更偏重形态学的维也纳病理学中。魏希瑟尔鲍姆是维也纳最早预见到细菌学影响力的人之一,也是在新学说的促进下研究浆膜炎症的先锋人物。他对结核病尤其感兴趣,而他的多名优秀学生,特别是安东·高恩 (A. Ghon),都为增进人们对该领域的认知做出了贡献。
维也纳大学病理学系的其他重要岗位尽归罗基坦斯基学派的杰出学子。亚历山大·科里思科(Alexander Kolisko,1875 – 1918)接管了法医病理学一段时间,最终在魏希瑟尔鲍姆退休后继任病理解剖学教授。他的重要成就包括研究自然因素导致的猝死,在维也纳大学法医学院成立百年纪念之际着手编辑《法医学文选》 (Beiträge zur gerichtliche Medizin),以及对骨盆畸形详细、准确的研究。
理查德·帕尔托夫(Richard Paltauf,1858 – 1924)继任了病理组织学与细菌学研究院主任,之后斯特里克 (Stricker) 与克诺尔 (Knoll) 先后出任大体与实验病理学研究院主任。帕尔托夫在新的免疫学领域很有造诣,极大地推动了该学科在维也纳的发展,促成了重要的《免疫学杂志》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的创办。病理解剖学方面,他跟随老师昆德拉特的指引继续研究淋巴肿瘤。
这段时期,雄厚的师资力量、优越的研究条件以及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使维也纳成为病理解剖学教育的世界中心,它的美誉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拉格学院与维亚纳学派关系密切。曾是罗基坦斯基与赫谢尔助手的汉斯·基亚里(Hanns Chiari,1851 – 1916)于1882年接替克勒布斯 (Klebs),成为布拉格大学的病理解剖学教授,将维也纳的传统带到了这座城市。他的熟练技巧、名声在外的尸检方法和教学能力为他迎来了许多学生。布拉格大学情况特殊,分而治之的捷克语和德语高等学校并立,从来就是民族矛盾的集中地。特赖茨窝、窝疝与特赖茨肌肉(即十二指肠悬韧带)的发现者文策尔·特赖茨(Wenzel Treitz,1819 – 1872)在纷争中因抑郁症自杀。基亚里的工作同样时常受到政治动乱的影响。1906年,他接替冯·雷克林豪森 (von Rechlinghausen)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
在病理学相关领域,新维也纳学派最重要的成就是匈牙利人伊格纳茨·菲利普·泽梅尔魏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1818 – 65)发现的产后脓毒症的传染性,这一发现确认了美国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 – 94)之前提出的意见(1843)。泽梅尔魏斯是斯柯达与罗基坦斯基的学生,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产科病房助手时,他注意到,他的病房由刚从解剖室出来的学生直接查房,产褥热发生率极高,而另一病房由助产士看护,则少有这种情况。尸检发现,死于产褥热的妇女和因伤口腐烂患上败血症的病例有相似的损伤,他很快确信,两种疾病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基于这一发现,他改良了产科操作,这在预防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与詹纳 (Jenner) 的预防接种相当。
维也纳的外科权威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1829 – 94)毕业于同时期伟大的柏林学院,对创伤引起的脓毒症也非常感兴趣,也是最早在其中发现细菌的人之一。他在消化道损伤方面有着丰富的外科经验,极大地完善了我们对该部位病理学的认识。而他对肿瘤宏观和显微结构的深入研究(见下章),不仅确立了他在外科病理学发展史上的领袖地位,也使他成为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始终强调,病理组织学研究是外科学进步的理性基础。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5-03 10:33:25 编辑
第九章 微尔啸与细胞病理学
回顾上世纪中期,我们会发现病理学虽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却处在一种令人费解的无助状态。相关疾病的主要大体病理变化已基本确定。朗契西、瓦尔萨尔瓦、莫干尼、桑迪福德、塞纳克、科维沙、雷奈克、路易斯、格哈德、布赖特、艾迪森、霍杰金以及当时众多的学界同仁,以十七、十八世纪大体病理学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基础,将人们对多种器官疾病的认知推向了难以超越的新高度。积累的零散细节急需某种必要的学说将它们连接起来。然而,这段时期人们为提供这种联系而建立的所有体系都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模糊虚构的“万物有灵论”和“布朗主义”,以及较为实际的约翰·亨特的血液生命学说和克吕韦耶的静脉炎理论,或经不起验证,或无法延伸。只有比沙在组织学上的伟大贡献对情况的厘清有所帮助,但也不足以满足病理学的需求。
试图以一个单独的理论体系囊括病理学各个系统病理变化的最近一次努力,正是我们上章刚讨论过的罗基坦斯基的体质假说。步履蹒跚的老维也纳医学派在他的带领下飞跃重生,这位掌握大量尸检材料的描述病理学大师在理论归纳上却比其他所有人都错得更离谱。生命的细胞学说发布之初,罗基坦斯基已经成年,他很可能见过第一位细胞病理学家。但最早的细胞理论将一种原始“胚基”当作细胞发育的源头,这位伟大的维也纳病理学家则悲催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选择这一谬论作为搭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
细胞学说的理论发源于德国,人们在这新知识中找到了准确的模型,新模型为病理学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整合,而是整个病理学科的革命。开启这段进程的灵感出自一位卓越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最后一位学识覆盖所有科学领域的哲学家、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导师——来自波恩与柏林的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1801 – 1858)。作为施旺(Schwann)、亨勒(Henle)和微尔啸(Virchow)的老师,他是现代组织学和细胞病理学发展的先驱。穆勒是最早使用显微镜分析组织的人之一,早在1830年就已开始对腺体和软骨进行深入的组织学研究,但对病理学意义最大的是他的早期作品《论肿瘤的微细结构与形态》 (On the Finer Structure and Form of Morbid Tumors)。论文发表于1838年,正是他的学生施旺首次提出细胞生长是动物生命基本原理的年份。这篇文章划时代地确定了新生物的细胞本质,而它反过来又始于作者本人发表于1836年的一项初步研究,其中他以一种半组织学的研究为基础区分了两种肿瘤,“网状癌 (carcinoma reticulare)”和“束状癌 (carcinoma fasciculatum)”。
依靠新近改良的显微镜及煮沸、酸处理和曾对比沙帮助很大的化学方法,后来的工作不仅发现了细胞本身,还揭示了它们的某些细微特征和生长状态。自此,穆勒强烈意识到一定能够依据这种细胞学的发现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肿瘤,于是他比较了临床上良性与高度恶性的肿瘤,却发现二者具有相同的结构,即细胞、胞内的细胞核与各种颗粒,以及胞外的纤维。他的学生施旺同时发现正常组织也由这些成分构成的。
接着富有想象力的穆勒又借助化学办法成功分离了几种蛋白类物质,他认为其中一种胶质具有某种特殊性,将其命名为“粘液变性瘤 (collonema)”,后来微尔啸在单纯的水肿结缔组织提取物中也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存在。穆勒这篇论文发表时并不完整,之后也一直没有完成。它确定了肿瘤的本质是细胞并推测它们来源于正常细胞,肿瘤良性与恶性则仍依靠它们的临床表现来区别。
泰奥多尔·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 – 1882)是穆勒在波恩大学的学生,后又在柏林做他的助手。他早期对腐败和自然发生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后来的伟大成就部分来源于一个意外。1831年植物学家马提亚·雅各布·施莱登(Matthias Jacob Schleiden,1804 – 1881)提出植物由细胞构成。与施莱登的一次偶然交谈令施旺产生了对人类组织进行细胞学研究的念头,他也确实并认真地执行了这个想法。发现所有动物组织都由细胞组成后,施旺发表了他的著名结论:“生物体的组成部分不论存在多大的差异,它们生长发育的原理都是同一的,那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他于1838年首次宣布这一发现,1839年发表完整论文。
然而,把施莱登的概念应用到组织学时,施旺也一并引入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后来被微尔啸发现,在此之前却坑惨了罗基坦斯基。这就是“胚基 (blastema)”理论。施莱登和施旺都相信一种生发性液体的存在,即“胚基”或“细胞形成质 (cytoblastema)”。在组织发育的过程中,胚基生长出核仁及其周围的颗粒,它们浓缩形成细胞核,然后新的物质逐渐围绕着细胞核聚集并最终浓缩为细胞质。换言之,细胞能够在物质内部以某种形式自然发生。这种细胞自由形成的理论当时很流行,直到被微尔啸推翻。
然而在微尔啸之前,组织学在穆勒另一名学生雅各布·亨勒(Jacob Henle,1809 – 1885)的带领下实现几乎同等重要的进展,他曾先后在苏黎世、海德堡和哥廷根担任解剖学教授。我们现行的组织学分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亨勒的早期研究。正如加里森的评论:“亨勒的组织学发现可媲美维萨里在解剖学上的成就。”幸运的是,他的早期研究成果的发表,为后来微尔啸建立细胞病理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亨勒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组织学家,他的《理性病理学手册》(Hand Book of Rational Pathology,1846 – 53)是学生的标准教科书,而在微生物感染理论中我们也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严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病菌学说早期信马由缰的发展。
组织学的进展很快在病理学中得到应用。细胞理论发表后的六年内就出现了两部附插图的病理组织学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34年,作者朱利尔斯·沃格尔(Julius Vogel,1814 – 80)当时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这本书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最新的发展已经使病理组织学图谱成为和大体病理解剖学图谱一样的迫切需求。该书分为两部分,大致对应病理学的总论和各论。显微镜下观察和制作插图所需的病理切片由双刃刀片切割制成(参见第十章中组织学技术史的简要描述)。
另一本书的作者赫尔曼·雷柏特(Hermann Lebert,1813 – 78)生于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城市),往来于在德国、瑞士和巴黎之间,用德、法两种语言同样流利地发表了他的发现。他的图谱名为《病理生理学的临床、实验与微观研究》(Physiologie pathologique ou Recherches cliniques, experimentales et microscopiques,1845),其中包括二十二幅精美图片及附带的文本,是他在巴黎时的研究成果。
随着这些作品的传播以及其后一些较为次要的书籍的发行,细胞病理学的观念渐入人心,人们开始习惯于谈论结核细胞、癌细胞等等,但直到微尔啸进入这个领域才真正地阐述了其重要意义。
病理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鲁道夫·微尔啸(Rudolf Virchow,1821 – 1902)生于波美拉尼亚一个名为斯希维尔本 (Schievelbein) 的乡村。他于1839年入读柏林大学,这名年轻的学子在约翰内斯·穆勒和约翰内斯·卢卡斯·施贡莱恩(Johannes Lucas Schönlein,1793 – 1864)的引导下对自然科学的基础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43年微尔啸毕业,毕业论文讨论的是炎症的一个阶段,这一宽泛的主题在其后多年仍占据了他很多的注意力。当时的柏林病理解剖学相对来说发展并不充分,这方面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弗罗里普(Robert Froriep,1804 – 1861)是查理特医院 (Charité Hospital) 博物馆的解剖员兼馆长、查理特大学的外科解剖学教授,以及一家名为“弗罗里普笔记”的杂志的编辑,微尔啸的首批论文就发表于此。弗罗里普是一位优秀的解剖学插图画家,还大量翻译了阿斯特利·库珀、迪皮特朗及其他顶尖外科医生的著作。
毕业一年后微尔啸来到弗罗里普的博物馆担任解剖助手,在此期间他除了解剖尸体之外,还勤奋地对组织进行显微镜下研究和分析化学, 这两项工作给他的未来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为病理学的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1846年,弗罗里普离职前往魏玛 (Weimar),微尔啸成为医院的解剖员。此时与他交好的两人,一个是本诺·莱因哈特(Benno Reinhardt,1820 – 1852)也是一位年轻的病理学新星,另一个是路德维格·特劳伯 (Ludwig Traube) 后来成为德国实验病理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微尔啸接任当年,特劳伯创办了杂志《实验病理学刊》(Beiträge zur experimentellen Pathologie),发表了微尔啸早期一些文章,并预计将会有更多的论文随之刊出。但好景不长,这家杂志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另一方面,勤勉的微尔啸和莱因哈特所掌握的重要数据却在迅速累积,于是两位朝气蓬勃的年轻研究者大胆决定发行自己的杂志,于1847年创办了《病理解剖学、生理学与临床医学档案》 (Archiv für pathologische Anatomie und Physiologie und für klinische Medizin),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他们的杂志满足了医学界的迫切需求,受到热烈欢迎,至今仍是病理解剖学的顶尖杂志。由于莱因哈特的早逝,微尔啸成为唯一的主编,从此该杂志被简称为“Virchow’s Archiv”。
接下来的1848年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普鲁士政府派微尔啸去西里西亚调查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斑疹伤寒。他的报告详细地报道了当地居民的不幸和糟糕的医学及社会现状,但由于思想上过于民主而为当权者所不容。撰写报告的同时,不知疲倦的微尔啸还参与出版了一家半政治性的杂志《医学改革》 (Die medizinische Reform), 同情当时的革命运动的观点。这对于当局来说就太过分了,于是年轻的病理学家微尔啸被免职了。
在柏林刚被免职,他立刻便受到维尔茨堡 (Würzburg) 大学的邀请,前往担任病理解剖学教授,这是该学科在德国的第一个正教授职位。接下来的七年硕果累累,细胞病理学诞生,维尔茨堡成为德国病理学教学最炙手可热的大学,柏林则由盛转衰,于是在穆勒的影响下,柏林大学设立了病理解剖学正式教授之位,并邀请微尔啸回来任职。微尔啸离开柏林的头三年,柏林大学的解剖员一职由他的老朋友本诺·莱因哈特担任,莱因哈特过世后黑姆斯巴赫 (Hemsbach) 的海因里希·梅克尔(Heinrich Meckel,1821 – 56)接着任职四年。回到柏林后,微尔啸成为新成立的病理学研究所的所长,主要精力也投入到研究所的博物馆里,在此潜心工作,终成世界一流的病理学家。
《细胞病理学》是他本人的讲稿汇集,也是他在这一新时期的首批出版物之一,但现在看来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研究。早在当弗罗里普助手的时候,他就明确反对过当时盛行的克吕韦耶的静脉炎学说,即静脉炎症是大多数病理损伤的原因。而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来自于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如讨论血栓形成和栓塞的经典著作(1846),解开脓血症产生之谜,以及关于炎症的重要观点,同时微尔啸也发现白血病。
生命体内血液在血管中的凝固早已不是新鲜事,由于这种情况在炎症中经常出现,使得约翰·亨特和克吕韦耶都将两种过程密切联系起来。克吕韦耶甚至极端地认为所有炎症皆始于某种形式的血液凝固,并寄希望于一种“毛细管静脉炎”假说,以解释炎症时静脉中常常无明显凝块的情形。然而与之矛盾的事实不断出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观察到有凝血的情形中常常未能检测到炎症,微尔啸即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的研究。
他首先将各种血管内凝血的现象统称为“血栓形成 (thrombosis)”,接着以对尸体的观察为基础进行推导,并辅以实验验证,最终作出结论:静脉炎症既不是静脉腔内凝血的原因,也不是其结果。血液的凝固由一组与之完全不同的因素导致,其中血液流速变慢是当时所能发现的最重要原因,可由压迫、异常扩张、病人身体虚弱或其他原因引起。子宫周围的血栓给在巴黎感染的产科病房工作时的克吕韦耶留下深刻印象, 微尔啸认为这种情形是扩张引起的。在他漫长而活跃的人生的晚年,微尔啸不得不对这一最初的理念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改和补充,但它已为新学术思想的开始扫清了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居功至伟。
微尔啸对身体某部位的血栓形成常常伴发肺脓肿现象进行研究。 血块中心部位的软化给他提供了线索。他向学生指出,血块形成后不久,其中心会出现多少有点类似于脓液的物质,这种软化能够并经常引起凝块碎片的脱落,脱落的碎片可随血流移动到相隔远端的血管,如果较大碎片堵住肺部的主要动脉则将引起猝死,较小碎片则后果较轻。脱落的碎片不论大小一律被他命名为“栓子 (emboli)”。
由于无法找到客观证据证明肺部“脓血症”的脓肿中存在小栓子,他转而借助法国的路易斯所擅用的统计学方法,通过研究近期一次严重的产褥热暴发中的大量病例,确认了他的想法,即这些损伤具有“转移”性。子宫周围的静脉中存在软化的血栓时病人常常并发肺部脓肿,而在同样严重的病例中,如果炎症仅限于子宫淋巴管,则肺部脓肿一般不会出现,这一事实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证明自发现之日起就像谜一样困扰着医生们的脓血症,只是简单的一个炎症部位的固体颗粒直接通过血流转移到另一部位的结果,或者用微尔啸的说法,“栓塞”。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他一直不了解这些继发性损伤或转移所具有的感染性,只是简单地指出,如果原发部位的病况往好的方向发展,则栓子和血栓一样转化为瘢痕组织和色素,但如果最初产生凝块的部位发生坏疽性软化,则转移性的沉积物“具有同样的坏疽性,就好像接种过坏疽性物质一样”。在同样的基础上,他清楚地描述和解释了分散的脓肿与心脏瓣膜疣状赘生物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梨状血栓”、脓液、“脓细胞”及它们与血液中白细胞的关系时,微尔啸很早(1845)就在他的研究中偶然发现了血液中白细胞大量增加这一毫无关系的现象,并称之为“Weisses Blut”或白血病。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就在同一年,休斯·班尼特 (Hughes Bennett) 也独立描述了这种疾病。这种异常与炎症在表面上的相似性是一位柏林医生指出的,当时微尔啸正打开了一名死者的心脏,这位医生突然惊叫:“哎呀,怎么有脓肿!”微尔啸很快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白血病,并第一时间将它们与自己的血液生成研究统一了起来,生理学家微尔啸总是不甘落后,与病理学家微尔啸齐头并进。他注意到,其中一种白血病的患者脾脏增大严重,淋巴结增大程度较轻,另一种的患者淋巴结大得惊人,在一个病例中甚至占满了骨盆以至于直肠和膀胱几乎看不见,而脾脏则只是轻微肿大。他还注意到,两种情况下血液中的白细胞也是不同的,第一种细胞体积大,“类似于脾脏细胞”,第二种体积小,基本只含有细胞核,整体上像淋巴结内的普通细胞。我们对脾脏型(或现在所说的脾脏髓性)和淋巴型白血病的区分最早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且自微尔啸首次描述后几乎没有修改。
这些研究都反复提及炎症,微尔啸对该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松懈。这是病理学中一块巨大的暗礁,一直以来的所有理论体系都在此触礁沉没。二十五年前,彻底灰心的安德拉(Andral)曾建议放弃把炎症当做一个研究实体的观念。微尔啸认识到刺激是炎症的恒定诱因,他表示无法想象不受刺激而发生的炎症,当然,在细菌学诞生之前,他对这些刺激物的本质一无所知。他十分草率地摒弃了著名的炎症四个基本症状,另以身体局部的营养障碍为基础,将“功能损伤”定为炎症的主要特征。接着他继续提出了“炎细胞”的概念,并认为这种异常是在原始因素刺激下,细胞在血管或其他变化的影响下过多地吸收了液体及相关的物质所致。因此他把组织的一种异常状态,现在称“混浊肿胀”或“胞内水肿”的异常作为炎症的核心要素,而这也可以发生于其它情况并且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再次探究了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眼角膜炎症,以这种没有血管的结构证明他的论点: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炎症时血管变化其实是次要的。他的有关炎症的这些观点直接导致《细胞病理学》的诞生,我们现在可以来谈谈这部著作了。
作为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微尔啸就推翻了罗基坦斯基精心构想的体液病理学系统。发表在1846年12月9日和16日《柏林医学杂志》(Berline medizinische Zeitung) 上的批评文章迅速获得了约翰内斯·穆勒的大力支持,甚至立刻在维也纳得到认可。用半个世纪后微尔啸自己的话说,“Die Krasen sind nicht wieder auf dem Markt der Wissenschaft erschienen”。病理学的最后一个理论系统也覆灭了。
《细胞病理学》不仅仅是对之前体系的一种替换,也不是微尔啸自己构建的新系统,它是简单的,但早期认识的一个原理,即所有生物学说得出的共同结论——生命是由细胞组成的。前面我们看到,施旺在施莱登的指导下已证明了有机体都由细胞构成,他的导师约翰内斯·穆勒对此也是全力支持;距离真相的大门只有一步之遥,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正是微尔啸发现的,他认识到细胞生命的连续性,留下不朽箴言:“所有细胞都来源于最初的那一个 (Omnis cellula e cellula)。”施旺本人所持的观点:细胞是由一种来自原始体液的重复自动产生的,这也正是罗基坦斯基接受的理念。微尔啸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这种思想,历史性地向所有人阐明,一个细胞产生另一个细胞,就像人和植物一样一代代地繁衍生息。
他将人体看作细胞的一种有组织状态、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每一个微单元都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接着以这种正确的理念为基础重建了病理学。新的知识使病理学的所有领域都焕然一新。炎症、肿瘤生长、变性等等至此都可以从细胞关系的角度进行认识,而在这些领域中,微尔啸本人都是变革的领路者。当今的医生很难体会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场革命,一个从学生时代之初就以细胞学的思维方式学习解剖学、胚胎学、神经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各个阶段的人,无法想象没有细胞存在的医学将是何模样。今天的我们都是细胞病理学家,却把先驱微尔啸的细胞学当作与生俱来理论。
微尔啸是研究组织细胞变性领域的先锋。他首次区分了“脂肪浸润”和“脂肪变性”,并启动了坏死或组织死亡的组织学研究。他创造了“淀粉样变性 (amyloidosis)”这一新词以表示一种像淀粉一样遇碘则颜色变深的病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讨论,这种病变之前一直被描述为“脂肪状变性 (lardaceous degeneration)”。他在术语学方面很有想法,坚持认为“过分遵守(传统和旧的术语)是一种错误,因为它容易造成混淆”。他自己引进了许多新词,包括“实质性炎症”、“血栓形成”、“栓子”、“骨样组织”、“白血病”和“淀粉样变性”。
微尔啸的言语率直,从不含糊其辞,因此他会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他有生之年,他对炎症、血栓性静脉炎、肿瘤和结核病的观点就已历经修正或完全推翻,细菌学的诞生更是引发了一连串他不可能预知的改变。虽然他对结核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其实从未将这一主题真正厘清。他发现了至少两种结核病,并对法国学派得来不易的启迪提出了强烈抗辩。这两种分别是(1)炎症后状态,等同于雷奈克所描述的“结核浸润”,以及(2)真性结核或以结节为组成单位的结节状结核。另一方面,他在《细胞病理学》当中绘制了一幅精美的结节的组织学图片。后来,感染性病因的发现最终将不同的结核类型统一了起来,这碗苦水着实让微尔啸难以下咽,因此,这位老斗士一直无法和伟大的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亲切相处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信念的力量让他在癌症的本质及其扩散这一主题上立场坚定,他对此的观点却完全不像一个发现了细胞连续生长规律及栓塞的人所应持有的。肿瘤与炎症一样,一直是他的关注所在。关于新生长的系列书籍具有不朽的价值,是他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其理论与他的细胞病理学密切相关。他将所有的肿瘤或新生物分为同源和异源两类,同源性是指已有的细胞体积或细胞数增加的结果,而异源性则是由改变特征的新型细胞增生而成。他举例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常见的子宫“肌瘤”是子宫中的良性肿块,组成它的肌肉与正常器官的类似,因此为同源变化,而癌症、结节以及各种炎症都是异源变化。
他把近于良性的皮肤肿瘤看作是同源型,恶性的为异源型,并认为其中最基本的变化是皮下结缔组织的转变,或用我们现在的说法--间变。他坚信每个细胞都是已存在细胞的直接后代,但也毫无障碍地接受细胞转化的概念。因此,作为胚基的替代物,他早年认为结缔组织是癌症的基质,当时的同行也将大量所谓的证据呈献到这位大师的手中。
关于癌症转移,即新部位或器官的继发癌症,他的观点出人意料。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很可能是栓塞引起的现象,只是同时对一个事实无法释怀,即转移常常发生于血液循环直接通路以外的部位。例如,继发的癌结节常见于肝脏和骨骼而不是肺部,而原发肿瘤所在部位的血液却必然会将肿瘤颗粒物质直接带到肺部。因此他表示:“正相反,转移性扩散发生的方式似乎有这样一种可能,即转化通过某些液体发生,这些液体能够造成感染,使不同部位复制出与原发性肿瘤性质相同的肿块, 就像银盐不会在肺部沉积,而只是路过,只有在到达肾脏或皮肤时才会沉淀一样,从癌症肿瘤流出的腐液也可能在经过肺部时不造成任何改变,另在更远端的地点,如相距很远的某处骨骼发生恶变。”
我们不能忘了,细胞病理学创立之初,可供微尔啸使用的工具就只有显微镜——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精良的仪器了,用剃刀他可以手工切出比较薄的切片,以及最简单的染色剂。他没有享受过后来改良的超薄切片机,也不曾获益于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十分好用的固定和染色方法。因此,他的肿瘤病理学仍留在雷马克(Remak)、蒂尔施(Thiersch)、瓦尔代尔(Waldeye和比尔罗特(Billroth)来重建和纠错。
罗伯特·雷马克(Robert Remak,1815 – 1865)是微尔啸在查理特医院的同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思路清晰、想法独立的细胞病理学家,当时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微尔啸。他很快便通过成熟的组织学技术证明了皮肤癌来源于表皮而不是结缔组织。埃朗根(Erlangen,德国城市)的外科医生卡尔·蒂尔施(Carl Thiersch,1822 – 1895),在没有切片机的情况下,他仅利用优质的剃刀和氨化胭脂红及靛蓝染料就制备出不同器官肿瘤的有色连续切片,确证了上皮肿瘤源于上皮(1865)。威廉·瓦尔代尔(Wilhelm Waldeye,1836 – 1921)是伟大的组织学家亨勒的学生,也是最杰出的现代解剖学家之一,他确认了内部器官上皮肿瘤也来源于上皮。此后,他专注于肿瘤转移的研究,通过大量观察证明癌症转移可经由直接蔓延和淋巴管、血管栓塞两种途径(1867 – 1872)。在肿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直接研究的比尔罗特(Billroth,参见第185页)也支持这些观点。而某些器官能从肿瘤的栓塞性转移中幸免这一事实,之前曾令微尔啸放弃了栓塞理论,现在也尚无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一般认为某些部位的“土壤”较之其他部位更适于肿瘤的生长,这种观点最早在1877年由孔海姆 (Cohnheim) 提出。
微尔啸为病理学做出的其他次要贡献不计其数,这里篇幅有限,不能详述。他关心生物科学的每一点进步,但接受这些新知识却非常谨慎。他拒绝接收大量涌现的细菌学报告,同时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因此在当时就颇受责怨。这些过失令他与自己的学生爱德温·克勒布斯 (Edwin Klebs) 及进化论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 – 1919)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人们责怪他顽固偏狭,但这何尝不是因为他难能可贵的谨慎呢。他所不认可的多种新细菌和一些进化的观点后来都被撤销,时间对他的审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他兴趣广泛,孜孜不怠,所涉猎的领域远不止医学。他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作为一名国会的议员发挥重要的作用。医学以外,他在科学方面的最大兴趣是人类学,在此领域硕果累累。虽然说到底只是一个副业,他也像对待病理学一样,非常热忱和认真。
虽然身材瘦小,他在学生心中的形象却是令人敬畏的。他是一名严厉的考官,有时几近冷酷,但如果应试者了解他的话,就会知道他要求的其实很少。他并不反感学生犯错,他本人犯的就不少;也不指望他们能描述大量的知识细节。他只需要考生证明他们具有独立观察的能力,并了解自然最基本的法则,即生物学真正的基础原理。他认为只要具备这样的基础,学生就能够搭建自己的框架,所有的细节都不会是问题。而他那些伟大的学生们也都不负所望,孔海姆(Cohnheim)、克勒布斯(Klebs)、雷克林豪森 (Recklinghausen)、林德弗雷斯 (Rindfleisch)、彭费克 (Ponfick)、奥尔特 (Orth)、霍佩·赛勒 (Hoppe-Seyler)、赛科斯基 (Salkowski) 以及众多的其他人都完美地达成了他的期望,精益求精,层楼更上。通过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微尔啸的影响传承至今,仍然主导着病理学。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7-01 08:12:20 编辑
正如前面我们已看到的,施莱登、穆勒和施旺发现了细胞是有机体的组成单元,以此为基础,微尔啸重建了病理学。在这之前,这门学科的关注点几乎仅在机体器官的特定大体变化上,而从此以后,组织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就成为了病理学必不可少的分支。
微尔啸的病理学理论也推动了其它学科的发展。虽然比法国和奥地利较晚认识到细胞学说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但现在开始,德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病理学正教授席位,微尔啸建立的维尔茨堡和柏林研究所很快被这片国土上的所有顶尖大学复制。新的教授职位最初主要由微尔啸和罗基坦斯基的学生担任,但它们发展迅速,不久便能够独立自主,于是很快“海德堡学院”、“布雷斯劳学院”等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改革进行得相当顺利。在一个大多数公共事业受国家控制的国度,将医院太平间改造成大学的病理学研究所是很容易的事情,医院的解剖员和学校的教授成为同一个职位。这一新的激励导致尸检频次大幅增长。世纪结束前,小型大学城每年进行的尸检多至千例,在柏林则达到五六千。材料的丰富进一步促成了病理解剖学观察范围的大幅拓展。
这段时期其他国家的进步就显得比较迟缓了。世纪前三分之一引领学科潮流的法国病理学如今开始停滞不前。在普法战争中失去斯特拉斯堡的同时,法国也失去了欧洲病理学的第一把交椅。只剩巴黎独木难支的法国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病理学就是巴黎病理学,而德国病理学则是众多繁忙多产的大学所做贡献的总和。
此外,由于医院病房归属于巴黎大学医学系的某些教授,医院实际上并不受学校监管,尸检大都由实习医生进行,他们与学校病理系毫无关系,也少有继续这门学科的打算。世纪后半叶法国的主要贡献在神经和实验病理学方面。
至于英国,虽然一些杰出的个体对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比法国更加无视病理学自主发展的价值。多年以来,设有病理学教职的只有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即便在爱丁堡,许多人也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学术负担和花销,想方设法废除这一职位。在多数医学院,如盖伊医院附属学院,病理学教研大都仍由执业医生和外科医师负责,这种方式强调了紧密关联医学与病理学教学的必要性,值得嘉许,但时间与设备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问题的研究。
病理学进展的大潮奔流不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过了意大利北部、巴黎、伦敦和维也纳,而今涌向德国。同时期组织学在德国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形成。这方面的进步主要在技术上。大体解剖学凭借手术刀和其他一些常见工具取得了进步,显微解剖学的发展则迫切需要一套精密的装置和程序。十九世纪前几十年,人们对新鲜组织进行手工切片,不经染色,直接在显微镜下检查。而世纪末,他们用合适的液体使组织硬化,将其包埋在硬质材料中以便切割,接着利用切片机切出极薄的切片,并以复合染料染色,使不同的细胞成分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在病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这里将用几个段落对组织学技术史进行介绍。组织学诞生于马尔皮基之时,其后缓慢发展,至比沙发现各种组织类型时取得一次飞跃,在吸纳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后进入全盛期。
即便比沙不屑一顾,显微镜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机械辅助设备。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得到了极大的改进,这主要归功于配有消色差物镜的现代复式显微镜的发展,其设计者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 (Joseph Jackson Lister) 是一名伦敦酒商(也是外科医生洛德·利斯特 (Lord Lister) 的父亲),利用闲暇钻研科学。后来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é) 又添加了著名的聚光器,并改良了目镜和物镜。在此期间,显微镜还得到了其他多项改善,显微镜学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在包括解剖学在内的多个领域变成了必不可少的仪器。
随着光聚焦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解剖学研究对更薄的组织切片的需求也愈加强烈。但是,除了软骨和骨骼以外的其他组织都过于柔软,难以获取良好的切片。为克服这一困难,人们提出了一些办法,冰冻法就是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率先使用该法的似乎是荷兰的皮特·德·莱默尔(Pieter de Riemer,1760 – 1831),在他之后,这种方法在多数早期的显微解剖学家当中都有所应用。卡塞尔(Cassel,德国城市)的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本尼迪克特·施蒂林(Benedict Stilling,1810 – 1879)就大量运用了冰冻法,尤其在1843年他对中枢神经系统组织学的经典研究中。最初的冰冻法一般是将盛有待切材料的容器浸入冰冻的盐水混合物中,经过多次改良后,现在的冰冻法以乙醚或压缩二氧化碳能够快速蒸发的特性为基础,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
其他人则满足于使用剃刀徒手切片。装有两片平行刀片的刀具十分有效,曾任伯尔尼大学生理学教授四十五年的生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古斯塔夫·瓦伦汀(Gabriel Gustav Valentin,1810 – 1883)使用的就是这种刀具。其方法是将两片刀片紧贴在一起,用螺丝固定,快速切入或拉出组织,从而获得薄的切片。
然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当下最需要改善的是支座的稳固性,于是便有人设计了机械切片机。第一台兼具移动中刀的机械精度和待切材料的机械控制这两个关键特征的超薄切片机的发明,要归功于巴塞尔的胚胎学家威廉·伊斯(Wilhelm His,1831 – 1904),他利用这台仪器完成了有关小鸡发育的伟大研究。然而,这之前已经有郎飞切片机和其他法国切片机存在,它们比较简单,也一直更为普及。许多在大学任教的生物学家很快发明了新的改良版,然后由学校的技术员完成机械细节的制作。最好的早期切片机之一是德国病理学家理查德·托马 (Richard Thoma) 设计、海德堡技术专家荣格 (Jung) 制造的版本(1881),最现代的切片机就是以此为模型制作的。
但是,除冰冻切片以外,这套新的程序需要某种基质将组织包埋固定以便于切片。一开始人们只是简单地将组织置于在松软组织中刻出的狭槽里,后来海登海因 (Heidenhain) 提出使用阿拉伯树胶,所罗门·斯特里克 (Salomon Stricker) 引进了一种蜡和油的混合物。至今仍具有宝贵价值的石蜡包埋法的引入,则要归功于多个领域的非凡开拓者——爱德温·克勒布斯 (Edwin Klebs)。在自己的实验室使用了一些年后,他于1869年描述了这种方法。十年后,马赛厄斯·杜瓦尔(Mathias Duval,1844 – 1915)引进了火棉胶珂罗酊 (collodion),又过了不久,德国的默克尔 (Merkel) 和西弗德克 (Schiefferdecker) 提倡使用火棉胶的一种商业变体赛珞锭 (celloidin),赛珞锭和石蜡同为今天普遍使用的包埋基质。
硬化和脱水---是最好的包埋程序所必需的步骤。乙醇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用来硬化组织,现在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脱水剂。用于固定组织的铬酸溶液的引入(1844)要归功于哥本哈根的阿道夫·汉诺威(Adolf Hannover,1814 – 1894),他也是约翰内斯·穆勒的学生。原始溶液的各种变型很快得到应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沃尔特·弗莱明(Walther Flemming,1843 – 1905)推出的铬酸-锇-醋酸溶液。弗莱明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学家,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细胞概念都出自他对细胞核及其分裂的精湛论著(1882),他接着微尔啸的箴言写道:所有细胞核也都来源于最初的那一个细胞核 (Omnis nucleus e nucleo)。1894年康拉德·岑克尔 (Konrad Zenker) 发明了由重铬酸钾和氯化汞混合而成的“岑克尔液”,他宣称这种固定液十分有效,而这已经在大量的应用中得到证实了。
福尔马林溶液的应用始于1893年,最早的提倡者包括(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医生F. 布鲁姆 (F. Blum)、他的父亲J. 布鲁姆 (J. Blum),以及F. 赫尔曼 (F. Hermann)。两年之内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它的原始发现者之一不得不感叹他们的远见卓识被遗忘的速度之快。这种物质在大体组织的固定和保存上表现出同等的价值,也是几种著名的固定和保存液的主要成分,包括十分好用的凯泽林氏溶液。凯泽林氏溶液是一种固定液,1897年由卡尔·凯泽林 (Carl Kaiserling) 发明,当时他与微尔啸同在柏林。
第一种重要染色法的发明者是美因茨(Mainz,德国城市)的约瑟夫·格拉赫(Joseph Gerlach,1820 – 1896)。1847年他向组织的血管系统中注入氨化胭脂红(ammoniated carmine)与明胶(gelatin)的透明溶液,意外发现碱性胭脂红对细胞核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被后者大量吸收,于是他推广了这种核染剂,并在准备《人类形态学的微观研究》(Microscopic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Human Morphology,1858)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这种染料。微尔啸也在自己的工作中采用了它。今天使用最多的核染剂明矾苏木精是维尔茨堡的F. 博默 (F. Böhmer) 在1856年研究一个化脓性脑膜炎病例的组织时率先应用的。苯胺染料的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染色的范围,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少有人能超过保罗·埃尔利希 (Paul Ehrlich),他发现某些苯胺染料甚至能够安全地对活组织进行染色。
其他用于分辨组织的有效方法包括金属盐浸渍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冯·雷克林豪森(Friedrich Daniel von Rechlinghausen,1833 – 1910)建立的银浸染程序。雷克林豪森是微尔啸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任斯特拉斯堡病理学教授愈三十年。以他为开端,我们可以正式开始讨论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段的病理学进展了。他的成就中,如今最广为人知的是1881年发表的专题论文,他的名字因这部出版物而与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联系在一起,但这实则是他的次要成果,他的足迹几乎遍布病理学的每个领域。
他不仅是病理解剖学家,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实验病理学家。在对角膜炎症及脓细胞与“固定”组织细胞活动性的早期研究中,他使用的银浸染法和“湿盒”都是他本人的发明。这些研究先于孔海姆完成,给予了后者很大的启发(他的炎症巨著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孔海姆英年早逝后,雷克林豪森曾被邀请继任他在莱比锡的职位。
雷克林豪森是骨病理学的大师,他的研究包括纤维性或变形性骨炎、骨软化、佝偻病、某些癌症对骨生长的刺激、胎传性梅毒导致的骨膜炎,以及多种较少人知道的骨病,他还发现了其中许多疾病之间的关联。
他的其他重要研究包括血栓形成、栓塞与梗死形成(“球形”、“透明”血栓与“逆行性”栓塞),由他命名的血色沉着病,多种组织退化,以及他进行了详细胚胎学研究的子宫腺肌瘤。此外,他和学生们还发表了大量病理解剖学方面的次要观察发现,共同将斯特拉斯堡建设为欧洲最伟大的病理学研究所之一。
微尔啸的其他学生也与雷克林豪森不相伯仲。奥格尔格·爱德华·林德弗雷斯(Georg Eduard Rindfleisch,1836 – 1908)任波恩大学教授,他出版了一本很有价值的病理组织学教科书,从而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在这本献给比尔罗特 (Billroth) 的书的引言中,他不禁感慨,对于这样一门日新月异的学科,做一名与时俱进的教科书作者真是困难重重。他富有感情地写道:“如果有人在几年后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忘了作者发表这些观点的时间是1870年,我将有充分的理由抱怨。”
这的确是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微尔啸的《档案》载满新的发现,新的杂志也开始创刊。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选取少数几位工作具有主流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简要介绍。爱德温·克勒布斯(Edwin Klebs,1834 – 1913)的名字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这位卓越非凡的人物在世事的变迁无常中被迫远行,先后担任波恩、维尔茨堡、布拉格、苏黎世和芝加哥大学的病理学教授,在古稀之年缔造了成熟的细胞病理学与新生的细菌学之间的第一次连接。他本人也在这一新的领域做出了大量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特殊贡献,下章将对此进行介绍。
他最初接受的是微尔啸的传统形态学训练,后成为公开与老师争论学科基础的少数几人之一。他很早就认识到我们现称为传染病的这类疾病所具有的寄生性,并因此将病因学置于疾病研究的首位,而将他的老师坚定不移奋斗终身的病理解剖学摆在了次要位置。尽管如此,他本身仍然是最顶尖的病理解剖学家。
他充满热情,容易进入丰收在望的新领域,却很少能在研究中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他带给各个领域的刺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细菌学方面,连科赫也承认对他的感念。克勒布斯与瑙宁 (Naunyn) 和布克海姆 (Buchheim) 一起创办并主编了杂志《实验病理学与药理学档案》(1872),这是他率先探索的又一病理学领域。对心内膜炎感染性的调研(1878)是他的研究方向。
1872年雅尔玛·海贝格(Hjalmar Heiberg,1837 – 1897)研究发现心内膜炎可能是一种细菌性疾病。他是奥斯陆大学的病理学教授,著名海贝格医学世家的成员之一。在一名患溃疡性心内膜炎的产后妇女的心脏疣状赘生物中,他观察到了纤毛菌的菌丝并对此进行了描述。他的同乡E. 温厄 (E. Winge) 先前也记录了类似的发现(1869),称之为“霉菌性心内膜炎”。在这之前,赘生性心内膜炎与脓毒症之间的关系曾几次受到关注。
朱丽叶斯·孔海姆(Julius Cohnheim,1839 – 1884)是微尔啸队伍里又一位伟大的反叛者,他破除了关于脓细胞来源的传统观点。炎症领域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由于孔海姆的研究方法几乎完全是实验性的,所以对这一伟大进展的详细讨论将留到实验病理学一章。
作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病理学教师之一,孔海姆将被后世永远铭记。1872 – 78年当他在布雷斯劳(Breslau)任教授时,学生们大批涌向这里,后来他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职位,他们又跟随他去了莱比锡。他的《普通病理学讲义》(Vorlesungen über allgemeine Pathologie,1877)是继微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教学汇编。尽管这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作者本人的研究。
除了对炎症、栓塞和梗死形成的研究(将在后面的章节介绍)之外,孔海姆对恶性肿瘤起源的观点也闻名于世。他注意到多种先天畸形都可以追溯到胚胎发育过程中的意外或缺失,并由此产生肿瘤也可能有相似的来源的设想。他提出,相互之间关系正常的细胞具有有序生长的全部能量;当胚胎发育出现意外时,细胞可能与环境分隔,并在孤立的状态下保持休眠;如果后期某些刺激激活了这些细胞,它们将利用之前留存的生长活力增殖,形成肿瘤。
这一理论对恶性生长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基本上已弃之不用,但对畸胎瘤的理解仍很有帮助。波恩的雨果·李伯特(Hugo Ribbert,1855 – 1920)的著名学说可看作由孔海姆的观点变化而来。李伯特同样认为肿瘤可能由保留了独立生长能力的孤立细胞发育而来,但造成这种细胞孤立的原因不是胚胎发育中的意外,而是成年后由其他组织的不规则生长导致的细胞与其正常环境联系的分离;这些细胞在习惯的环境中保持正常,遇到新环境则可能异常生长。
某些类型的恶性生长倾向于在晚年发生,李伯特对此的解释与之前的蒂尔施和瓦尔代尔类似,以组织平衡状态的扰乱为基础,由于失衡,一种组织能够过度生长并排挤另一组织。这些理论对研究具有启发性,但人们最终发现它们不能够解释所有事实。
孔海姆最优秀的学生是卡尔·魏格特(Carl Weigert,1845 – 1904),他开启了人们对组织变性与坏死的认知之路。卡尔·魏格特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小城蒙斯特堡 (Münsterberg, Silesia),与孔海姆共事之前,他曾受训于微尔啸、海登海因、李伯特和瓦尔代尔,受到了他们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他在普法战争期间做了一小段时间的军医,随后进入布雷斯劳医学门诊,抓住机会对天花导致的皮疹进行了深入的显微研究。这项研究为他后来在凝固性坏死方面的伟大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使他获得孔海姆的注意,成为了他的助手。此后魏格特一直追随着这位伟大的实验病理学家,跟着他到莱比锡,任副教授,协助他完成巧妙实验的同时,也在形态学领域取得同样出色的成就。1884年孔海姆过世,魏格特却未获邀继任他在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对此他倍感失望。显然他的犹太人身份不能被人们接受;他的资历是公认的无可挑剔。魏格特迁到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近二十年始终保持着活跃的研究状态。他在工作中猝然倒下,死于冠状动脉血栓,享年五十九岁。
1871 – 2年的天花流行开启了他在两个重要领域的研究事业。彼时他还是布雷斯劳大学的医学助手,对细菌在接触传染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仅略懂皮毛,在组织学技术方面则已是专家,于是他将组织学的染色方法运用到寻找细菌当中。他使用了核染剂洋红,组织内细菌的第一次成功染色就是他的功劳。尽管所找到的细菌与天花之间只存在次级关系,但这一事件作为细菌学的里程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极大地促进了接下来的研究。
同样是在对天花的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这种未知的天花病毒对感染部位的皮肤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但同时也是高度局限性的。后来白喉方面的研究也支持他的早期观点。他精彩地描绘了受到这类损伤的组织状态及其发展过程,为此孔海姆造了一个新词“凝固性坏死”。随着研究的成熟,魏格特认为贫血性梗死是典型的凝固性坏死,“这一情况的发生要求组织本身含有可凝性物质,且在坏死的过程中可凝性的血浆液体仍能渗入,其间没有任何发酵变化或化脓情况发生来干预和阻止这一过程”。栓塞和梗死形成受到了他很大的关注,他也是第一个准确描述心脏梗死的人(1880)。
对组织变性的研究使他注意到修复的问题,尤其是与慢性肾炎、肝硬化和心肌纤维化相关的修复。他断定,每当上皮或类似组织遭到破坏,如果不出现化脓且间隙组织本身未完全受损,那么间隙结缔组织将过度生长。此认知当中,生长是其他组织受损的后续结果,这与微尔啸所教授的细胞生长只在受到直接刺激时才会发生的观点是对立的。魏格特强调修复过程中新组织的生长具有自发的过度性,后来他的表弟保罗·埃尔利希提出的著名的免疫学侧链理论即是以此为基础。
魏格特是一名技艺高超的技术员。他开发的组织连续切片法和细化的特殊染色不仅广泛应用于病理学,对普通组织学和神经学也同样大有裨益。他的其他成果当中,粟粒型肺结核的研究(1877 – 1886)大概是比较突出的一项,他提醒人们注意静脉壁内部的结节是该病病毒播散的来源。
同时期的恩斯特·齐格勒(Ernst Ziegler,1849 – 1905)出生在瑞士,是克勒布斯和林德弗雷斯的学生,一生中的黄金阶段是在弗莱堡任病理学教授之时。他对这门学科的深入影响不仅在于所作出的具体贡献,更在于对其组织结构的优化。全世界的当代病理学家中一大部分是读着齐格勒的《普通病理学与病理解剖学》 (General Pathology and Pathological Anatomy) 成长起来的,这部伟大的教科书出版于1881年,历经多次再版与翻译,至今仍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之一。他创办了两家杂志并担任主编,分别是《病理解剖学与普通病理学通告》(Beiträge zur pathologischen Anatomie und allgemeinen Pathologie,1886,又称“齐格勒的通告”)和《普通病理学与病理解剖学中心期刊》(Centralblatt für allgemeine Pathologie und pathologische Anatomie,1890),它们的影响力仅次于微尔啸的《档案》。作为研究者,齐格勒主要关注疾病的诱因,以及炎症、炎性新生长和修复,即身体的防护力。
德国病理学这段伟大进程的其他参与者在此只能略提几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岑克尔(Friedrich Albert Zenker,1825 – 1898)是德累斯顿(1855 – 1862)和埃朗根(1862 – 1895)大学的教授,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关于伤寒症中某些骨骼肌蜡状变性的专题论文。此外,他在旋毛虫病、粉尘吸入及脂肪栓塞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是最早描述脂肪栓塞的人之一(1862)。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的恩斯特·诺伊曼(Ernst Neumann,1834 – 1918)一生高寿而活跃,他在组织受损后的再生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观察发现,对骨髓的重要开拓性研究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白血病的理解。朱利叶斯·阿诺德(Julius Arnold,1835 – 1915)使海德堡成为德国最顶尖的病理学院校之一,他本人的重要研究包括核分裂与细胞分裂、粟粒性结核结节的精细解剖(1880 – 2),以及粉尘和金属颗粒的吸入对机体的影响(1885 – 90)。
苏黎世的卡尔·约瑟夫·埃贝特(Carl Joseph Eberth,1835 – 1926)也是一位长寿的著名病理学家,他与学生舒密尔布施 (Schimmelbusch) 共同完成的对血栓形成的研究实验,揭示了血流停滞的重要影响以及血小板在凝血中所起的作用,确认了之前都灵的朱利奥·比佐泽罗(Giulio Bizzozero,1882)和巴黎的临床医生、血液学家乔治斯·海姆(Georges Hayem,1882)提出的关于血小板的言论。埃贝特作为伤寒杆菌的发现者(1880)可能更多人知道。埃米尔·彭费克(Emil Ponfick,1884 – 1913)是雷克林豪森和微尔啸的学生,以确定人类放线菌病的病理性质(1880)著称,对于这种寄生物,人们此前已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奥托·博林格(Otto Bollinger,1876)和奥斯卡·伊斯雷尔(Oscar Israel,1878)。该病曾被当作一种恶性肿瘤。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1847 -)终身研究动脉疾病,他以通向胎盘的血管在分娩后发生的生理性硬化为依据类推,提出了动脉硬化的一种解释,是病理学中对此最令人满意的解释之一,其中心思想是血管内膜的硬化是对中层衰弱的一种补偿。托马另以对血细胞计数设备和切片法的技术改进闻名。约翰内斯·奥尔特(Johannes Orth,1847 – 1923)1902年接替微尔啸成为柏林大学的病理学教授及微尔啸的《档案》杂志主编。
在此期间,法国的病理解剖学停滞不前,只有一个领域除外,即让·马林·沙尔科(Jean-Marin Charcot,1825 – 93)领导的神经病理学。沙尔科在巴黎的妇女救济院管理着最顶尖的现代神经科门诊。他受训于古老的巴黎病理解剖学系,也曾担任该系教授,因此将病理学的视角带到了神经学的研究当中,获益良多,解释了这一艰深领域许多疑难的临床现象。他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对多发性硬化相关症状的解剖学阐释,他将该病最早的解剖学描述归功于克吕韦耶和卡斯韦尔。他对运动性共济失调症的骨髓进行了准确的组织学研究,将首次描述归功于胡丁(Hutin,1827),并直言宣称这一主题整个都是“法国的战利品”和“雷奈克开创的解剖病理学纪元的一部分”。沙尔科本人描述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损伤并对其症候群进行了解释。由中枢神经系统的某些疾病导致的关节病至今仍被称为“沙尔科氏关节”。
沙尔科与维克托·科尔尼 (Victor Cornil) 最早论证了小儿麻痹症中脊髓前角的萎缩,杜申(Duchenne,1806 – 75)曾预测了这种现象。此后不久维尔皮安 (Vulpian) 和普雷沃斯特 (Prévost) 指出了运动神经细胞的损伤(1866)。维尔皮安的学生朱尔斯·德热里纳(Jules Dejerine,1849 – 1917)对脊髓疾病做了全面而精湛的研究。德热里纳是法国人,在瑞士出生,他很早就对神经病理学产生兴趣,最终继承沙尔科成为妇女救济院的第二位神经学教授,尤以对不同类型失语症脑损伤的定位著称。他的成就来自于对病变区域进行的最认真细致的组织学检查。德热里纳和沙尔科学派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纠正了关于大脑中枢定位的错误推断,这些错误起因于人们无根据地将实验动物的结果应用到人体上,自威利斯时代开始一直累积到当时。
皮埃尔·马里 (Pierre Marie) 是沙尔科最出色的学生,他在1885年描述了肢端肥大症,1886年提出了垂体与该病的相关性,其依据包括本人和其他人的尸检发现。事实上巨人症与垂体增大之间的关系此前已多次有人提及,这其中就包括病理学家爱德温·克勒布斯,他与临床医生弗里斯彻 (Fritsche) 合作,在1884年发表了一个病例的完整描述,其显著特征包括体型庞大、尤其明显的颅骨扩增,以及脑垂体增大。然而,该患者出现的迁延性胸腺扩大却令他们疑惑不解,直到后来马里确定了这一现象与垂体之间的病因关系。
1890年马里首次描述了肥大性骨关节病,从此该病就冠上了他的名字。他是沙尔科的忠实弟子,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病理学研究中延续了导师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马里在神经病理学和无管腺生理异常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两个领域基本上都处在法国的领导之下。后一学科的两位领头人物分别是贝尔纳·伯纳德 (Claude Bernard) 和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色夸 (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他们在前一领域中也同样有突出的作为。鉴于二人的工作大都是实验性的,这部分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
这一时期法国顶尖的组织学家查尔斯·菲利普·罗宾(Charles-Philippe Robin,1821 – 1885)通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细解剖研究,对法国神经学的伟大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沙尔科同为重要杂志《人类和动物的正常生理与病理解剖学刊》(Journal de l’anatomie et de la physiologie normales et pathologiques de l’homme et des animaux,1864)的创办人。
英国病理学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过,其教学与发展都倚靠能干但忙碌的内外科执业医生,而两个领域的临床医生也都做出了大量的重要贡献。威廉·格尔爵士(Sir William Gull,1816 – 90)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盖伊医院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可以和法国神经病理学派领军人物的成果相匹敌。他是最早准确描述运动性共济失调(或脊髓痨)中脊髓损伤的人之一,对大脑动脉瘤也有精彩阐述。然而,他最伟大的成果,应该是发表于1872年、与亨利·高恩·萨顿 (Henry G. Sutton) 共同完成的对慢性肾炎中“动脉微血管纤维化”的研究,这是对小动脉硬化性肾萎缩的首次清晰描述。虽然格尔和他的同事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慢性肾炎和小动脉性肾硬化症进行区分,但他们十分恰当地强调了肾萎缩与小动脉普遍性增厚的关系,其中后者被他们介绍为著名的动脉硬化的一种特殊类型。
对手医院及医学院圣巴瑟罗缪 (St. Bartholomew) 的外科医生詹姆士·佩吉特爵士(Sir James Paget,1814 – 99)极大地促进了外科病理学的发展。他于1851年出版《肿瘤讲堂》 (Lectures on Tumors),1863年出版著作《外科病理学》 (Surgical Pathology)。1871年一次尸检时的伤口感染使他在三个月里丧失行动能力,他因此受到启发写了《解剖的毒性》 (Dissection Poisons) 的专题论文和讲义。有两种疾病以佩吉特的名字命名,以表彰他的首创性描述,分别是湿疹样乳癌(1874)及畸形性骨炎(1877 – 82)。
外科医生本杰明·布罗迪爵士(Sir Benjamin Brodie,1783 – 1862)和乔纳森·哈钦森爵士(Sir Jonathan Hutchinson,1828 – 1913)也都推动了外科病理学的进步,值得一提。布罗迪在骨和关节疾病方面有重要观察发现,哈钦森尤以研究先天性梅毒引起的皮肤红斑闻名(慢性角膜炎,切牙缺口,内耳疾病,一般合称“哈钦森三联征”)。
而在这时的美国,病理学才刚刚启航。在这里,医学的早期发展大都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中心,在其教务长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1843 – 1898)的领导下,美国医学教育的许多先例逐渐建立了起来。佩珀编纂了第一部大型的《美国医学系统》(American System of Medicine,1886)。在病理学中,他以最早描述恶性贫血中的骨髓变化(1875)著称。这一疾病自1855年艾迪生的描述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872年苏黎世的比尔默 (Biermer) 再次描述了它。孔海姆在对佩珀的描述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876年研究比尔默一个病例的组织时提到了骨髓的变化。诺伊曼、瓦尔代尔和彭费克在白血病方面的工作,以及孔海姆对真假白血病的辨别(1865)给佩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阐述恶性贫血的优秀论文中总结:“脾脏、淋巴腺和骨髓等主要造血组织的功能障碍”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根源。
继塞缪尔·格罗斯 (Samuel Gross) 后美国第一本重要的病理学教科书出自弗朗西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1841 – 1915)和特奥菲尔·米切尔·普鲁登(T. Mitchell Prudden,1849 – 1924)之手,二人分别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的医学实践教授和病理学教授。该书自1885年问世以来已多次再版。
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1849 – 1919)和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1850 – 1934)对美国病理学影响更大。奥斯勒出生和受教育都在加拿大,他将最优良的英国学术传统带入了美国医学,并有着超常的教学能力。他先后任教于麦吉尔、宾夕法尼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新大陆杰出的内科学教师。他强烈认识到理解病理学对于医学进步的绝对重要性,本人对这一学科也做出了许多小的贡献。威廉·韦尔奇长久以来被尊为美国病理学的教务长,他的主要成就在实验病理学领域,将在后面的章节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翻开华丽的一页,进入使病理研究产生重大转折一段历程——细菌学的兴起,它与本章记述的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7-02 08:33:49 编辑
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病理学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病理组织学的延伸和实验生理、病理学的进步,更是由于病原学的重大发现。新兴的细菌学解决了某些困惑了医学界二十个世纪的重要问题。
传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人们自古就对此有明确的认知。鼠疫与梅毒所表现出的明显传染性就不可能被忽略。外行如薄伽丘(Boccaccio,1358)和笛福(Defoe,1722),他们广为流传的作品中就包含了关于鼠疫的医学观念。弗拉卡斯托罗论传染的著作和他对梅毒的专门研究,以及其后关于这一主题数以百计的论文,都明确了梅毒传播所具有的传染性。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可怕灾祸麻风病也被认为是可传染的,而隔离措施的有效性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确曾将传染归咎于活的病毒,并进行调查研究以验证这种关于活触染物的猜测,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和安东尼·冯·列文虎克(参见第四章)就在他们简陋的显微镜下发现了肉眼不可见的生物。
十八世纪早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染性疾病特有的临床表现以及它们所提示的传染方式。特异性传染与免疫学说的先驱、英国乡村医生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1654 – 1734)用别具一格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观点:“鼠疫是不会引起天花的,天花也不会导致麻疹,它们更不会产生水痘,就像母鸡不会生出鸭子,狼不能生羊,蓟不结无花果;因此患了一种疾病也不可能防止其它疾病的发生。”
同样,免疫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古人意识到患了某些疾病后会对之后的再次发作产生防护作用。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就实际应用了这一知识,他们通过接种脓疱物质有意将天花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由此导致的病状较轻,但能对此后的自然传染产生免疫作用。这种“人痘接种”的方法后来在整个文明世界得到了广泛应用。
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 – 1823)引进疫苗接种,真正免疫学的基础才随之建立起来。詹纳是一名英国医生,也是约翰·亨特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他发明的天花免疫法同样有效且比“人痘接种”安全得多。当时的英国农村流行一种说法,正如一名奶场女工所述:“我不会得天花,因为我曾患牛痘。”受到启发的詹纳决定通过直接试验来验证其真伪。1796年五月他将一名挤奶女工手臂上的牛痘浆液接种到一名健康男孩身上,接着在七月给他接种真正的天花病毒,结果这名男孩没有感染天花。
这一试验通过诱发一种无害的损伤来预防相似但十分严重的疾病-天花,其预实验的成功为更大范围的重复验证提供了依据。1798年詹纳发表了首批二十三个案例的研究,并根据注射物的来源(vacca,牛)将这种方法命名为“疫苗接种 (vaccination)”。其价值立刻得到认同,人们在欧洲和美洲开始了大规模接种,一度几乎传遍全球的天花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所有文明社区的罕见病。除了霍姆斯和泽梅尔魏斯(第八章)强调的分娩时单纯的清洁之外,医学中再没有别的预防法曾取得与此同等的成功。
詹纳这一成就丝毫不逊于麻风和鼠疫中隔离措施所取得的成果,这是经验和推演所得出的结果。在詹纳的时代,传染病的控制上要想取得进一步科学进步所需要的仪器和方法尚未出现。只有当显微镜经过改良后,这种进步才可能实现,而如果没有化学合成染色剂的辅助,即便有显微镜也只是徒劳。
微生物的发现也仅是跟上了工具发展的步伐,人们在显微镜下发现的首先是相对较大的寄生虫,很久之后才是更小的细菌。1810至1830年间,著名的消色差透镜问世,此后不久人们就逐渐发现了较大的寄生虫。 1839年柏林临床医生约翰·卢卡斯·舍恩莱因(Johann Lucas Schönlein,1793 – 1864)找出了黄癣的病因,1842年他的助手雷马克用舍恩莱因发现的微生物使自己患上了这种疾病。其后不久人们陆续发现了其他的皮肤寄生虫;同时也发现了与曲霉病和放线菌病有关的真菌。这期间,意大利医生阿戈斯蒂诺·巴锡(Agostino Bassi,1773 – 1856)已明确显示了某些微生物与蚕僵病之间的因果关系(1837),并预言天花、鼠疫、梅毒和其他人类疾病的致病菌来源于动植物。
巴锡工作的重要性立即获得了德国的亨勒的认可,在别的许多地区也同样迅速地被人们接受。事实上,关于疾病中存在微生物传染的意见不断涌现,其速度之快令亨勒感到必须对大量累积的推测设定一些限制,尽管他曾预言微生物学将为病理学中许多病因不明的疾病带来光明。在著名论文《论瘴毒与传染》(On Miasms and Contagion,1840)中,他制定了微生物与疾病之间病因关系成立的基本条件,后来科赫将此拓展为细菌学的基本法则。亨勒总体上强调了(1)须证明某种疾病与其假定的病原寄生物恒定相关,且该寄生物不存在于其他疾病中;(2)须能获取该寄生物并将其与其他微生物分离;以及最后(3)须证明分离出的病菌具有致病力。他还做了很多工作以控制人们对新近发现的病菌的滥用,这种情况当时已经在发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种疾病满足了以上大部分条件,其发现者是卡西米尔·戴维恩 (Casimir Davaine)。1850年他在一头死于炭疽病的绵羊的血液里观察到一种特殊的微小杆状物并进行了记录,当时他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巴斯德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观点发表之后,他才于1863年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回到了这一主题上。戴维恩很快证明,通过接种患病动物的血液,即便稀释一百万倍,该疾病也能够从患病动物传到健康动物;而接种来自另一健康动物的不含前述小杆状物的血液则无法传染这一疾病。炭疽致病菌作为最大的细菌之一,在细菌学起步阶段屡次推动其发展,巴斯德与科赫都发表了有关它的重要著作。
正是这两个人,为感染的研究注入了最大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首先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既不是医生也非有经验的生物学家,他在化学方面接受了最好的训练,与细菌学有相当的差距。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 95),生于侏罗省的小镇多勒 (Dôle),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预备训练时开始研究化学,在校期间以此为主要兴趣,于1847年毕业。
毕业一年后,他到第戎 (Dijon) 任物理学教授,这期间的一项发现成为之后他在细菌学领域所有杰出研究的起点,即可以通过发酵来分离能使光偏振面向相反方向旋转的两种酒石酸。此前他已经依据结晶的原理分离了这两种酒石酸,而这次他发现其中一种在发酵中被破坏了,而另一种保留了下来。这一发现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发酵活动的本质。
自此他对发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控制啤酒和葡萄酒不良发酵的体系由此产生,该体系对法国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巴氏消毒法”即起源于这些研究。此外,他对法国南部的一种新型蚕病-微粒子病的微生物病因进行研究,并倡导在蚕种的运输和使用过程中采取合适的隔离措施,事实证明对他的国家而言,这和发酵一样具有同等的价值。
与此同时,他还对自然发生说进行了巧妙的研究。这是一个老话题了,科学上一直争论不断。1668年,意大利医生、博物学家弗兰塞斯克·雷迪(Francesco Redi,1626 – 1694)通过证明有苍蝇在腐肉中产卵,曾一度令相信腐肉可自发生出幼虫和蛆的人无言以对。然而,不断有新的证据出现支持腐烂物中自发产生微生物的观点。另一名意大利人、优秀生理学家斯帕兰扎尼神父(Abbé Spallanzani,1729 – 1799)推翻了新兴的原始生长力学说,该学说认为存在一种原始力量可产生生命形式。甚至哲学家伏尔泰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尖刻地抨击了自然发生说的信奉者。但这种信仰并没有消除。动物细胞学说的建立者泰奥多尔·施旺也反对这一理论,与斯帕兰扎尼相似,他证明了通过适当加热可防止有机物腐败(1836)。
虽然如此,到1860年,这个难题仍鲜活如初。随着巴斯德对发酵研究的愈加投入,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迫切,显然,在其得到解决之前,他对发酵类型特异性的研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在发表于六十年代早期的一篇重要著作中,他击退了所有反对意见,真正为细菌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他的实验结果对该学科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而他在实验中设计出的保持液体无菌的方法对学科技术的进步同样影响深远。
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将巴斯德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传染病领域。他将关于发酵的想法延伸到腐败这一主题,吸引了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 – 1912)的注意。一直到1870年,伤口大量化脓仍被当成是好事,即便不像以前那样用污物刻意促成。李斯特很快证明,预防伤口及手术过程中微生物滋长的措施整体上防止了化脓的发生,使伤口得以一期愈合,将疤痕以及病人的痛苦和生命危险降至最低。现代无菌外科手术从此开始。
微生物致病的特异性是巴斯德发酵类型特异性观点的合理延伸。他表示,接触一种疾病不会随之诱发另一种疾病,就如同向啤酒中加入已知能导致一种特定啤酒“病”的细菌后不会出现其他病情。在如此广袤的领域,没有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将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的,但巴斯德得到了一批优秀同事的帮助,并因此很快找出了引发感染过程的细菌。
然而,比单纯地发现和分离细菌更重要的,是他发明的炭疽与鸡霍乱的特异性免疫,其方法是分别给牛和家禽接种经过加热、干燥或以其他方式“减毒”的致病微生物。他最大的成功则在狂犬病方面,确定了感染的部位从而找到了免疫物质的来源,但未能检测到致病菌。巴斯德研究所遍布世界,其中多家的负责人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这些是对巴斯德最大的纪念。
如上所述,通过法国人巴斯德的毕生工作,细菌学和免疫学的许多早期理论得以建立。而学科实践则在伟大的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的手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科赫是汉诺威人,1866年毕业于哥廷根,之前提到,当时雅各布·亨勒是那里的解剖学教授。我们在前几页中总结了亨勒在细菌学上的超前观点,这些见解对科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业后科赫开始了医学实践,但仍保持着对微生物及其作用的特殊兴趣。他的第一项研究是关于炭疽致病菌的生活史及感染能力。在一部杰出的著作中,他分离出戴维恩及其他人曾观察到的微小杆状物,且在动物体外进行连续多代人工培养后,将培养物注射到动物体内仍能重现这一疾病。结果发表之前科赫将它们递交给了一位在植物细菌研究领域已成名的人物——具有影响力的布雷斯劳植物学研究所主任费迪南·科恩(Ferdinand Cohn,1829 – 98),科恩立即邀请科赫前来演示他的工作。面向优秀的布雷斯劳团队的这次演示标志着细菌学新纪元的开始,它给孔海姆和魏格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这两人的著作都表现出与科赫的惊人一致。
科赫对疾病细菌学的理解有三个层面的贡献:他开发了检测和纯化细菌、将其与所有其他种类分离的方法;他界定了确认某种细菌是特定疾病病原的条件;以及最后,他本人对特异的致病菌也有一系列伟大发现。
这其中的第一层,他使用了卡尔·魏格特(Carl Weigert,1845 – 1904)提出的方法,后者是第一位给组织中的细菌染色的人。上章我们看到,在1871年对天花的研究中,魏格特已经用从胭脂虫中获取的动物染料洋红对细菌进行了染色,现已知这些细菌仅仅是天花脓包的继发性感染菌。1875年,德国的苯胺染料化学已取得巨大进展,魏格特在研究一名新生儿脐带周围的溃疡时发现脓液中存在小颗粒团,这些物质正是细菌,他用新的苯胺染料甲基紫对它们进行了漂亮的染色。科赫发现几乎所有细菌都能被热固定在一张玻片上并很方便地用这些新染料进行染色。
科赫更有成效的发明是分离纯种细菌的方法。他在1881年描述了这些方法,当时不朽著作《伤口感染》(Wound Infection) 已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前途在望的德国细菌学家,孔海姆与其他人也对此表示了认可,为他争取到柏林帝国卫生部的任命。此前科赫曾使用液态的肉汤来培养微生物,但当所有细菌在这种营养液中同样生长良好时,很难将不同种类分离开来。一种巧妙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在温热的肉汤中添加了明胶,再加入混合细菌,充分搅拌使之混匀,随后令液体冷却凝固。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不同细菌就会生长为分散的单个菌落,每一个都是纯种菌株,能够从“明胶板”上部分转移出来,在新的培养基中一代代地无限生长而不再混有其他微生物。
科赫对伤口感染的研究确定了感染和化脓过程中细菌的高度特异性,其后的工作证明这些细菌在后续所有世代中能够保持纯种繁殖,从而强化了这一论点。发明特殊分离方法的第二年,他取得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结核病原菌。在前面的章节我们看到,该疾病的各种不同表现从一开始就给医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雷奈克曾最终将痨病归为单一疾病,并公开反对认为它是多种炎症后遗症的流行观点。后来的权威人物微尔啸则又反对这一理念,把结核病区分为两大类,并将其中一种追溯到此前所患的炎症。但是,另一名法国人让·安托万·维尔曼(Jean-Antoine Villemin,1827 – 92)很快提出了一项惊人的证据:只需简单地将伤口中的物质注射到正常动物中,结核就能不断地从人传给动物,从一个动物再传给下一个动物。然而,这一强有力的证据却未能获得认可,直到微尔啸自己的学生朱利叶斯·孔海姆(Julius Cohnheim,1839 – 84)以无可置疑的方式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将结核物质接种到兔子眼球的前房,这个部位的病理变化每天都可以观察得到。
凭借着耐心与独创的技术,科赫发现了该领域前辈未能捕获的病原微生物,最终完成了对结核病的描述。发表结果时,他提出了对这门学科至关重要的科赫法则,即一种微生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被判定为某种疾病的病原:(1)必须恒定地与这种疾病相关,(2)必须能够从病损部位获取并与其他微生物分离,(3)其纯化物通过接种必须能使适当的动物发生同样的疾病,以及最后(4)在人工诱导的疾病损伤部位能够再度找到这种微生物。
其后每年他都有新的成就。1883年,作为德国霍乱派遣队的领队,科赫在东方发现了霍乱弧菌,从而找到了方便有效的霍乱检疫控制方法。在他的有生之年,其他较为次要但依然引人注目的发现仍然层出不穷。他在细菌学领域逐渐占据了等同于微尔啸在病理学中的地位,两人都在本国获得了国家的最高认可,也在各自的学科分支赢得国际声誉。科赫的学生延续了他的辉煌成就,正如同微尔啸的学生将细胞病理学发扬光大一样。
但是,在细菌学早期将这门新兴学科与病理学连接起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这两人的竞争者。他就是爱德温·克勒布斯(Edwin Klebs,1834 – 1913),前面我们已经留意到他是病理学上的全才。他早期就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现认为具有感染性的重要疾病。他与科赫和比尔罗特同为最早研究细菌与创面脓毒症关系的人,也是首批用过滤的方法对液体进行消毒的人之一,几乎不比巴斯德和钱伯兰 (Chamberland) 晚,更先于科赫尝试使用固态的细菌培养基。他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天赋,为每一门科系开辟道路,然后撤出赛场留于他人建功立业。他很早就开始调查伤寒热与结核的细菌病原,也几乎成功,但真正得出明确结论的研究就只有白喉——其致病菌常被称为克吕二氏杆菌。他还是通过喂食进行传染病传播实验的先驱。克勒布斯犯下了许多有据可查的错误,但他异常的勤勉和众多的实验成果给予了该领域其他人莫大的启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传染病的具体病原菌大都被揭晓。工具和方法终于开发了出来,研究活动如火如荼。所有疾病的致病菌都将被发现,随之就可以治愈。(传染性)疾病,除却少数无可避免的机体必须承受的变性以外,将被彻底清除。幸福时代仿佛近在眼前。
科赫的学生和助手们在这部分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之一的弗里德里希·洛夫勒(Friedrich Löffler,1852 – 1915)不仅与克勒布斯共同发现了白喉杆菌,还发现了鼻疽病杆菌,为不断增长的病原菌列表又添了一笔。1880年卡尔·约瑟夫·埃贝特(Carl Joseph Eberth,1835 – 1926)描述了伤寒杆菌,1884年科赫的另一名同事格奥尔格·加夫基(Georg Gaffky,1850 – 1918)分离出了它的纯化品,伤寒热的漫长历史至此又写入了新的篇章。
1871年挪威人阿莫尔·汉森(Armauer Hansen,1841 – 1912)发现并报道了麻风损伤中的特殊微小杆状物,1879年柏林细菌学家及性病专家阿尔伯特·奈塞尔(Albert Neisser,1855 – 1916)认为它是一种细菌,这与奈塞尔在淋病脓液中发现淋球菌是同一年。早年常见的肺炎球菌,现已被分为多种类型,最早对它进行描述的荣誉分属巴斯德、美国陆军军医处处长乔治·米勒·斯腾伯格(George Miller Sternberg,1838 – 1915)以及德国的阿尔伯特·弗兰克尔(Albert Fränkel,1848 – 1916)。显然克勒布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早看到这种微生物,而安东·魏希瑟尔鲍姆(Anton Weichselbaum,1845 – 1920)则留有最好的描述之一。魏希瑟尔鲍姆是罗基坦斯基学派中第四位任职维也纳病理解剖学教授的人,在细菌学中主要以1887年发现急性脑脊膜炎的病原菌脑膜炎球菌闻名。
1884年哥廷根的亚瑟·尼科莱尔(Arthur Nicolaier)的发现,就在意大利的卡洛(Carlo)和拉托尼(Rattone)证明该病的传染性后不久。其纯化则在1885年由受训于德国的日本优秀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Shibamiro Kitasato)首次完成。1894年开始于香港的黑死病大暴发中,北里和亚历山大·耶尔辛 (Alexandre Yersin) 同时独立发现了瘟疫的病原菌,从而使长久以来探索的、人类又一最古老最著名疾病的原因大白于天下。热带痢疾的病原阿米巴由身处埃及的科赫与卡特里斯 (Kartulis) 和美国的奥斯勒及同事确定,此前不久,另一名日本人志贺洁 (K. Shiga) 在粪便中寻找阿米巴无果,却在日本的痢疾样本中分离出一种杆菌,即此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痢疾志贺氏菌。1900年西蒙·弗莱克斯纳 (Simon Flexner) 分离出了一种不同的痢疾杆菌菌种。伤口感染中最常见的入侵者葡萄球菌和链球菌,它们的早期描述则包含有许多人的功劳。
最令人惊讶的是,早在伏拉卡斯托罗 (Fracastoro) 的作品发表之时就已成为传染性疾病理论主要支柱的梅毒,其病原却直到二十世纪才被发现。热切的年轻细菌学家提出一个又一个病原体,仅仅一个月后就都被迅速否决。1905年皮肤病学家拉沙 (Lassar) 收集了过去二十五年里报道过的一百二十五种病原体,而同年,比前辈们拥有更先进技术的原生动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1871 – 1906)和皮肤病学家埃里希·霍夫曼 (Erich Hoffman) 就发现了真正的病因——梅毒螺旋体。
与此同时,免疫学和预防免疫也取得了巨大的前进。这两门学科的进步带来的首先是体液病理学的又一次复苏,接着是与之相冲突的固体病理学的重现,最后二者取得了一种清晰、或许是长久的调和。新的体液病理学随着特定细菌毒素和抗毒素的发现而兴起。1888年巴斯德的两名学生埃米尔·鲁 (Émile Roux) 和亚历山大·耶尔辛发现培养了白喉杆菌的培养液具有毒性。几乎同时,北里也表示他本人分离出的破伤风杆菌,其培养物在过滤除去所有细菌后仍对动物有剧毒,其生长培养基中也发现存在一种特殊毒素。两年后,在科赫的研究所,埃米尔·贝林(Emil Behring,1854 – 1917)和北里发现,将这种毒素注射到动物体内一段时间后,这些动物的血清会获得中和毒素的能力,因此再向它们注射通常情况下足以致死的剂量时,这些动物能够免受侵害。不仅如此,如果将免疫动物的血清注射到另一动物体内,它同样能保护后者抵御该毒素。
几个月里人们心情渴切,传染病似乎可以通过使用特定的抗毒素而即将被征服。与破伤风抗毒素同时发现的还有白喉抗毒素,由贝林和他的同事开发。小规模的实验室试验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在人身上得到确认,各国的白喉发生率急剧下降。这一成功可能是疾病治疗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里最光辉灿烂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悲哀地认识到最初的希望过于乐观了,因为他们发现抗毒素治疗仅适用于少数的传染病。
但人们仍很快发现,体液防御不仅针对细菌毒素,还能抵抗病菌本身。1889年汉斯·毕希纳 (Hans Buchner) 证明血液本身具有杀菌能力,从而解释了其抗腐蚀性,这一特性曾给约翰·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1894年理查德·法伊弗 (Richard Pfeiffer) 发现,将霍乱弧菌注射到对其免疫的豚鼠腹腔后,它们很快就丧失了运动能力,形成颗粒,最后分解成碎片。如将同种细菌注射给正常动物则不会发生类似的分解现象。免疫的动物血清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能够造成这种破坏。
许多研究人员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现了相关的“凝集”现象,即细菌或细胞在对其免疫的动物血清的作用下所发生的凝集和粘附。1896年马克思·格鲁伯 (Max Gruber) 和赫伯特·达拉姆 (Herbert Durham) 发现,可通过与已知抗血清的反应来鉴定从病人身上分离出的细菌。费尔南德·维达尔 (Fernand Widal) 则反向而行,指出可以用已知种类的细菌测试病人的血清,通过这种方式辨别其所患疾病。检测伤寒症著名的格鲁伯-维达尔测试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
一年后鲁道夫·克劳斯 (Rudolf Kraus) 发现了一个与凝集现象密切相关的反应,当他将细菌培养物的清滤液与该细菌的抗血清混合时,混合液出现浑浊或沉淀。他将这一现象称为“沉淀素反应”。由于具有很强的特异性,该反应很快被用于蛋白质沉淀、尤其是血迹检测试验中。
所有这些发现都使人们对体内的液体元素产生了新的见解,并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它们在疾病中的重要意义。由此看来。希波克拉底学说似乎彻底回归。当然,阻止接触传染病发生的不是浓度适宜的胆汁和黏液,而是体液中适量的特殊防御物质。然而,与之相对的固体病理学说也进展顺利。俄国人埃利·梅奇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1845 – 1916)在敖德萨 (Odessa) 时曾证明液体中的变形虫样细胞能够吞噬固体颗粒(1884)。后来梅奇尼科夫慕巴斯德之名来到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在这里很快证明了血液中的白细胞能够且偶尔确实吞噬和破坏了致病细菌。他将这些细胞命名为“phagocytes(吞噬细胞)”(来自κύτος,细胞,以及ϕαγεîν,食用),将吞噬细菌的过程命名为“phagocytosis(吞噬作用)”。现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身体清道夫的概念即由此而来。
因此,在短短十年内,抵御细菌感染的机制就有了两种解释,事情变得难以理解。毕希纳、法伊弗和其他人发现血液在产生免疫之前已可在一定程度上消灭细菌,产生免疫之后则效果更好;梅奇尼科夫证明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他所发现的吞噬细胞。两种理论都可以解释所谓的“先天”或原始免疫,以及通过特异性免疫接种获得的免疫。而这个看似疑难的问题很快就在J. 丹尼斯 (J. Denys) 和莱克里弗 (Leclef) 的工作中得到了解决,二人于1895年证明,对特定疾病免疫的动物血清显著促进了吞噬细胞对该疾病致病菌的吞噬作用。
这项研究得到了其他人的确认,尤其是阿姆罗斯·赖特爵士 (Sir Almroth Wright) 和他的同事,他们提出了“调理素”(来自希腊语中意为“我准备”的单词)的概念,来描述作用于细菌使之更易受到吞噬作用的血清物质。
如此一来,体液和细胞防御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调和。而将两类免疫的多种现象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工作系统中,则是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 – 1915)的功劳。这个伟大的体系就是类比芳香烃的化学侧链所提出的著名的“侧链”理论。埃尔利希将受伤的细胞比作这类芳香族化合物,赋予它们生成和释放侧链的能力,这些侧链在细菌入侵时能够保护细胞。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针对病菌及其毒素的“抗体”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已具有充分的依据。侧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护性侧链的释放多于即刻损伤的需求,它依据的是损伤之后组织的过度保护反应,埃尔利希的表兄弟卡尔·魏格特曾提醒人们对此事实引起注意。埃尔利希的假说至今经过了大量的修改,某些具体概念几乎已被遗弃,但他对繁杂多样的免疫学现象进行了细心的组织归纳,由此为这门学科带来的动力是无价的。
随着多种特殊抗体反应的发现,新兴的免疫学取得了巨大进步。朱尔斯·博尔代 (Jules Bordet) 曾提出一般免疫反应的理化假说,受到广泛追随。1900 – 1902年他和奥克塔夫·让古 (Octave Gengou) 发现对特殊红细胞免疫的动物血清获得了溶解同类其他细胞的能力,为免疫学做出了重要的特殊贡献。他们发现血清中有两种成分在这一反应中发挥了作用,即“抗体”和“血清补体”,因此提出了“补体结合反应”。1906年经过奥古斯特·瓦色尔曼(August Wassermann,1866 – 1925)的修改后,这一反应在梅毒的诊断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现已知,对某种蛋白产生免疫的动物,其血清在补体结合与沉淀素试验中能够同这种蛋白发生反应,如果向这种免疫动物的血流中注射少量该种蛋白,则免疫动物可能陷入强烈的休克。查尔斯·里歇 (Charles Richet) 在1912年将这种现象命名为“anaphylaxis(过敏反应)”(来自ἀνá与ϕυλáσσειν,提防)。一系列相关现象如今统称为广义的“变态反应 (allergy)”和“过敏 (hypersensitiveness)”。
即使只对最明显的现象作这样简短的总结,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免疫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过短短几十载,却已然达到了不同寻常的复杂程度,其各个分支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延伸。
细菌学和免疫学不断发展之时,在与之相关的两个领域,包括非细菌类寄生虫造成的人类感染和寄生虫病的传播,人们也取得了同样丰硕的研究成果。疟疾是人类的大敌之一,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病,其病原寄生虫揭晓于1880年,发现者是驻阿尔及尔的法国军医阿方斯·拉韦朗 (Alphonse Laveran)。而这一疾病的传播方式则仍然存疑,直到1897 – 1898年,罗纳德·罗斯 (Ronald Ross) 在印度发现了蚊子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工作得到了巴蒂斯塔·格拉西 (Battista Grassi) 和其他意大利人的确认和进一步发展,他们阐明了按蚊在疟疾人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这些最终成果来自于多项极其重要的研究,其中的两个发现就曾为认识昆虫传播途径指明了道路。早在1879年,英国的帕特里克·曼森爵士 (Sir Patrick Manson) 就证明了蚊子是最常见的热带丝虫病病原寄生虫的携带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曼森的建议和鼓励最终促成了罗斯疟疾研究的成功。另一个开拓性的发现是在美国,西奥博尔德·史密斯 (Theobald Smith) 找到了“德克萨斯牛瘟”的病原寄生虫,并发现牛蜱是该病在感染和健康牛之间传播的媒介(1893)。
疟疾通过蚊子传播这一事实的确认为其他热带病之谜的解答开启了大门。其中最光辉的成就之一来自于1900年一支美军调查团的努力。这支团队由沃尔特·里德 (Walter Reed)、詹姆斯·卡罗尔 (James Carroll)、亚里斯泰迪斯·阿格拉蒙特 (Aristides Agramonte) 和杰西·W. 拉齐尔 (Jesse W. Lazear) 组成,他们将黄热病未知病原的传播来源追溯到一种现称埃及伊蚊的蚊子。为了证明这点,他们进行了严酷而艰苦的试验,在此过程中,卡罗尔轻度染病,而拉齐尔献出了生命。距今更近的一些年,人们发现了众多其他疾病的昆虫传播途径,亦因此得以实施有效的控制方法。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
本帖最后由 强子 于 2016-07-02 08:37:23 编辑
前一章所记述的事件显然开启了一种研究疾病的新方法。迄今为止,此前许多病因不明的异常状态仅限于人类或偶发于动物,现在则可以把这些疾病随意转至实验动物并可研究整个疾病的发展过程。因此,细菌学的出现直接诱导了实验病理学的产生。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实验病理学是一项新发明,因为它自古就存在。古代的哲学家和今天的生理学家一样意识到简单地观察生命的自然进程是不够的,某些事实必须通过受控的实验才能了解。
此外,尽管后来的人们能够自由探索人体及其内部疾病,但古代的迷信和宗教偏见却极大地阻碍了这类观察。曾几何时,文明世界愈千年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的基础,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动物解剖和动物实验。克劳迪亚斯·伽林在他一生只见过寥寥数例人类尸体的内部情况。
诚然,伽林设计实验的目的是阐明生理学问题,但我们可以发现,用来解释正常机能和机能失调的实验两者之间并无清晰界线。在实验科学中,生理学和病理学变得无法分割。如果我们注意到哈维证明血液循环的实验直接解释了一型水肿的发生原因,这就很明显了。
如果说伽林难以接触到人体病变组织,实验病理学是唯一的依靠,那么对于没有这一限制的研究人员,它的适用性也丝毫不打折扣。罗基坦斯基的文件夹中存有七万例尸检档案,仍坚持:“病理解剖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是活体,要跟踪所发现的解剖学异常的起因、存在状况和演化,需要靠实验病理学创造条件。”这一宣告发布的五十年内,专门致力于实验病理学研究的机构迅猛发展,充分证明了他的观点。
此外,遇到通过偶然观察难以快速获取明确信息的情况,实验常常是一条捷径。哈维的方法在他发现血液循环后立刻被应用于病理学问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血液循环得到证实后,甚至于在这之前(参见彼得·保尔的观察,第87页),人们必然多少已经意识到循环障碍与脚踝皮肤肿胀及全身水肿之间的关系,却迟迟未能确认,而后来伦敦的理查德·洛厄(Richard Lower,1631 – 1691)仅仅通过很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个问题。
洛厄在他的《心脏学论》(Tractatus de corde,1669,发表于哈维的划时代著作问世四十一年后)中,描述了大量动物实验,其中许多通过压迫或结扎静脉,专门研究静脉循环瘀滞所产生的结果。他没有找到预期的淤血,却在打开压迫点远端的多处严重肿胀部位时,发现组织中充满了血清,简而言之,呈现人类水肿时常常观察到的状态。直到他结扎了狗横膈膜上方的腔静脉并观察到腹水的产生,这才谨慎地得出了结论。这一实验仅用了两天就获取了一条重要信息,的确是走了捷径。
用途广泛的动物实验绝不仅限于循环障碍的研究。与洛厄同时代的约翰·康拉德·布伦纳(Johann Conrad Brunner,1653 – 1727),十二指肠布伦纳氏腺的发现者致力于腹腔脏器,尤其是消化道相关脏器的功能研究。他摘除了若干只狗的胰腺,这在当时是十分了不起的手术操作,接下来的情况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手术后的这些狗比原来更饥饿,极度口渴,频繁排尿。然而,在当时他的实验太超前,而无法充分的理解这些现象发生的机理。如果有十九世纪的化学分析方法,他将成为第一个发现胰腺性糖尿病的人,实验中的狗显然处于糖尿病状态。
许多人都在使用实验方法获取期望的生物学信息,以上只是其中的两个。之所以特别强调较后期的开拓性实验研究,仅仅是因为这些工作独具的特性。相互竞争的各国一致将现代实验病理学创始人的荣誉颁给了约翰·亨特。如果这一称号实至名归,那就是因为在其他方法无效时,他始终坚持利用实验来解决问题。他本人开展了各种实验,在动物试验失败时就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长时间的实验劳作损毁了他的健康。但他并没有引进新的病理学研究方法,只是简单地依靠不屈不挠的实践, 坚持来证明实验方法的价值,使实验病理学的地位再也不可动摇。
微尔啸赞赏亨特建立了实验病理学的方法,他自己也广泛地应用到实验中。在对栓塞的伟大研究中,他经常尝试通过实验来再现损伤,以此支持他从尸检解剖的发现中得出的推论。这些活动代表了现代实验病理学的基调。对于情况尚不明朗的损伤,准确而规范的人工模型常常成为了解其自然诱因的最可靠办法。魏尔啸注射真实的血栓、组织、空气、脂肪甚至微小的淀粉颗粒到血管中,这些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微尔啸最终理解了栓塞的发生及临床表现,其作用大概等同于他所进行的尸体解剖。
路德维格·特劳伯(Ludwig Traube,1818 – 1876)是微尔啸的同事,曾在布雷斯劳跟随普尔基涅 (Purkinje) 学习,后到柏林受训于约翰内斯·穆勒和舍恩来因。他早年发行了杂志《实验病理学刊》(Beiträge zur experimentellen Pathologie),几乎仅面向采用实验方法取得的病理学结果。特劳伯本打算致力于普通的临床观察,但医院的一项行政命令切断了可供研究的患者来源,于是他将精力转向动物实验。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了迷走神经切断后发生的肺部疾患。虽然他的刊物十分短命,但他的影响仍旧深远,在1848年的革命中重新获得临床机会之后,他的职业提升十分迅速。他成为了一位颇受欢迎的临床医学导师,其精确信息的获得大都离不开实验的帮助。
前面已经提到了冯·雷克林豪森的早期研究。微尔啸认为脓细胞是局部组织细胞,他这名高徒则是老师的脓细胞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虽然1863年雷克林豪森本人研究白细胞阿米巴运动的湿盒实验强烈表明了白细胞与脓细胞之间的关系,1867年对蛙角膜炎的实验研究似乎又证明脓液及其中的特定细胞可产生于已存在的组织细胞。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就是在低等动物蛙的角膜上,关于炎症本质的世纪争论最终有了结果。
雷克林豪森发表研究成果的同一年,微尔啸的《档案》卷40在首篇刊出了朱利叶斯·孔海姆的革命性文章《论炎症与化脓》 (Ueber Entzündung und Eiterung)。孔海姆(1839 – 1884)大概是微尔啸众多著名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和老师一样出生于波美拉尼亚,1864 – 1868年在柏林做后者的助手。同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病理学家一样,常规组织学和神经学曾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此间研发的出色技术在后来令他颇受助益。病理学问题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在探索的过程中他设计了许多研究炎症的精巧实验。
学习冯·雷克林豪森的方法,孔海姆一开始也选择了蛙角膜进行实验。完整的实验步骤如下:他用苯胺蓝对前房房水染色,进入此处的白细胞染上蓝色;然后他刺激角膜,受损角膜处很快出现类似于白细胞的新细胞;这些细胞不是蓝色而是白色的,因此它们并不来自于邻近的前房。接着他将染料注射到蛙背部的淋巴囊中,这一操作使大量白细胞着色,这些白细胞最终将进入血流。他再次损伤蛙角膜,此次经过染色的细胞出现在了刺激部位。
这似乎已经完全证明了损伤部位的脓细胞来自血液,但孔海姆希望得到双重证实,他期望看到流动中的细胞。他想到了一个便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即使用薄而透明的蛙肠系膜。现在这已是十分普通的实验。他将蛙肠系膜铺展在温暖湿润的玻片或软木环上,以便在显微镜下观察其中细小的血管。将刺激物斑蝥素施加到部分组织上后,他观察到一个神奇的变化:血管变宽,血流变慢,之前在快速的血流中无法辨认的红细胞和白细胞现在清晰可见。他很快便真切地观察到了惊人的事实:血液中的白细胞穿过毛细血管壁,在受损部位聚集。结论很明确,脓细胞,也即炎症区域中的白细胞,来源于血液白细胞。至此,曾受到古人相当重视的血管在炎症时的作用,在历经局部细胞变化论的支持者微尔啸的贬低后,重新成为了炎症研究的关注点。孔海姆总结说,“没有血管就没有炎症”。
然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旧的观念出现了新的支持者。维也纳的萨尔蒙·斯特里克(Salmon Stricker,1834 – 1898),匈牙利人,罗基坦斯基赞赏他的才华,曾为他特设实验病理学教授职位。借助于高超的组织学技术,斯特里克于1865年发现了毛细血管的红细胞渗出,后来更得以在自己的领域与孔海姆一较高下。他回到了角膜研究上,用硝酸银刺激角膜后迅速检查受损部位,发现局部细胞几乎立刻就有变化,发生反应并增殖,而此时,本身无血管的角膜,其周围毛细血管中的任何细胞都不可能来得及到达该区域。这些局部细胞的集聚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化脓区域。
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许多人参与其中。梅契尼科夫 (Metchnikoff) 对大小吞噬细胞的区分极大地帮助了事实的厘清。孔海姆所认为的白细胞是被动挤出毛细血管壁的观点经过了修改,以支持趋化性或化学吸引的现代学说。人们最终发现,名称不同的各种局部组织细胞,以及浸润到损伤部位的多种白细胞,全都参与了炎症过程,因此参与这场争论的每一位成员都对此做出了贡献。
孔海姆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主要是通过实验方法。他成功地在兔眼前房中接种了结核,因而能够通过透明的角膜观察到疾病的发展过程,向存疑的科学界确证了该病的传染性,自此,致病菌的分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栓塞过程研究》(Investigations on the Embolic Processes)一书发表于1872年。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梗死来源于末端动脉 (“Endarterien”) 栓塞的学说,以此解释某些出血性梗塞来源于静脉倒流和梗塞区域病变毛细血管血细胞渗出。此前,梗死形成一直被认为是由梗塞区域的毛细血管闭塞导致的。
这些高水平的成就使孔海姆成为欧洲实验病理学的领头人,在普通病理学领域的影响力也仅次于微尔啸。众多学子争相进入他的实验室,威廉·韦尔奇 (William Welch) 就是其中一员。韦尔奇后来更深入地探讨了血栓、栓塞和梗死等主题,并发表了研究心脏疾病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论文,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这些循环系统问题的理解。韦尔奇在布雷斯劳学习时,这里的学科发展正处在最辉煌的时期。孔海姆忙于肿瘤理论研究和《普通病理学讲义》 (Lectures on General Pathology) 的编辑,魏格特做了大量尸检,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埃尔利希几乎已经对苯胺染料很有研究了;科恩和海登海因正吸引着植物学、细菌学和生理学的热心学子,而就在几个月前,科赫刚刚到此演示了关于炭疽病的伟大研究成果。韦尔奇听从孔海姆的建议开展了急性肺水肿研究并得出结论,这一常见病可由左右两个心室工作效能的不均衡所致。
游学过程中,韦尔奇结识了可勒布斯、斯特里克、赫斯歇尔 (Heschl)、基亚里、林德弗雷斯、齐格勒与冯·雷克林豪森。回到美国后,他毫不犹豫地进入病理学领域并很快接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理学教授职位。此时,正是细菌学发展的飞跃期,在这一领域韦尔奇也走在了先驱的行列,与纳托尔 (Nuttall) 共同发现了产气杆菌(产气荚膜杆菌、韦尔奇氏菌)。此后他在美国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
而在法国,实验方法则在一个相当不同的领域产生了重要成果。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 – 1878)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他来到巴黎时还是一名满怀希望的剧作家,却在那里变成了生理学大师。转变来自于一个善意的忠告,贝尔纳听从建议转学医学,跟随生理学家马让迪 (Magendie),受到了后者的影响。马让迪满足于生理学研究本身,而贝尔纳则更关心这些研究在疾病中的应用。他在一场重病康复期完成的这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实验医学》 (Experimental Medicine) 很好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贝尔纳发现肝脏通过储存糖原的功能而参与了糖代谢的调节(1843 – 57),由此奠定了 “内分泌器官”的认知基础,对我们当前的糖尿病理念也有重要意义。关于胰液的研究工作(1849 – 56)开启了人们对消化生理及病理的全新理解。他的第三个发现是关于血管的舒缩机制,不仅对常规生理学十分重要,而且对理解多种病理状态也有应用价值,包括主动充血,或许还涉及心绞痛和许多无法清楚认识的病理生理范畴的情形。
贝尔纳在巴黎的实验病理学教授职位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色夸(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1817 – 1894)接任。布朗-色夸是毛里求斯人,美法混血,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他进一步推动了内分泌领域的发展。就在艾迪生发现与肾上腺损伤所致的相关疾病后不久,布朗-色夸通过实验证明动物被摘除肾上腺后出现严重症状或迅速死亡,从而证实了艾迪生的结论:肾上腺对于生命的维系至关重要。他相信内分泌对机体的影响,并因此试图通过注射器官提取物来缓解年龄增长带来的变化,以及较理性地,通过这种方法治疗肢端肥大症。此前他的同胞马里亚 (Marie) 和其他人已发现该病是由另一无管腺——脑垂体的异常引起的。使用实验方法研究神经病理学的布朗·色夸跟上了法国病理学的潮流。他的脊髓半切和横切实验帮助人们理解了该器官某些自然损伤的症状,他的名字也因此与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综合征联系在一起,即布朗·色夸综合征——伴发对侧麻痹的偏瘫。
内分泌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巴黎著名医生泰奥菲尔·德·波尔多(Théophile de Bordeu,1722 – 76),他主张每个器官都能合成特定产物,这些物质会进入血流。如今这一概念一般限于没有外分泌的腺体,它们在动物的新陈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甲状腺、甲状旁腺、脑垂体、胰腺、肾上腺和性腺。波尔多的简单理论被细化到极致;某些腺体的内分泌物现已被分离提取,特定内分泌腺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也得到了确定。
这些腺体异常及相关代谢失调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观察历史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突眼性甲状腺肿,1786 – 1815年间,巴斯的卡勒布·帕里(Caleb Parry,1755 – 1822)研究了八个病例,其后罗伯特·詹姆斯·格拉夫 (Robert James Graves) 和德国的卡尔·巴塞多 (Karl Basedow) 分别于1835和1840年详细描述了这一疾病。
我们目前了解的关于无管腺功能的知识,很多是通过研究摘除动物腺体后的结果得来的。动物学家和生理学家莫里茨·希夫(Moritz Schiff,1823 – 1896)记录了实验摘除狗的甲状腺后产生的系列症状(1856及其后),现已知这些症状是甲状腺机能减退所致。1883年伯尔尼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柯赫尔(Theodor Kocher,1841 – 1917)报告了无意中在人体上进行的同一实验,描述了他自己的若干病人因其他疾病需要而手术切除甲状腺后发生的代谢失调。英国的威廉·格尔爵士 (Sir William Gull) 在1873年描述了其他原因导致的人甲状腺机能减退症候群。
就在刊登巴塞多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经典描述(1840)的同一卷杂志上,伯恩哈德·莫尔 (Bernhard Mohr) 发表了对一种重要肥胖类型的观察结果,该病现称“弗罗利希综合征”(来自1901年阿尔弗雷德·弗罗利希 (Alfred Fröhlich) 的描述)。尸检发现了一个变性的脑垂体肿瘤。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器官与巨人症和肢端肥大症的关系,也了解了艾迪生发现的在解剖学上并不起眼的肾上腺所能引起的致命慢性病。而阐明胰腺在正常代谢中所起的作用则是现代生理学的一项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糖尿病的本质。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不断增长的关于无管腺的生理学知识将更多地应用于病理学问题的解决。
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群德国临床医生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了生理机能障碍与特定器官病理学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主要引路人和导师是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冯·弗雷里奇斯(Friedrich Theodor von Frerichs,1819 – 1885),他毕业于哥廷根,因在基尔 (Kiel) 和布雷斯劳医疗诊所的工作和教学成果,于1859年受邀前往柏林接替德国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教师之一舍恩莱因。弗雷里奇斯在布赖特氏病、尿毒症、糖尿病和疟疾方面都有重要研究,但最为后世铭记的则是他对肝脏疾病的深入研究。他以《肝病诊疗》(Klinik der Leberkrankheiten) 为题发表了两篇内容相对独立的专题论文,总结了这一器官的研究历史和已有知识,又加入了自己的杰出成果。他详细讨论了名为急性黄色肝萎缩的退行性疾病,并提醒人们注意,亮氨酸与酪氨酸的过量分泌及其在尿液中的结晶是这一疾病的特有病症。
他最重要的实验工作是黄疸研究,包括结扎胆总管、注射胆汁成分等,但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充分论证。他对脂肪肝兴趣浓厚,部分阐释了饮食与脂肪肝形成的关系。他常常用到最先进的化学方法,不仅是实验病理学的早期带头人,也称得上化学病理学的先驱。他的学生伯恩哈德·瑙宁(Bernhard Naunyn,1839 – 1925)受到他对胆结石分析的启发,开发了该领域的化学研究并构建了一套准确的化学分类方法。
为争取可供研究的病人而在查理特医院展开的激烈竞争使得弗雷里奇斯一直很讨厌微尔啸和特劳伯,而他的学生们并不这样。冯·梅灵、埃尔利希(von Mering Ehrlich)和瑙宁(Naunyn)大概是他的学生中成就最高的,其中又以瑙宁的研究方向最接近他所铺设的线路。
约瑟夫·冯·梅灵(Josef von Mering,1849 – 1907)和奥斯卡·闵可夫斯基 (Oscar Minkowski) 发现狗被切除胰腺后出现了糖尿病症状,即人为造成了胰腺性糖尿病,这是弗雷里奇斯学派最辉煌的成就之一,为现代医学另一同等重要的进步——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铺平了道路。
1878 – 85年任弗雷里奇斯助手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 – 1915)无疑是近代化学和实验病理学及相关领域的代表人物,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他对免疫学的贡献。埃尔利希最初受训于布雷斯劳学院,对魏格特的鉴别染色技术印象深刻,在染色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染料原理,在他的布雷斯劳同事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基础理论,其应用之广足以支持包括血液学、免疫学和化学疗法在内的数个新兴的主要学科。埃尔利希根据白细胞染色特性的区别对其进行了分类,并在科赫发现结核杆菌的同一年发现了这种病菌的抗酸性,这都是微量化学分析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他的血液研究为我们现在的贫血和白血病分类奠定了基础。
他是一位多产的化学家,勇于归纳一般化的理论。他借鉴了凯库勒 (Kekulé) 提出的苯环结构(有机化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围绕这一结构建的),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免疫学理论,建立了新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他自己的免疫学。
在化学疗法的研究中,染料又一次为他提供了介质。他在活体内成功地选择性染色细胞及侵入者使他产生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改造染料,使之包含能够杀菌的化学基团,同时对组织内的病菌具有相同的选择性亲和力。依据这一原理,他向梅毒螺旋体发起了攻击,试验了一种接一种强化染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废料堆已经累积了六百多种无效品,第六百零六种才终于试验成功,成就了医学界一个伟大的励志故事。
鉴于化学对于病理学的助益在不断增长,在此对其生物学分支的发展历程进行一次回顾是十分合宜的。同生理学一样,对生物化学的探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病理学。我们可以看到,早在炼金术时代,冯·海尔蒙特就提出了颇有成效的特殊发酵理论。许多伟大的病理解剖学家都曾使用化学分析方法,最早是灵敏的味觉尝试,后来这一方法被淘汰,改为其他刺激性较小的途径。莫干尼把从浆液腔中得到的渗出液标本煮沸,仔细观察凝结物的性质;布赖特将病理解剖学和尿液分析相结合,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安德鲁及其他人率先将血液化学应用于病理学;罗基坦斯基宣称未来的病理学将是化学病理学,而细胞病理学家微尔啸纠正了罗基坦斯基在化学上的错误。
然而,成体系的化学病理学的建立则需要更多的协作,这发生于1825—1850年间,当时德国的化学实验室在贾斯特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 – 1873)的影响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李比希是法国盖-吕萨克化学学派的学生。有机化学开始于这一成果丰盛的时期。不仅如此,由于弗里德里希·沃勒(Friedrich Wöhler’s,1800 – 1882)在实验室里实现了有机物氰酸铵到尿素的转化(1828),而尿素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物质,是人体内氮代谢的主要终产物。因此,横亘在有机化学与生命体化学之间的屏障也几乎在竖起之日就被打破。随之,李比希、沃勒及他们的同事和学生继续不断地发表了其他有重要生理学意义的发现。
而在菲利克斯·霍佩-赛勒(Felix Hoppe-Seyler,1825 – 1895)的推动下,化学生理与病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霍佩-赛勒最初学的是医学,在柏林病理学研究所给微尔啸当了八年的助手。他创办的《生物化学学刊》(Zeitschrift für physiologische Chemie,1877)影响深远,所著生理化学教科书(1877 – 81)哺育了该领域第一代研究人员。
埃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1852 – 1919)是近年生理化学的领军人物,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他在柏林大学担任化学教授二十七年,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培养的大批优秀学生,推动了生物化学各个方向的进步。今天的糖和蛋白质化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费舍尔一手建立起来的。他阐明了蛋白质的结构,发明了蛋白质的分析方法,利用蛋白质的“构成部件”重新合成大分子的类蛋白化合物;这些伟大的成就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所有的化合物中,蛋白质似乎是生命和生命过程最基本的特征。
化学的进步使新的生理和病理学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在形态学研究进展已接近极限的领域,这些新方法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强力推动。
水肿和炎症一样,是个古老且令人头疼的问题,千百年来的病理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在此栽过跟头,而渗透压和胶体水合作用的现代理化研究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曙光。如果没有化学,人们不会理解坏死、化脓、坏疽和退行性病变,而最近获得的组织酵素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损伤组织的钙化和结石形成所涉及的众多不同过程曾被单独划分为地质学问题,这有点滑稽,更合适的说法或者应该是矿物病理学,而实际上这显然是化学病理学的研究内容。
免疫学家期望着胶体化学家帮他们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在人们发现某些促生长物质或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一系列迄今性质不明的疾病后,一个新的学科悄然兴起。然而,化学带来最多实质性帮助的领域,大概中毒研究。血液化学研究极大地延续了布赖特、保斯托和安德鲁开启的光明前景,人们对尿毒症、糖尿病和各种酸中毒的理解也相应提升。现在用简单方便的化学方法检测人体代谢过程,就能够发现和理解人体功能失调,这是传统病理学无法做到的。
以化学领域成就的这几段简述为此书作结并不合适,因为病理学未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将极大地依赖于化学。我们看到了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界的病理解剖学家是如何通过理性的研究使病理学脱离揣测的阶段;看到随着细胞学和组织学的兴起,器官病理学发展为组织病理学,组织病理学进化到细胞病理学;看到细菌学引入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未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完善也必将一如既往地应用于病理学。人们的注意力曾相继集中在病变的器官、组织和细胞上,并都相应取得成果;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设想,至今成谜的细胞内胶状乳浊液将成为未来的研究重心,并极有希望获得成功。各大医学研究院不断增加用于发展化学方法的设备,说明人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
当然,现在也不能保证今后必将出现如同十九世纪的细胞学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尽管评价当代的进步十分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仍有很多证据表明,现代病理学表现为集体的智慧,比起在上个世纪产生巨大效用的个人能力,当前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良好的管理,学科文献的迅速累积,众多优秀教科书的频繁修订,以及各学科领域的精彩综述和专题论文。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很容易发现目前知识中的缺失和不确定性。
世界大战(译注:这里指一战)使人们更加认识到管理细节对于科学研究和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影响到科研组织方式的改进。病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带头人精心策划、妥善安排,通过他们的学生,填补现有知识中的空缺。路德维格·阿朔夫 (Ludwig Aschoff) 在德国建立的著名的高效率教研组织可以看作这种趋势的一个实例。因此,管理才能和对项目的前瞻性,虽然听起来没那么梦幻,却和个人在研究中的创造力一样,已成为病理学知识增长的重要原动力。

- 赚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