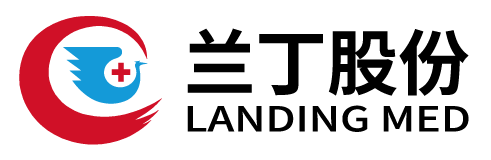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西藏公主(zt)
她的名片是粉紅色的,以藏文、中文与英文字体印著“西藏公主”頭銜。她喜歡Prada服飾,美國的hiphop,歐洲的techno舞,港台流行歌曲,賓士轎車及网球,但不喜歡彈鋼琴。雙子座的她,小學作文立志當中國國家主席。一位极具潛力的中國政壇明日之星,她的名字叫堯西·班·仁吉旺姆,第十世班禪喇嘛(1938-1989年)的獨生女。
仁吉曾在美國大學念政治系,一年里有4個月時間待在中國。北京的家是十世班禪喇嘛生前住所,位於北京火車站附近的一座3層樓高,有50個房間的別墅。平日有專人打理公主的服飾,在采訪時,一襲橙色絲質傳統藏服与同色系的珊瑚項鏈、念珠及戒指,襯托出仁吉的青春气息。在完美無瑕的妝扮中,一個人頭胸章突兀地別在她的前襟,那是她父親的照片。
十世班禪喇嘛圓寂於1989年,當時仁吉未滿六歲,“父親圓寂那么多年,但感覺上一直都在身邊。”她對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父親見到她總是又親又抱,以及小時候住在北京郊區西山,父親陪她在花園里与馬等動物一起玩。“父親40歲得子,將我視為掌上明珠。他每天早上念晨經,在佛像前盤腿,把我放在腿上;父親很忙,每個人見到他總是要磕頭,父親允許我不必向他跪拜,否則每次見面都要跪拜的話,我將永遠趴在地上跟他說話。”
藏族人說“天上有太陽、月亮,人間有達賴、班禪。”藏傳佛教的兩位領袖是六百万藏人心中的神。“我与第十一世班禪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父親去世十周年紀念會上,我与小班禪擦身而過;另外是2002年回西藏那一次。按理說,我与第十一世班禪應該有特殊感覺(如果我們真是父女)。上次會面旁邊很多人,鬧哄哄地,我沒有感應,今後有机會我會好好用心去感覺。」
仁吉承接了父親的德澤,大前年她回西藏時,成千上万藏人聞風而至赶到日喀則迎接她,將她視為“度母”轉世,能為西藏帶來好運。“藏民不能忘記我的父親,他們對我父親的愛,全都轉移到我身上來,我每天要獻上一万多條哈達,手都腫了,但心中很喜悅。我覺得我對他們有很大的責任,一定要為百姓做點什麼。“仁吉离開拉薩那天,大昭寺廣場涌進六万人,有人熱淚盈眶高喊,“公主,常回來看一看,我們會想你的。”
仁吉的政治智慧超過實際年齡。她在18歲時,就是西藏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現任世界援助協會顧問及廣州十多家藏藥店的董事長。她知道自己的好坏將影響十世班禪喇嘛的聲譽,她很自豪“這麼多年,沒有說錯一個字,沒有作錯一件事。”
13歲之前,仁吉在北京上學,在校成績名列前茅,并擔任學生干部。因為從小耳濡目染,以至于長大后對政治抱有高度興趣,她的大姨董榮透露,仁吉就讀小學三年級的一篇作文中提到,長大后要當國家主席,“可能是家族遺傳吧,我喜歡政治,我非常希望從政,希望能夠得到政府安排,能夠參政議政。”仁吉深知自己的使命。
班禪圓寂後,留下一些遺志有待完成,“具体實施父親提倡的“以寺養寺”規划,透過現存的剛堅發展有限公司下屬的地毯厂、酒店、唐卡及車隊等經濟運作,使寺廟自給自足,減輕信徒負擔。”
至今她尚未決定畢業後留在美國或返回北京。仁吉用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各种可能性,“以前總覺得時間很多,回西藏後,整個人都成熟起來,時間突然不夠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在西方學習9年,學習到語言、知識与文化,我想將西方高科技知識及先進管理帶回家鄉,讓藏區經濟平衡發展。”
附:堯西·班·仁吉旺姆自述
歷代班禪中,确實只有爸啦結婚,從第一任班禪大師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為第十世班禪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緣是很深厚的……
北京嘉里中心一樓。23歲的堯西·班·仁吉旺姆順手從報架上拿起一份英文報紙,她立刻被頭版頭條標題——“4月13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將在杭州舉行”所吸引。在她想拿走報紙時,門口的侍者擋住了她。
她几分咄咄地問,能否買下?侍者含笑拒絕。
那就在外面買吧,她無奈道。這個侍者
并不知道眼前這位年輕的、全身時尚名牌的、漂亮中還帶著洋气的女孩是誰,她為什么非要這份報紙不可。
堯西·班·仁吉旺姆,密宗的含義是:智慧的圣母。
“這是爸啦為我起的名字。”回到她的城堡,那間藏式薰香氤氳的屋內。她身著那件唯有特殊級別的人才能穿上的黃色藏裝,藏裝明黃黃的亮,賽過屋中正面壁畫里珠穆朗瑪峰上的一抹余暉。她在衣服上別上一枚像章,像章里一個男人微微笑著,那人就是她的“爸啦”——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确吉堅贊。
十世班禪身邊的人都稱呼堯西·班·仁吉旺姆為公主。她笑眯眯地說,你也可以叫我仁吉。
桌上,一盆粉艷艷的紅蓮花。管家端上一碗白稠稠的酥油茶后,一直靜候在公主的身旁。仁吉旁若無人,一邊翻閱清華大學的學習提綱,一邊熟稔講述往事。可是,“公主的身份,在當今中國如何被肯定?”
如何被肯定,無從考證。打從我記事起,爸啦身邊的人就這么稱呼我。至今很長時間了,我也很自然了。我想,“公主”一名緣起于爸啦是十世班禪,是藏傳佛教的領袖吧。
1983年6月,我出生到了人世間。首先,我想很多人會很好奇我爸啦的這段婚姻,會提出疑問“班禪怎么會娶妻生女?”生長在內地的人不明就里,不了解藏傳佛教的習俗。藏傳佛教屬于大乘佛教,与注重自身解脫的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強調的是利他,利大眾,清規戒律較少,所以在藏區,活佛通婚的事情极為普遍。但歷代班禪中,确實只有爸啦結婚,從第一任班禪大師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為第十世班禪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緣是很深厚的。
而我的阿媽啦,李洁,身為前國民党將領董其武心愛的外孫女,一位名門閨秀,一個漢人女子,能在爸啦解除監護后,認識他,嫁給他,也自是他們的奇緣。
爸啦過世時,我才五歲半。他生前是不可能向一個小孩子解釋他為什么文革甫一結束,就萌動凡心的。我現在長大了,根据阿媽啦的回憶,和我個人的分析,我想正是爸啦在“文革”的遭遇為他日后的姻緣埋下了伏筆: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9-09-21 23:29:00 编辑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
我和阿媽啦被通知火速赶往日喀則,途中無人向我們提起爸啦的事情。等我們到達班禪歷代行宮德虔頗章時,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有的人甚至哭昏過去了。
那年的那天,天空,日喀則湛藍的天空,自此在我的心靈上仿佛
塌了一角。
在我10歲那年,阿媽啦做了一個神奇的夢,她夢到了佛祖。佛祖在夢中指點她,要她送我遠行,去往美國,在那里學習將是我最好的出路。她從夢中陡然惊醒,從那時她就蓄下這個想法。
也許,在你們眼里這太不可思議了,但事實就是如此。
1996年7月21日,小學畢業后,我去往美國紐約留學,暫居于媽媽的五姨家中。那時的我才13歲。
如果不曾捕捉到仁吉眼中的犀利,就不會相信仁吉在美國的一段生活:見識布魯克林貧民區生活,128中學的大姐大,手拿小刀和黑人學生比划。她說那對她倒是很寶貴的一段人生經歷,別以為公主就沒吃過苦。
五姨畢竟去美國時間不長,一切處于創業階段,生活也不盡如人意。我住在她家,條件自是不比在國內了。
她將我送往离家較近的128中學就讀。呵呵,那可真是一所可怕的中學。學校里加我,一共4名亞裔學生,不會說英語,會說點廣東話。其他學生多是黑人學生。在那里,我見識過布魯克林區最差的生活環境,也第一次嘗到背后被人突然襲擊。那段時間,我形成了一個人走著走著突然回頭的習慣。
我想也是那段生活,讓我体內另一种性格被激發,那就是反抗。我是十世班禪的女儿,我絕不允許自己宁愿被欺侮而不敢還手。當然,這一切要瞞著阿媽啦。就算我再想她,受多大的苦,我也不想在電話里透露半個字。
在那所學校,我一共呆了五個月。五個月里,我和那幫黑人學生一樣,拿起小刀,在放學后追逐打拼。他們在阿媽啦為我買的厚皮甲上留下一道道口子,也許由于有護身符護体,所幸沒有傷及我的肉体。
三個月后,阿媽啦到美國看我。知女莫若母,她從一點一滴的細節中看出了端倪,特別是她每天站在窗口目送我上學時,發現我有回頭的習慣,她知道我有事沒對她說。
在逼問下,阿媽啦知道了我在紐約的這段真實生活。通過朋友的介紹,她在美國為我找到了一位監護人。這個人就是好萊塢的武打巨星:斯蒂芬·西格。
轉到洛杉磯私立學校讀書后,每到周末放假,斯蒂芬都會派車接我回他家住。他有6個孩子,自從做了我的監護人后,他就常說他一共有7個孩子。我是他最寵愛的一個。
我這位監護人可不像他在銀幕上那樣冷冰冰的一副硬漢形象。他本人是极其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私下极其溫和,而且十分好客,家里就像一個自由市場,常常人來人往。
更為有趣的是,他很注重身材,不僅常常健身,每頓飯還像時髦女性般計算著卡路里。不能說他是我的第二個父親,但他讓我見到了美國人身上的勇敢和獨立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國給予了我家庭般的溫暖。即使在我去華盛頓讀大學政治系后,他也經常去看我。
仁吉念念不忘西藏的藏粑,也愛喝正宗的卡布其諾。如同她身上流淌著漢藏兩族的血液,中美兩國的文化也在她身上交替自如。
選讀政治對我是非常必要的。你知道爸啦生前來往的友人都是政界人物。我從小就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他們的消息。在這种環境熏陶下,從熟悉每一張面孔到關心他們做什么,久而久之,我對政治產生了濃厚興趣。
而且我是班禪的女儿,我曾發誓要繼承他的遺志,終生致力于民族團結,加快藏區經濟建設,架起中西方文化間的溝通橋梁。要做好這些,豈能不懂政治?
我在美國從沒忘記過這一理想,始終刻苦學習。在圖書館里,我常常讀書至深夜,甚至最后一個离開。還常常利用學習之余,盡力參加一些國際活動,比如在牛津召開的“藏學研討會”,訪問世界紅十字會、世界女政治家大會,擔任過學校學生會主席、洛杉磯國際學聯主席,現任西藏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世界援救協會總顧問等
,社會活動總是很丰富。
考大學那年我考上的是美利堅大學政治系,最終畢業于弗吉尼亞大學政治系。
我不否認,我在美國擁有名牌跑車,大學四年,同學多是公主或王子,這其間昂貴的費用,都要感謝阿媽啦的操持。爸啦圓寂后,曾為我們留下了房產,加上她自己也有工資。曾有過一些崇敬我爸啦的教徒,提出幫助我們,都被阿媽啦婉拒了。她希望在能力所及的范圍內,讓我盡量吃好、穿好。這不僅出于愛,她說過,我是十世班禪的女儿,過体面的生活,不僅是個人尊嚴的需要,也事關國家和藏民的尊嚴。
大學畢業前,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表示愿意接收我繼續深造。就在我舉棋不定時,去年五月,阿媽啦從中國打來電話,向我轉達了有關方面的愿望,他們希望我能回國深造,并將安排我參加中華青聯,以及到清華大學讀博。所以,我現在就在清華攻讀金融學博士學位。
在常人眼中,公主是沒有煩憂的。但我有,我有我的煩憂。如果我不是班禪的女儿,不用身負重任,我也許會做做女儿家的夢想,比如當個服裝設計師什么的。但,我不能有負眾望。
在我18歲那年,國家安排我回到西藏,那是我第一次离開阿媽啦回到家鄉。那里通訊并不發達,生活條件十分有限。可不知怎的,十世班禪女儿到來的消息卻一傳十十傳百,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或是一個村落的老老少少跑來看望我。
而他們只想得到我的祝福,只想向我獻上一條洁白的哈達。45天的行程過去了,當我离去時,大昭寺廣場云集了數万藏民為我送行。他們熱淚盈眶,口中念叨“常回來看看,我們會想念你”。
載我离去的車子越行越遠,可那些藏民還佇立在那儿,向我招手。我不斷回敬他們哈達時,胳膊酸痛得舉不起來。在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身上的擔子遠比這酸痛的胳膊更為沉重。
我知道,爸啦在保佑我,可他的眼睛也一直在注視著我……
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确吉堅贊
班禪大師俗名貢布慈丹,1938年藏歷土虎年正月初三誕生于青海省循化縣溫都鄉的一個農戶。1941年,班禪行轅堪布會議廳按宗教程序認定貢布慈丹為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迎往青海塔爾寺供養。1949年6月3日,經當時的國民政府總統李宗仁批准為十世班禪。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全國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等職。
1989年1月,班禪大師從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体合葬靈塔祀殿開光典禮時,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而去世。
董其武
1899年生于山西河津一個窮苦農家。1924年入伍。以才干為傅作義賞識,從排長逐級升任第35軍軍長。曾參加長城抗戰、綏遠抗戰,抗戰期間參加了平型關大戰、忻口會戰和著名的五原大捷。1946年底,任國民党綏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年9月通電起義。
解放后任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軍第23兵團司令員等職,曾參加抗美援朝。1953年后任69軍軍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國民党起義將領中授軍銜最高的一個。歷任全國政協常委、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1989年在北京去世。歷代班禪中,确實只有爸啦結婚,從第一任班禪大師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為第十世班禪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緣是很深厚的——堯西·班·仁吉旺姆自述
(編輯:欒樹)
(转自美国 侨报网)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
“七万言書”列舉了“七個認識”,言辭尖
銳激烈。可想而知,“七万言書”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雖對其中言論提出不同意見,但也肯定了爸啦在材料中指出的部分問題。
可是,一年多后,“七万言書”被打成“反動綱領”。爸啦受到嚴厲批判,繼而,一切職務全被撤銷,同時扣上了“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圖謀叛國”三頂帽子。
周總理曾有心保護爸啦,先將他從拉薩接到北京,安排爸啦一家人住進已故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寓所。除了參加民委辦的學習班和被安排到低壓電器厂勞動改造,那段日子,相對于倍受沖擊的老干部,爸啦過得比較平靜。
可他還不知道,痛苦,還沒真正開始……
1966年,“文革”剛一開始。爸啦就被中央民族學院的造反派強行押走,造反派鐵絲的勒痕深深嵌入爸啦的雙肩。
1968年,爸啦被再次押走,這次他被徹底隔离監護。曾有資料轉述過爸啦在監護中的生活細節,比如說他為了排解心中郁悶,曾故意和看守找事吵架,也曾砸坏過他住的小屋的窗子等等,對于這些細節,我無法證實。但試想,爸啦三歲就被迎往青海塔爾寺當活佛供養。他被關時,年僅28歲,血气方剛,哪受過這种侮辱?一個大活人,在長期無人与他交流,每天只能与冰冷的鐵門、灰暗的單人牢房相伴,未來看到的只有遙遙無期的監禁,他怎會不煩悶、不憤懣?
關爸啦的小屋僅僅八九平米,屋內除了一床一桌一椅,設施极其簡陋。屋子的窗戶上設有一個漏斗狀的小窗子,看守正是通過小窗監視里面的一舉一動,而爸啦則無法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他知道,离他最近的就是當時的北京副市長万里。再過去就是彭德怀元帥、羅瑞卿將軍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因為曾是“隔壁近鄰”,所以,爸啦平反后,我們家与万老家走得最近。
為了不使光陰白白流逝,爸啦除了每天在屋內誦讀佛經,就是學習漢文和馬列著作。所以日后,原本只會說藏語的爸啦除了能說一口流利漢語外,還精通馬列著作,并將一本藏文字典翻譯成了漢語。
可這些仍無法排遣他內心的寂寞。爺爺、奶奶那時盡管健在,但都不屬于能探視他的人員,而當他每每得知其他難友的妻儿探視時,就會因為自己無人噓寒問暖尤其感傷。
微笑的仁吉,紫色的眼影,精致的淡妝卻掩蓋不了她眼中的一絲銳利。她說是雙子座的女孩,自然會有雙重性格。而且她身上流著藏傳佛教領袖的血,還有她親愛的阿媽啦的血,這就像性格的兩面:堅強和溫柔。在西藏,她屬于“團結族”。
是的,在藏區,如果父母一方是漢人或藏人,那么,他們生下的孩子就是“團結族”。這沒什么,我爸啦一生光明磊落,我是他的女儿,這點性格也极像他。
十年牢獄生涯,令爸啦身心疲憊。解禁后他更加渴望擁有一份俗世的家庭幸福。
1978年,中央組織了一批像爸啦這樣特殊的民主人士,讓他們出游看看祖國山河變化。于是,一支考察團隊就這樣形成了,帶隊的副團長正是阿媽啦的外公董其武。爸啦在這支團隊里年齡最小,与他能夠親近的反倒是我太姥爺
身邊的警衛員。在兩個月的接触中,爸啦向這名年輕的警衛員袒露心跡:他想找對象結婚。警衛員是個熱心腸,滿口答應幫爸啦物色對象。
活動結束后,警衛員找到我的阿媽啦說,小洁啊,我們團隊里有個叫班禪的,你能不能幫他介紹一個女軍人啊。
沒讀過什么書的警衛員雖和爸啦相處一段日子,可他對班禪的歷史掌故知之甚少。阿媽啦從小生長在太姥爺身邊,常識典故耳濡目染。高中畢業后,她先在太姥爺的69軍當醫務兵,后又考入第四軍醫大學軍醫系。想來那時的她,雖未曾見過班禪一面,肯定也是久聞大名。對于一個19歲的少女,“十世班禪”無疑充滿太多傳奇。
加之阿媽啦生性活潑開朗,也是一個熱心腸,得知此事后,馬上熱忱張羅開來。要為男方作介紹人,豈能不見他本人一面?于是,阿媽啦請警衛員代傳口信,她要見他本人一面。
不知為什么,警衛員沒把事情向爸啦講清,爸啦這邊以為是正式見面了,而阿媽啦也帶上她的五姨一同赴約。這种場面,也難怪爸啦會產生美麗的“誤會”,如今想來,也許全是命運使然。
我無從得知,爸啦第一次見到阿媽啦時的感受,但你可以看看阿媽啦少女時代的相片,她是那么美,一雙眼睛顧盼神飛,极顯聰慧。面對這樣一位优秀的女性,爸啦即使真的“錯認”了,他肯定也是愿意“錯”下去的。
不可能有戀愛經驗的爸啦,率性如他,一開頭就向阿媽啦坦言,自己一無所有,什么都不可能給她。不光如此,因為自己沒有徹底平反,如果兩人真走到一起,她還要做好隨時同被監護的心理准備。
這番話留給了阿媽啦极深的印象,她過去還不曾得知有誰會剛一認識,就如此坦白的。也許,正因此,兩人的愛情真正萌芽。
對于他們的婚姻,阿媽啦的家人自是不看好,要從中反對。首先,男方大女方很多,雖然是尊貴的十世班禪,但畢竟頭頂上的“三頂帽子”還沒完全摘掉,盡管如此,1979年1月,阿媽啦還是嫁給了爸啦。此后,爸啦嚴守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戒律,從此不再作為出家人穿過袈裟,只穿華貴藏袍,即使參加重大的宗教活動,也毫不避諱自己已有妻室。
十世班禪44歲那年,他得到了至愛珍寶,仁吉。仁吉翻開了那一本厚重的相冊,一遍遍地說,我真是他的掌上明珠,我一直都過得很幸福,可是爸啦与我生活的短短几年,才是我最幸福的時光。說著說著,她低垂的眼瞼隱隱閃動著淚光。
我出生一百天后,鄧穎超媽媽和習仲勛伯伯來到我家。我的小名“團團”就是鄧媽媽起的。鄧媽媽抱起我,說這小女娃儿的臉蛋團團的,干脆就叫她“團團”吧,而其中另一層深意,也是希望漢藏民族間能團結和諧。
爸啦可真是疼我啊。如果他在家開會,要求絕對的安靜,沒有任何一個人敢隨意走動,唯有我可以跑出跑進,一會儿跳到他的大腿上,一會儿摟著他的脖子膩著他。
也許正是因為聆听佛經長大,我也比較早慧。從小過目不忘,即使一歲多時所見,現在依稀還能說出几分,這常讓阿媽啦吃惊不已。而早慧如我,又怎會忘卻,1989年1月爸啦的离去。
以往為爸啦送行,往往只要送上机就可以了。可那次,爸啦十分戀戀不舍,一次次讓人叫我進艙內,一次次叮嚀我很多事情,比如要好好學習,將來做他的助手;一定要听阿媽啦的話等等;當時陪在爸啦身邊的活佛們事后回憶說,我們母女离開他后,爸啦曾真誠地對他們說,這次他离開我們,內心非常難過。希望活佛們以后能像照顧他一樣,好好照顧他的家人。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