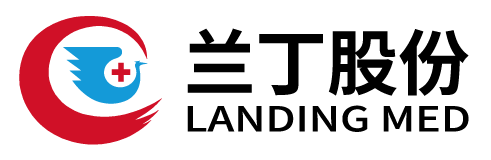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fw]美丽的悬念——徐悲鸿与孙多慈
美丽的悬念
一九三O年,一个时常漫步南京城墙的年轻才女闯入了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她叫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蒋碧微回忆录中称她孙韵君,据说是她的原名。
徐悲鸿对刻苦而有才华的学生非常欣赏,其中就有女学生孙多慈。
这是一个令无数后人感叹与疑惑的美丽悬念。
由“敬爱吾师”延伸成“平生知己”?而徐悲鸿又如何由欣赏之情转化为刻骨之爱?究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冲破年龄差距与世俗藩篱?
性格即命运。简单地以情人来形容,实在是太表面化了。
孙多慈与蒋碧微一样是大家闺秀,不同的是性格有天壤之别。蒋碧微刚烈如火,她想得到什么,就会舍命争取。孙多慈则柔情似水,她会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的孙多慈,到南京投考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没能录取,转而到中大艺术系作旁听生。孙多慈写诗作画的天赋加之勤奋,使她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徐悲鸿只要发现哪个学生才华不凡,就毫不吝啬地加以赞扬,愿意多给些指导。
次年暑期,孙多慈投考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阅卷的徐悲鸿给她的绘画作业打了95分,孙多慈以本届考生最高分被录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央大学校园,中国的顶尖学府,孙多慈的出众也不难理解。命运把美貌、聪慧、善良、温婉都给了她,加上贵族家世和优雅举止,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其祖父孙家鼐,清末进士,官至光绪年间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其父孙传瑗,国学教授,古诗文造诣浓厚,对长女多慈疼爱有加,自称“平生爱女胜爱男”。
大户人家的见识,使孙多慈幸运地逃脱旧式女子的命运,可以不缠足,可以从小跟男孩子一样上学念书。如果说美貌毕竟与生俱来,那么学识与教养无疑是后天的。有的人家虽然有钱,也不愿送女孩子读书。而孙多慈家人却有些现代教育理念,对女儿同样栽培,这也影响到孙多慈的人生态度,对父母言听计从,恪守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
徐悲鸿发现孙多慈内秀而外美,像发现一块璞玉,对她备加呵护。他画孙多慈肖像素描,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其艺Mir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弛然自废之无济耶!”
课堂上的素描课,徐悲鸿关注着孙多慈的动作,细心地给她修改习作。看徐悲鸿做绘画示范,本身就是一次艺术享受。而在徐悲鸿的画室,孙多慈有时是一个观摩者,有时是一个被画者。他们从艺术谈到人生,从写生谈到油画,孙多慈对恩师的点拨心存感念,但她毕竟出身书香书门,并无非分之想,而徐悲鸿,也不曾有舍弃家庭的念头。
风言风语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大怒,甚至大吵,不能容忍。她有她的判断:“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察觉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在徐悲鸿与孙多慈相识初期,并没有超过师生之情,应该是真实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赴法留学十年的老同学盛成回国,去看望徐悲鸿。巴黎一别,南京再见,畅谈甚欢。徐悲鸿一本正经地问盛成,成家了没有,盛成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徐悲鸿一听连忙说道:“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很不方便。我给你介绍一位最得意的女学生。”
徐悲鸿向盛成介绍孙多慈的身世,拿出孙多慈的诗作,盛成一看,字迹漂亮,文采飞扬,果然是一个少有的才女,也非常赞赏。徐悲鸿告诉盛成,明日他为孙多慈画像,蒋碧微去宜兴了不在家,请盛成也过来,大家一起聊聊。
盛成说:“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丹凤街中大宿舍的悲鸿寓所,一上楼见悲鸿正在给孙画像。因为昨日同悲鸿通了消息,我就坐在一旁,注意观察孙多慈的言谈举止,但直到结束,我对她也没有产生什么好感,至少我感到她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头脑中产生了第一个印象后,我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没有再去丹凤街。”
盛成与孙多慈无缘,徐悲鸿的媒人没有当成。这也说明,徐悲鸿当时对孙多慈只限于一个师长的关怀,也许他欣赏孙多慈的内在之美,是年轻的盛成无法体会的。徐悲鸿为孙多慈画肖像,画出的眼睛美丽无邪,清净如水。
我在重庆采访了一位九十八岁的老教授,他是孙多慈的同班同学。
对徐悲鸿的敬重,老教授是由衷的,说起徐悲鸿对每个学生的关爱,可以举出许多生动事例。但他说到孙多慈,就是不承认孙多慈比其他学生画得好。只是说:“徐先生看中孙多慈画,还不是因为喜欢她这个人,孙多慈画的画,也就是这样啦。” 虽然过去这么些年,我似乎仍感觉到小男生的醋意。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偏爱很公开,他说孙多慈聪慧绝伦,无人能比,惹得个别男生暗生不满。其实做徐悲鸿学生,早已习惯老师对尖子的夸赞,可孙多慈受表扬却让人妒忌。班上难得有个美女同学,本该是男生梦中情人,却不给同龄异性一点机会,自然叫人酸溜溜的。有人跑去找徐师母蒋碧微告状,说徐先生和孙多慈太近乎,别人像在陪公子读书。
学生们是冲着徐悲鸿来报考中大艺术系的,指望老师广布恩泽,确也无可厚非。找徐师母打小报告的学生并不知道,蒋碧微听来并不新鲜,徐悲鸿确实对孙多慈极为喜爱,已经当面向她坦陈了一切。显然,徐悲鸿开始在感情旋涡中挣扎了。他的坦陈说明他做人的真诚,也期待蒋碧微的理解和宽慰,他说:“你不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再到国外去。”
徐悲鸿太天真了。他以为坦白是个契机,能弥补他与妻子情感的空白。蒋碧微的大声哭骂,像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叫徐悲鸿幡然猛醒,内心的愧疚随之冲去。他懂得蒋碧微不会知道他需要什么,彼此隔阂更加深刻,渐行渐远。
而对孙多慈的无辜牵连,徐悲鸿尤为焦虑。他绝非怕事之人,拔刀相助的个性使他不会抽身而退,反而点燃了他久违的激情。一团死水的家庭气氛,是怜香惜玉到萌发爱意的催化剂,难舍难分的情愫冲击着横亘于师生之间的道德之藩。
试图给孙多慈与盛成牵线一年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又是一段众说纷纭的史实,幸而徐悲鸿自己给出了答案。
如果说,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开始并非一见钟情,有徐悲鸿友人为证。但他们后来超出了师生之情,这也是一个事实,而且也有人证。他不仅是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也不仅是一个画家和一个教授,他还是一个情感充沛、有血有肉、义字当头的七尺男儿。
徐悲鸿感情的丰富层面,实在是太复杂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徐悲鸿给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写信,谈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矛盾感情。舒新城是著名出版家,也是徐悲鸿极其信赖的挚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徐悲鸿说:“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此诗为孙多慈而写:“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正式出版的《中华书局收藏名人书信手迹》长卷中,我查到徐悲鸿给舒新城写的这封信原件。舒新城理解友人的苦衷,他自己也经历婚变,似乎并没有太多麻烦,可能在他看来,是徐悲鸿太多愁善感了吧。于是,复信作答曰:“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读来怅然,不知是劝告,还是鼓励。
诗以言志,画以抒怀。徐悲鸿少有的委婉柔情,一泻无遗地倾注在油画布上,完成了人物油画《台城月夜》。可惜,我们无法看到这幅徐悲鸿创作鼎盛时的画作,只有蒋碧微回忆录中有文字记载:“画面是徐先生与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处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地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画作,当初是想送给盛成的,徐悲鸿很满意,摆放在学校自己画室最显著的地方。蒋碧微陪着朋友到学校找徐悲鸿,徐悲鸿在画室泰然自若,倒是蒋碧微颇为尴尬。徐悲鸿给朋友看别的画,蒋碧微动作很快,把《台城月夜》和另一幅孙多慈肖像拿来,请旁边一位学生替她送回家,等于把画没收了。
蒋碧微说的这件事,有另一个当事人,就是徐悲鸿的老同学盛成。
盛成晚年回忆说:“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还住在友人欧阳竟无先生那里。悲鸿来看我们,谈话间欧阳竟无先生提出想观赏一下悲鸿新近创作的画,悲鸿也很高兴,约定翌日在中大等我们。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欧阳竟无先生坐车来到丹凤街见到了蒋碧微,我们邀请她一起去中大参观悲鸿的画室,她欣然表示赞成。
“到了中央大学,一行人先参观艺术系的画室,里面放着不少悲鸿的作品。欧阳先生说希望看看悲鸿刚刚完成的新作《田横五百士》。悲鸿一面答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蒋碧微上前一把拿了过来,转身向后面的画室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打开后面画室的门,蒋碧微一步跨进去,四下寻找,发现了那次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半身像,还有一幅题着《台城月夜》的画,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把两幅画抓在手里。
“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碧微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罢。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微就对我讲,悲鸿病了。我问她,人在哪儿。她板着脸说,在他房间里。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蒋碧微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这里哪有你的事体!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无疑是蒋碧微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徐悲鸿当时画在一块大的三夹板上,当他要给一位老友的父亲画像时,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画了新画。这幅可能成为一幅名画的杰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然而,另一幅孙多慈的肖像画,画着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却保存至今。
蒋碧微曾经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她对徐悲鸿不能说没有爱,但她的优雅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徐悲鸿总是一味退让,而不去跟她争辩。当孙多慈被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后,蒋碧微怒不可遏,焦虑异常。她担心这位才貌双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与徐悲鸿天天见面,那可能真是分不开了。她对徐悲鸿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国外去,你该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吧。”
徐悲鸿当然听出蒋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声辩,沉着脸,写了一封辞职信,叫她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蒋碧微舍不得放弃教授夫人的地位,没把这封信交出去。徐悲鸿这回是铁了心。当晚他们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鸿说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佣人告诉她,徐悲鸿匆匆回家,把衣服装进一只小箱子,没说什么话,就不告而别。
徐悲鸿在南京离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鸿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作翔实的补充。
“舒新城日记里记着,徐悲鸿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请几个留法的老同学,搞文学的,在舒家吃饭,蒋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说,不许中央大学收孙多慈这个学生,或者你辞职到法国去。徐说:你跟着我在外面闯了十几年了,你应该自立于社会,我每月三百大洋,给你一百五十大洋。蒋不同意。看到蒋打上门的泼辣性格,舒新城担心地说,这样下来,必然成为悲剧。”
不知何故,蒋碧微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鸿与蒋碧微的争执,总以徐悲鸿的默然作为结束。而徐悲鸿竟然出走,令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措手不及。蒋碧微自己回忆说,当她托友人四处寻找时,徐悲鸿从上海寄了封信给她,诉说他离家的原因。信中说:“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总之你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南京师范大学与徐悲鸿的名字分不开,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徐悲鸿曾经执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划入南师大美术系,美术系近年又扩展为美术学院。而今南师大老校区,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旧址。
在南师大美术学院的资料室,保存着徐悲鸿亲笔批注的石印教材,这是美术学院引以为自豪的珍贵文物。我去采访时,资料员抱出一大包来,深灰的封面,遒劲的书法,原教材的题目与徐悲鸿的批语浑然一体。《吴昌硕画册》:“须深会此意,不可仅徒以貌求之。”《吴兴金北楼画册》:“绿肥红瘦,可称佳作。”《郎世宁画乾隆皇帝春郊试马图》:“虽无韵致不失精”。《某山水画集》:“恶劣”,《某花卉合册》:“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鸟草虫合册》:“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师大绘画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导学生画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动逼真,似乎在它们周围,仍萦绕着徐悲鸿教课的声音。高柏年说:“徐悲鸿带回来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两米高,有的超过两米多。其中包括,一个全身的《维纳斯》,两个全身的《奴隶》,一个全身的《掷矛者》,还有一个全身的《斗士》和一个《掷铁饼者》。”
在欧洲留学期间苦练素描写生的徐悲鸿,曾经得益于西方大师的雕像。当年赴欧洲留学、游学、考察的人数不胜数,惟有徐悲鸿带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无私地献给中大艺术系,填补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空白。它们曾经培养过几代学生,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们面前写生的学生,早已成为很有声望的画坛名家。
学生画石膏像写生熟练了,徐悲鸿就安排裸体人物写生课。先从上海请来一位女模特儿,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鸿对模特儿很尊重,也要求学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怀好意,曾问艺术系学生徐风说:“学生作实物写生为何要用裸体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风照搬徐悲鸿的话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徐风把这段对话告诉徐悲鸿,徐悲鸿感慨道:“你讲得对!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存在,无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见多怪!知道这种观念不合时代潮流,转变也不容易。根本的办法,还是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做努力吧。”
同样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曾经主持过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画家韦启美至今难忘的,是徐悲鸿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体味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精华。此时,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开始形成,那就是重视基础、师法造化、中西结合、提倡写实主义。中国美术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经融入徐悲鸿的教学之中。
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是在今天的东南大学主校区。中大的礼堂还在,圆型苍穹的标志性建筑,曾经是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中大著名教授讲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艺术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树丛中留有一处平房,屋檐中间横匾曰“梅庵”,是仅存的中大艺术系教室。踏在吱吱作响的红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鸿和他的学生并没走远。
“梅庵”前一棵老松树,高大的躯干上绑着支架,柔韧的树枝成弧状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秃秃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绿色。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据说是六朝人种植,与南京古城一样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鸿和他的学生有一张合影照片。时间应该是春天,穿着西装的徐悲鸿怡然含笑,旁边的同学也都放松自然,女生则身着毛衣,把脱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着的孙多慈亭亭玉立,脸上没有任何苦恼的痕迹。
命运似乎对她格外关照。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满足了一个女子追求艺术的愿望,而遇到画坛大师徐悲鸿的悉心栽培,学业大有长进,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丽,太年轻,在校园如鲜花一样开放,很难想像世事的艰辛、人心的叵测和莫名的妒忌。
据说,在上海舒新城家聚会的几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内,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婚姻生活都有了变故。有的是在上海结识富家小姐或者知识女性,有的是在异地遇到红颜知己,好在西风东渐,离婚并不是难事,他们快刀斩乱麻,无一不与原配夫人离异,组建了新家庭。他们看着百愁莫解、坐拥愁城的徐悲鸿,劝他尽快作一个了断。
徐悲鸿却说:“我没有想过跟谁离婚,也没有想过跟谁结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这么说,回到南京对蒋碧微也这么说。上海友人笑他太书生气了,而蒋碧微则认为他心口不一。其实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他任凭情感泛滥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他处理感情与家庭的方式,未免书生气,又新潮又守旧,一败涂地。
一场家庭暴风雨过后,没有雨过天晴。
徐悲鸿蒋碧微所执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离方向之后,又进入以往的生活轨道,他们仍成双成对地出入社交场合,在众人面前带着微笑的面罩。徐悲鸿继续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蒋碧微也并不拒绝徐悲鸿成功带给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们之间默默滋长。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已是昨日黄花,比争吵更无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6-12-13 18:32:00 编辑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