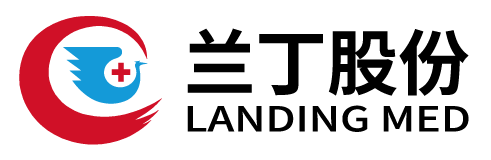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美学心得(第二百一十五集) 罗国正 (2020年10月)
美学心得(第二百一十五集)
罗国正
(2020年10月)
2937、明清之际文学家贺贻孙指出:创作应“以吾之手就吾之性,以吾之才就吾之学,引而伸之,触类旁通,则异者可同,二者可一也。”他认为“天下极假之事,必以极真之功力为之。”他以自然景色的不同和变化来比喻文章的特点:“太华千仞,崱屴无垠,呼吸天门,环抱日月,若是者高厚也。”“屈注天池,倒连溟勃,蛟龙百怪,变眩莫测,若是者博厚也。”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身纳山河大气,笔锋洋溢自然之美。经年努力不息,心有灵犀,水到渠成,厚积薄发,举一反三,融汇贯通,内慧外秀,渐至高厚、博厚的艺术境界。这是大多数成功的艺术家必由之路,这也大概是贺贻孙所言之意。
2938、明清之际,戏曲家丁耀亢提出:“清者以浊反,喜者以悲反,福者以祸反;君子以小人反,合者以离反;繁华者以凄清反。”他用对应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讲出了中国古代悲喜剧艺术规律。
2945、清朝文学家魏禧说:“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必然”。“虽极工巧,凌轹古人,皆雕虫耳”。“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郁积于胸中,必有所发,不发于事业,则发于文章”。“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他又主张这样审美风格的文章:“阴阳互乘,有交错之义”。“洪波巨浪,山立而汹涌者,遭之重者也;论涟漪瀫,皴慼而密理也,遭之轻者也”。“重者,人惊而快之,发豪士之气,有鞭笞四海之心”;“轻者,人乐而现之,有遗世自得之慕”。“要为阴阳自然之动,天地之至文,不可偏废也”。他认为静的艺术是最高境界:“夫尺幅之画,山、水、草、树、石、楼台、人物之形,风云之变,纷然难出其上,素之所馀,几不足以容指。而善画者之画,则若未尝有一笔一墨之着于其间,此何以哉?静故也”。
魏禧的观点有点偏激,只属一家之言。但其中也有不少闪光点。关于散文,他主要从儒家六经的传统“文以载道”,“明理适事”。他反对“八股文”,认为它违反了散文的写作规律。“载道”与“有用”,以至“实用”之间的平衡,开卷有益、有趣、入心、令人回味,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提出文学艺术要“阴阳互乘”,我认为这观点没错,问题是他只认为静的艺术是最高境界,这就与这些观点相矛盾。动与静的艺术各有其最高境界的美。例如舞蹈艺术、书法艺术,就不能只强调静为最美。事实上,有的艺术须要静的美,有的艺术须要动的美。同一艺术,在不同部分、或不同段落或不同时段,对动与静的处理,都有所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待续)
(本集责任编辑:严建中 詹邓)
2944、清朝音乐家庄臻凤说:“琴乃天真元韵,音出自然”,“鸣琴乃除忧来乐之意”,“拘之则音乏滞”,主张“得心应手”,“或偶得名人佳句”,“或因鸟语风声”,“感怀入耳”,“谐音谱词,费尽勾思”,“音律句读,弗类他声,若不发明,难于入彀”。初学之人,“必借名手摹出,方可再弹”。“难弹处正是琴中骨理”。
庄臻凤主张音乐是用来愉悦情感,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反对使人增加惆怅悲怨。这样理解音乐艺术有偏激,但却符合很多人的实际需要。他说:“必借名手摹岀,方可再弹”。“难弹处正是琴中骨理”。这两句话道出百业千行的道理。使我联想起十几二十岁时,常与武林高手练功,练完之后,多在公园里边散步边聊天,常见到一些年青人天天非常勤奋地练功(很多个公园都有这样的年青人),但多年之后,见他们进步都不大,我们都为他们可惜,这样太浪费青春岁月了。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跟的老师傅,是年轻时只是跟人学过一两个武术套路,还学得不到位,根本上没有系统地、认真地较长时间苦练过,到晚年,为了挣点钱,就自吹自擂,有些年轻人就相信了,跟他练武。从他打出来的动作,给我们的印象是:动作生硬,不连贯、断劲、没有灵通感和气场感。第二个,连找个师傅都不想,到书店买本书,天天就照着书本在公园猛练。多年以后,只见他们人变老成了很多,但功夫基本没有长进。在书画方面,这样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一定要找对老师、或师傅,除了有特别天赋的人外,不然的话,用功一辈子,只是个写字匠,画画匠。所谓名师出高徒,就是这个道理。找到名师,是幸运的,可以节约时间、精力、财力,还可以练出真功夫。
2943、清朝印学家许容,治印别树一帜,被称为如皋派,他说:“执笔为法书之关键”。“必须笔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自然,以尽字之真态,妙合天趣”,“方圆平直,无不如意”。“执笔之法既明,然后可以刻印”。再而达到“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各有其宜,毋涉于俗”,“其文已不杂,章法、笔法皆已完美,然后用刀”。
许容明确书法是治印的基本功,这观点也几乎和所有印学家一致。我长期以来总是感觉现存的很多书法理论,还没有将书法的作用讲透,其实中国书法是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很多个方面的基础,如国画、治印、修定力、练气、审美能力的培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学习、弘扬真、善、美等等,都起到很大作用,绝对不可轻视。真迹、真气能留在作品中,可世代激活龙的传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并可为灵魂开窍。
虽然许容的观点,基本上已有前人论述,但他归纳得很好,如:“必须笔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自然,以尽字之真态,妙合天趣”。这是到了非常纯熟、炉火纯青状态的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或方可达到的境界。又如:“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这不仅是书法、篆刻、绘画、雕塑等艺术力求做到,其实,很多方面的事业、工作也可以此句为格言。人们应举一反三地感悟、运用。
2941、清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享年九十岁,在古代这样的岁数,是非常长命的。)说:诗最忌卑荣,扬子云以雄词为赋,然其自言犹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盖文有士气,有丈夫气;旧人论诗极忌庸俗,以其无士气也;且又恶纤弱,以其无丈夫气也”。“凡言格言律,言气言调,当以气为主”。 毛奇龄对诗和文的审美,非常强调“气”,不但有“气”,还要有“丈夫气”,“士气”。他这理念,很像中医强调的“气”,中医认为,没气就没命。而毛奇龄所讲的诗与文的“气”也达到这级数,没有了“丈夫之气”、“士气”,则诗与文也等于没命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他比较长命,是否与对中医的“气”和文学的“气”的注重有关?这大概是“文之气”,主要是心理调节,“中医之气”,主要是生理调节吧!当然,从他的经历来看,大部分时间也是有条件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2942、清朝文学家汪琬主张“文统”与“道统”的统一。他说:“人之有文,所以经纬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于晦且乱,则人欲日炽,彝伦日斁,天地之道将何托以传哉”!“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他强调“才气”,并说:“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之举也”。
我以为,凡能创作出优秀文章、包括各种艺术品的人,绝大多数的作者,他们的心中都有信奉的“道”,只是人们是否认可具体创作主体心中的那个“道”,或能否理解他的“道”。古今中外也如此。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普遍人对具体作者的“道”,不理解、或不认识,或对此作者的“道”与主流公认的“道”不同,就认为其“无道”。但人们不反问一下,完全“无道”的人,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吗?我以为这种可能性趋向于零。在中国古代,较为通行的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盛行,大量作者取其一家,或多家的思想作为自己作品的理念,作为“道”贯彻入内。其实,真正的“大道”只有一个,其它都是“小道”。提倡“大道”,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有利于人类,具有人性。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每个创作主体,在现实的体验中,思考里,通过特定的角度,抓住具体的细节,力求用优秀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气场很大,实现以小见大,这就是汪琬所说的“才与气之举也”。
2940、清朝画家笪重光,是顺治进士,官御史,享年六十九岁,主张浑与清、情与象、动与灵相结合来绘画。认为书画同源,“绘心”即“文心”;诗文书画,相为表里;画家人品与画品一致,“人非其人,画难为画”。他说:“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抚缣素。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实境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他还说:“画能如金刀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
笪重光注重用对应的美学范畴来表现画的结构,强调写实景为山水画传神,主张在继承上有所创新,认为博采众长,长期积累文化修养是提升绘画能力所必须。笔划与留白是互相依存、制约的,懂得“计白当黑”。他的“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对后世影响较大。现在的书画家都常提及。
2939、明清之际文学家侯方域认为文章重在“骨”和“气”:“秦以前之文主骨”,“皆敛气于骨也。”“如秦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嶝,非仙灵变化来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而“汉以后之文主气”,“皆运骨于气者也”,“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泊西注,未知其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
显然,侯方域是推崇秦汉文章,审美的焦点在“骨”和“气”上。这些观点,在他之前的文人已有类似的提法,而且不单在文章、诗词上有这种提法,书画家也不少主张要“骨”和“气”。当然,不同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偏好。平心而论,无论是文,还是书画,单凭“骨”和“气”是不够的,我认为应具有以下几个要素:灵魂、主题、骨、气、血肉。灵魂是首位。大家试看看,古今中外,优秀的文章、优秀的艺术品,基本上都是有我所讲的要素,单凭“骨”和“气”是难以完成伟大作品的。好的文章、艺术品就像永远有强大活力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肯定是有灵魂的。
侯方域主张“必先驰聘纵横,务尽其材,然后轨于法”。“必先游览天下”,“又必其有无饥无渴齐毁齐誉之性情寓其中,而后进乎技也”。
我理解他的意思为:从精神到身体、从读书、思考、游览、社会实践,从荣耀到羞辱等等全方位尽量经受极限性学习、体验、磨砺后,进入“轨于法”,“进乎技”。
候方域河南商丘人,明未随父居京师,是“四公子”之一,福王时,被阮大銊捕,后得免。顺治其间,中式副榜。初放意声伎,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恋,演成有名的《桃花扇》。后发奋诗文,在美学上有见解。他很有才气,可惜只享年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