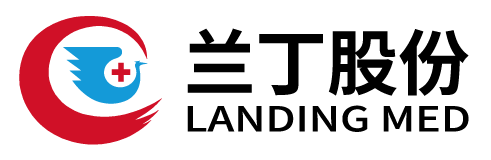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垂钓随笔
总感觉我的家乡是一个水城,沟壑纵横,无数的细小河流在青翠的丘陵间徘徊,迟迟的不愿离去,暮日里闪烁着点点金光。


夏季的旱情仿佛也如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仿佛时光久远,不再深刻,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自来水,无需挑水吃的缘故。冬季尤甚,总不肯散去的雾,白蒙蒙着一切,人要是站在高处俯看,不由得会高声赞叹:好一片壮观的云海!只可惜,高处总是不多,绝大多数都在云海里穿行,稍倾,就有水从发尖坠落,倘若再有一阵风,就有些叫人受不了了。

乡人好辛香,概因潮湿。于是,菜里就有为数不少红艳艳的干辣椒,以去潮气,乡人风湿较少,与奢辣有关。椒种得多,相应,处理办法更多,最常见的是泡椒。各家各户都有几个大体是圆的坛子,与世隔绝的常年浸泡着各种的蔬菜,最多的是罗卜、辣椒和生姜这老三篇。此三类以时间泡得愈久愈好,家有陈年泡菜,有时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我一直相信,这种极陈的泡菜在密闭的坛子里已经完成了一种神秘的化学反应,滋生出能强烈刺激味蕾的,并能将油脂分解溶于汤的酶。“酸罗卜炖老鸭子!”乡人大声招呼,不由得口内生津。







能活到几年,算得上的老的鸭子也是不多,因此,泡菜更多的拿来做鱼,做鲜鱼。一个极陈,一个极鲜,这两种有天壤之别的食材一相逢,造就一台轰轰烈烈的历史与现实大戏。

剁细的泡菜,沸腾的油锅,“哧啦!”初遇时发出一片惊呼,不妨再投几段葱白,我喜欢戗葱白的味道。猛火慢慢的爆,待得泡菜的味道完全渗入油中,下郫县的辣椒豆瓣,阆中的保宁醋,投几十粒花椒,有新鲜的尤佳。翻炒几道,加瓢水,滚若干滚,便可往火红的汤中入鱼,千煮豆腐万煮鱼,此时关火至最小。

现在,就有时间,点上一支烟,或静坐消疲,或追着小儿满屋乱跑,玩一些猫捉老鼠或老鼠捉猫的游戏。待得有浓香弥漫,深深吸一口,陈泡那馥郁而纯厚的味在前,鱼鲜那清灵活泼的嗅觉在后,相互交融而又层次分明。


乡人善吃鱼者众,尤其精湛者可将两许小鲫骨刺悉数理出,珐琅质的骨刺不会有一丁点肉丝,完整得几乎就如同化石。据称,如此弃骨就是瘦狗也不会感兴趣,江湖间也就对精通此类者赠送雅号:狗见愁。小儿甚喜鱼眼、鱼鳔,别的大致是不理,倘若是在古时,被那强人剪径,定会断定是大户人家的公子,殊不知,他不过是有一个爱钓鱼的老小子罢了。

标签:



 ,钓鱼可真是考验人的耐性哈,呵呵,看到成果还不错嘛,有那么大的<。)#)))≦(鱼)
,钓鱼可真是考验人的耐性哈,呵呵,看到成果还不错嘛,有那么大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