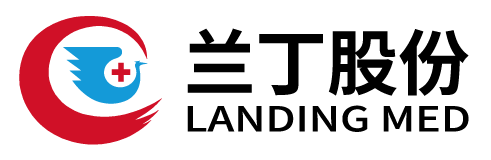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长篇小说连载)爱,永不止息(全文完)
彦锐当时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助理,一个月拿着一千多的工资,名为助理,却和打杂的没什么区别,受尽白眼和欺负。于是,闷声不响的报名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
彦锐是个执着的男人,一旦下了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律师资格考试,比起公务员考试,不知难上多少倍,更不知多少人从拥挤不堪的独木桥上掉下来,摔的血肉模糊。彦锐连续考了两年,两年落榜。我们相识的那一年,是他第三次报考。他后来告诉我,那一年,他孤军奋战,身边所有的人都不支持他,父母甚至嘲笑他是异想天开。
面对白眼和嘲笑,彦锐抱以沉默。夜里,每当读书读累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窗台上,点燃一根两块五一包的长城,在烟雾缭绕中看星光闪烁的夜空。
尽管我们在同一座城市,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气息,经常走同一条小街,用同样牌子的牙膏,甚至对同一家面馆同一种口味的面,情有独钟。但如果没有网络,我想,我和彦锐,会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但是,网络这张奇妙的网,却在一个特别的冬夜里,将他和我从各自的人生轨迹上,拉到了一起。
我和彦锐的相识,是偶遇,也是宿命。
不知不觉,母亲离开我已经两个月。回到学校后,在亲友和同学的关心下,我慢慢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但思念和悲伤依然不减,只是被我强压在心底的最深处,不能碰,也不敢碰。
我清楚的记得,那一晚黄昏过后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室友们相约出去逛商场,我素来不喜欢商场之类的娱乐场所,所以一个人留在寝室里,用室友的电脑上网。正百无聊赖的盯着网页发呆,屏幕右下角的小喇叭伴随着欢快的“滴滴”声,闪烁个不停。
点开一看,是一个叫做“琴心三叠”的陌生人发来的加为好友邀请。想也没想,点了拒绝。不到两秒钟,又是他。扫了两眼,再次拒绝。没隔多久,还是他。有些烦了,狠狠的用鼠标点下拒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我胸中的不满。可是,对方依然执拗的邀请不断,我的脸因气愤而有些发热,但慢慢的,气愤又变成了好奇。我突然很想知道,对面的那个不断被我拒绝的男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怎样的原因,让他锲而不舍的,非要加我不可。
在好奇的驱使下,我轻轻的挪动鼠标,迟疑了一会,终于点了“接受”。
彦锐,就此,以他略带无赖的执着,闯入了我的生命。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理论课授课全部结束,我终于结束了神仙般的逍遥日子。
小雅、芳芳和我,是老板这一届新收的三个学生,戏剧化的是,我们三个最初没有一个报的是现在的专业。小雅和芳芳最初报考的是血液,我则选择心内。复试后,因为两个大科室招生皆满,于是在科教科的调剂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皮肤性病科,一个小医院通常不设,而大医院不得不设,却设置而不重视的小科。
本科临近毕业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接到科教科的电话,告知我原来报考的心内科已招满,是否同意调剂到其他科室。而当时只剩两个科室可选,皮肤科和感染科。
那时候,母亲还在世。有母亲在的时候,我习惯性的凡事都事先征求母亲的意见。这一次关于前途的抉择,自然更不能儿戏。我向科教科争取了一些时间,想和母亲商量之后再做答复。
我考研那一年,非典刚刚过去,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母亲的意见是让我选择皮肤科。她说,我儿从小体质就不好,免疫力又差,如果再来一场非典,还没等冲上前线救死扶伤,自己先壮烈了。女孩子家家,还是学学小科目,平安又安逸的过一生,挺好。
母亲的一句话,让我于众多饭碗中,歪打正着的选中了如此独特的一只碗。
我曾经问过很多同行,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医。有的说,为了光宗耀祖;有的说,为了子承父业;有的说,为了给亲友看病方便。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缘由,总不能一一细数。
我选择从医,却还是因为母亲。
当年报考,母亲问我,想学什么?我很茫然。母亲建议,学会计吧,这是个好职业。我摇头,讨厌每日和数字打交道,多枯燥!母亲又提议,学兽医吧,你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将来去为小动物们看病,正合适你。我还是摇头,正因为喜欢小动物,才不忍心看着它们痛苦,更不忍心在它们身上开刀。母亲叹气,那学中医中药吧,将来学成之后,在老家种上一大片药田,勤勤恳恳,发家致富。我还是摇头,我不喜欢中医,也讨厌中药味儿。
母亲终于火了,一拍桌子,小兔崽子,你到底想干啥?!
我缩了缩脖子,斜着眼睛,瞄了瞄母亲气得发抖的手,想起她终年被病魔纠缠,身体每况愈下。想到这儿,梗起脖子,冲母亲嚷道,我要学医!
母亲愣了愣,立刻眉开眼笑的拉过我的手,拍小狗一般的拍了几下,学医好啊,学医有出息!还是我儿志向远大!
用母亲的话说,三百六十行中,唯有医生,不论在任何年代任何局势下,都能得以生存下来,而且备受尊敬。即便是兵荒马乱,也不至于饿了肚子讨饭去。
母亲朴素的生存之道,和我埋在心底的愿望,隔着十万八千里,却风驰电掣般的相向而撞,不谋而合。
三百六十行里,因为母亲,我独独挑中从医这一行;医学专业众多碗中,却是母亲,为我阴差阳错的选了最独特的碗。
而我至今仍小心翼翼并诚惶诚恐的手捧着这只碗,痛并快乐着。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三)
皮肤科历来以门诊取胜,故,病房常常不受重视。我所在的医院,只有门诊,没有病房。读研三年,从未到过病房,也从未到内外科轮转。除了专业知识,胸中,空空如也。
读研的三年,和其他专业的同学相比,我很逍遥。按时上班,按时下班。而这样的逍遥,也为将来埋下了痛苦的种子。试问,一个不会写病程录也不会管病人的住院医生,工作之后,要想踢开头三脚,会有多么难。
但在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只觉得自己选了一个好专业,乐得轻松。
考研之前,打破头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皮肤科医生,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闪过。本科的皮肤科课上,除了打瞌睡就是睡觉,睡的一张小脸红扑扑的,喷出的鼻息润湿了凉凉的课桌,罩上一层朦胧的雾气。讲台上老师匀速的讲课声调,是最好的催眠曲,偶尔咳嗽一下清清嗓子,惊醒了我,一抬头,幻灯上一张极其恶心的皮肤病图片快速闪过。小心翼翼掉个头,继续埋头大睡,与其被恶心无数,还不如昏睡百年。
上帝喜欢开玩笑,三年后,我也成了讲台上那个唱催眠曲的人。一眼扫去,讲台下仿佛一个个当年的我。我很想对这些孩子们说,偷着睡可以,但千万别打呼噜。
最初接触专业时,着实适应了一段日子。就像第一次上解剖实验课,虽然新奇,但心里也有些许的恐惧。
视觉冲击,让人很有压力。
虽然大部分时间里见到的病人,并没有教科书图片上那样恐怖,但偶尔遇见一两个比图片还恐怖的,这一天,都没胃口吃东西了。久而久之,当心足够强大时,即便是一边端着饭碗吃饭,一边翻看专业图谱,也一样大块骨朵,食之有味。
记得有一次,白天随老板出门诊的时候,见了一例“蜱叮咬”的病人。一位农村来的老婆婆,白天在山上拾柴,晚上回来,在小腿上发现好大一片红肿。来看门诊的时候,老人家的儿子用小瓶子装来了元凶,蜱。
老板来了兴致,即兴给我们几个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而我却对那小小的虫子产生了兴趣。晚上回到寝室,用室友的电脑,找出小虫子的放大图片,一边捧着饭缸,一边研究它长了几只爪。兴趣所致,又一口气找出其他经常几种引起皮肤的虫子,如疥螨、隐翅虫、刺毛虫、桑毛虫等等。看的手舞足蹈,还把图片发给彦锐,让他也开开眼界。
据彦锐后来回忆,我那一晚的“虫子开会”系列图片展览,让他一晚都噩梦不断。
我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断的在专业里寻找着有趣的东西。不知不觉,竟深深为它着迷。
误打误撞,竟也能找到喜欢的专业?!
我告诉彦锐,他和我的专业,在我心里的位置是一样一样的,都让我如此着迷。
彦锐听后,立即表示要继续努力。
“努力什么?”我问。
“努力比你的专业占据的位置更高一些,我不要和它成亲兄弟。”彦锐如是说。
我在屏幕的这一边,捂着嘴坏笑,小声的说,那你们就当爷俩吧,嘿嘿~~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五)
我从未想过,彦锐会是如此帅气的男子。我想象的他,戴黑框眼镜,中等身材,略胖,皮肤有些黑,一脸胡茬,整个儿一有些邋遢的中年男子形象。
结果,却恰恰相反。他皮肤白净,面如满月,浓黑剑眉,板寸,不胖不瘦。不笑时很严肃,可微微一笑,竟连桃花也要开了。
彦锐的帅,不是惊世骇俗,却很有亲和力。我后来戏称他为“少妇杀手”,从少女到中年妇女,老少通吃,尤其招年轻少妇喜欢。彦锐身上成熟男子的魅力,让人根本无法漠视。
而他的帅,却成了我自卑的源泉。
彦锐曾经不止一次问过我的样貌,我都含糊而过。自卑感,严重侵袭着我。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彦锐,丑小鸭和白天鹅,不该并肩而行。自然,我是丑陋的鸭子,他是美丽的天鹅。
彦锐也许觉察到我的自卑,有意无意的透漏他的审美观,女人漂亮与否,他根本不在乎,只要看上去舒服就行,熟悉了之后,谁还在乎眼前的人是不是漂亮。
对于彦锐的说法,我将信将疑。真有不爱美女的男人么?我很怀疑。
我年幼时,母亲总说自己生了个丑姑娘。还编了一套顺口溜用来形容我的样貌,豆角眼,两头尖,大鼻子,孔朝天,掉在地上摸不着,抱在怀里吓一跳。母亲年轻时很俊俏,父亲也很帅气,却偏偏生下了我这个丑姑娘。据母亲后来回忆,她当年怀着我的时候,最不喜欢我三叔。而我们家族的俊男美女中,唯独三叔是上天的败笔。老家有种迷信的说法,怀孕的时候,孕妇讨厌谁,将来孩子生下来反而像谁。母亲很后悔,当年一念之差,竟造成终生遗憾。
所以,我从小就讨厌照镜子。像男孩子一样在野地里疯玩,摔泥巴、吹口哨、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蛋等等,几乎忘记了自己也是个女孩。母亲又极其配合的为我剃了五号头,配上晒得黝黑的皮肤,不论从正面、背面还是侧面看,都是一个活脱脱的傻小子。
上帝还嫌不够热闹,又在我入睡之时,偷偷溜到床边,坏笑着在我的鼻梁上、脸颊旁撒上碎碎的米糠,从此,我又多了一条不愿照镜子的理由,雀斑。
一年年长大,样貌也有些许的变化,虽未曾脱落的花儿一样,却好歹不至于站在街上影响市容。只是平凡,平凡的仿佛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我。
上帝关上一扇门时,必定会为你留一扇窗。我没有漂亮的容貌,却有一头人人羡慕的黑发,光亮、柔顺、挺直。
华仔说,我的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我散开一头柔顺的长发,默默的想,如此平凡的我,会是彦锐的梦中情人么?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六)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却知道了彦锐的初恋情人。
彦锐的初恋女友,是他技校的女同学。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唯有一点不好,女孩的母亲从骨子里看不起彦锐。那种蔑视的眼神扫射在身上,如高瓦探照灯一样,让人从头到脚的不舒服。女孩母亲在背后挑拨离间,无所不能。偏那女孩耳朵根软,脾气又不好,听了母亲的话后,就和彦锐发脾气。一来二去,两人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最后,女孩还是跟彦锐分手,和一个颇有家底的男人去了上海定居。
初恋,在任何一个男人的心里,都无可替代。那是一段被无数个第一次填满的美好回忆,最初的悸动和最朦胧的美,即便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依然会让一颗心柔情似水,心如蜜糖。
彦锐是个不记仇的人,即便两人分了手,还依然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和彦锐一起去网吧,他的初恋正在线,彦锐让我看那女孩的视频,很温婉的一个女孩,虽然不是会让人眼前一亮,但看起来很舒服。两人像老朋友一样在QQ上聊天,我坐在彦锐身边,突然很羡慕那女孩,心里不禁涌上一丝酸涩。彦锐十分敏锐的扑捉到我的脸上一闪而过的落寞,一只大手霸道的拉过我冰凉的小手,和我十指相扣。他掌心里传来的温暖,让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我靠着他的肩膀,默默的想,不管这个男人曾经属于谁,但这一刻,是完全属于我的,只是我的。
网络上的我,和现实中差别很大。生活中,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从不多话,喜欢默默的躲在角落里,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大会和陌生人打交道,常常记不住初次见面的人,从名字,到样貌,即便是记住了,恐怕也要张冠李戴。
而网络上的我,却极其健谈。风趣、幽默,活泼、开朗,偶尔,也很调皮,喜欢捉弄人,但都无伤大雅,不至于让人过于尴尬。
彦锐说,程聿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姑娘,每次和你聊天,心里都很愉快。你就像我的解忧丸,什么不开心的事,和你说说,心里就会豁然开朗。
有一天,彦锐和我东拉西扯了半天,才扭扭捏捏的问我,家里人都怎么称呼我。
我正聊的高兴,脱口而出,“我爸喜欢叫我丫头”。
从此,丫头,成了彦锐对我最亲密的称呼。
不知不觉,彦锐叫我丫头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我也隐约感觉的到,彦锐对我,渐渐暗生情愫。
这一声“丫头”,一叫就叫了六年,直到我的眼角长出了细细的鱼尾纹,在彦锐那里,我依然是他口中的“丫头”。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七)
日子在无声无息中流淌,在近乎自虐的节省下,我的积蓄日渐多了起来,买电脑的日子指日可待。
就在这时,彦锐突然要离开这座城市,经人介绍去北京工作。
彦锐很兴奋,我却很失落。彦锐说,傻丫头,到了北京后,我们还可以像从前一样在网络上交流。我勉强打起精神,祝他一路平安。
彦锐去的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很大。彦锐初到北京,只是暂时做一些行政工作,并未单独接管案件。
彦锐带着无限的憧憬和希翼奔向北京,可到了之后,却被现实无情的奚落一番。北京土著的一贯排外和高傲自大,把彦锐这个外地人远远的排斥在圈子之外。而学历又将人分出三六九等,这个队伍里,随手一指,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彦锐不用比也知道,自己必定在那最末一等。
彦锐租住的房子离单位很远,是一个简陋的地下室,房间阴暗潮湿,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窗户微露于地面,手机常常收不到信号。房东是一对山西夫妇,承包了地下室,隔成几个窄小的单间,专门租给彦锐这种外地来的打工仔。地下室里住满了各色人物,无非都是千里迢迢漂泊于此谋生活的底层百姓。每天人来人往,人声嘈杂,隔着薄薄的木板墙,东家的吵架声和西家的炒菜声,不必侧耳倾听,也能清清楚楚的传到耳朵里。
彦锐的北漂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悄然开始。
彦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乘一个小时左右的地铁去上班,夜里又披着星光循着同样的路线回来。因为刚刚上班,彦锐手里接到的多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更多的时候,是别人不屑于做或不想做的杂事。由于是新人,彦锐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闷头完成好手里的工作。即便是这样,依然经常被同事调侃和嗤笑。
由于彦锐是东北人,在张口就是京腔的北京人眼里,他的口音可谓土的掉渣。东北人说话特点是咬音很重,而且很多时候平卷舌音分不很清,z c s和zh ch sh发出来通常都是一个调调,这样的发音后果是,那一首著名的“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的绕口令,用东北话说出来,和赵本山的小品一样逗乐。
其实彦锐的普通话,在我看来已经说的很标准了,但在北京的日子里,还是不时的被身边的同事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彦锐说,有一次单位发工资,他高兴的问同事,“发工织(资)啦?”同事马上校正,是“工资”而不是“工织”。彦锐后来把这段插曲当成笑话来讲,虽然是以颇为轻松的自嘲方式说与我听,但我却多少能体会彦锐当时心里的那份苦涩。
直到现在,彦锐仍坚持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管是出于律师职业本身的需要,还是对当年那段曾经过往的耿耿于怀,在他口中,再也听不到地道的东北口音。
而我那时的东北口音却是地道的很,浓浓的东北味儿还带着老家的乡土气息。我喜欢用独特的东北字眼儿,在和朋友聊天时,尽情的展示东北人独有的幽默。
在最初和彦锐接触的日子里,他对我说土话很是反感,不止一次的纠正我的发音。出于对他的理解,还有那份浓浓的爱,渐渐的,我说土话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后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虽不算很标准,语调之中如果细听,还混着些许的北方气息。但仅仅是这样,在工作后,在南方佬听来,已算是最标准的普通话了。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八)
临近夏天的时候,我的积蓄已经足够买一台二手电脑。正值学生毕业之际,恰好有很多人处理电脑。我在校内网上研究了好久,终于相中一台,恰巧在我同一宿舍的楼上。出售电脑的是一个即将毕业的本科女孩,确切的说,是两个。这台七成新的电脑,是她们二人共同所有。
在商量价钱的时候,出了一点小插曲,因为是二人共同财产,所以很不好砍价钱,谁都不想自己吃亏,最终以一千零二十元的价钱买了下来。这二十元任我磨破了嘴皮也没砍下来,两人把自己说的比我还惨,仿佛少那二十块,日子就没法过了。想想还是算了,不就多吃一周的白菜土豆么,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成交。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美滋滋的抱回了属于自己的电脑。
我记得,那是一台HP,外壳是我喜欢的天蓝色,17纯平,40G内存,对我这个电脑白痴来说,上网、聊天和看电影,已绰绰有余。大大的显示器放在书桌上,竟占去一半的桌面,仰着笨重的大头,不小心碰到,还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塑料声音。
我很满意,由于还没来得及去办理校园网络,只能守着黑色的屏幕傻笑。也许是两个女孩不怎么经常清洁,键盘里、屏幕上,沾满了灰尘还有油渍。我端来一盆温热的清水,用一块小手绢小心翼翼的擦拭了一番,连键盘的缝隙也不放过,竟然还清理出了几根瓜子皮。
换了两盆水后,电脑终于焕然一新,我手握着鼠标,靠在坐椅上,心满意足。
第二天,马不停蹄的办好了网络,又买来网线,跑来跑去的忙活了一天,终于可以上网了,当然,用自己的电脑。
在室友的帮助下,安装好了各种必备的软件,这其中,最最必不可少的,就是那只对眼的胖企鹅。
有了电脑之后,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网络。对着电脑吃饭,对着电脑看书,对着电脑发呆,张开怀抱,无怨无悔的接受辐射。
我是高度近视,近视的原因和其他爱学习的孩子们不太一样,有些难于出口。通常情况下,我只说这是家族遗传,几个姑姑都戴眼镜。而实际却是初中毕业那一年,捧着我家十二寸的黑白电视看了一个暑假的后果。
我怕买了电脑之后度数更要节节高升,于是,最初的日子里,常常是把椅子退到对面床的扶梯前,把耳机线拉的长长的,翘着二郎腿看电影和电视。后来,我和屏幕日渐亲密,不知不觉回到了正常范围内。
有了电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我和彦锐聊天,再不会被迫下线。而且,想聊多久聊多久。
彦锐说,那段在北京的日子里极其灰暗,而我是他生活中的唯一亮色。他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我晚上从医院下班回来的那几个小时。不管这一天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都会讲给我听。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
每天下班后,急三火四的冲向食堂,打了饭菜就疾步往宿舍奔。到了寝室,一边脱鞋一边开电脑。常常是一边抱着饭缸吃饭,一边和彦锐聊天。
只要有彦锐陪着我,即便吃白菜萝卜,也是美味佳肴。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十九)
彦锐说,丫头,等你毕业了,来北京找工作吧。
我说,好。
彦锐又说,你来北京的的时候,我去接你,好么?
我说,好。不过,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认错人怎么办?和彦锐聊天的时候,我很喜欢逗他。其实,他的样子,只那一眼,就刻在了心里,又怎能忘记?
我手上的疤痕是独一无二的,你一定不会认错人。彦锐也逗我。
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疤,人,亦如此,起码在我心里,无可替代。我在心底轻轻的说。
彦锐不是近视,只是有些散光,却很喜欢带眼镜。我是高度近视,没有散光,却不得不每天架着一副大眼镜。不过,戴眼镜也有额外的好处,就是看人看的格外清楚,尤其是帅哥。
我和彦锐说,有一次下班路上看到一帅哥,帅的掉渣,目不转睛的看,直到走出去很远了,还回过头眺望,结果,撞电线杆上了,眼镜差点撞碎。
彦锐听了哈哈大笑,说他有一次在街上无意中于前方见一漂亮的背影。长发飘逸,身形妖娆,走起路来,风姿卓越。心动之下,疾步跟过去。侧面一看,撇了撇嘴,再转到正面,则逃之夭夭。
我总结,从背面看是希望,从侧面看是失望,从正面看是绝望。
我说,如果见到了我,不论从哪一面看,都会是绝望。
彦锐严肃的说,你不一样。
彦锐刚去北京的时候,和我一样,没有自己的电脑,上班的时候用单位的电脑和我聊天,下了班后,只能隔三差五的跑到房东夫妇那里,用他们的电脑和我聊天。
房东的电脑放在一张小椅子上,彦锐只能蹲着和我聊天,每次聊天后,腿都会酸麻的要命。即便如此,彦锐仍然乐此不疲。房东大哥很好奇,和彦锐每天聊天的那个女孩,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彦锐笑笑,只说,大哥,你不懂。
一句不懂怎能满足这位大哥的好奇心,反倒让他更加好奇。有一天,房东大哥趁彦锐回房取手机的间歇,冒充彦锐和我聊天。一开始还好,可聊着聊着,我明显感觉不对。第一,彦锐的打字速度向来很快,不会像这位大哥一样,半天才蹦出一句。这样的速度,只有练一指禅的哥们,才能匹敌。第二,彦锐的说话习惯我知道,和他的风格完全不同。第三,彦锐知道我的情况,不会如他一样,上来就抓住我问东问西。
我,终于出于愤怒。
一会的功夫,彦锐回来了。房东大哥装作若无其事的在床上翻书,彦锐一上来,我就冲着他大发脾气。彦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终于弄清楚了状况后,也很气愤,一边对我好言安慰,一边问房东是不是确有此事。那房东自知理亏,讪讪的承认,只说一时好奇,并无恶意。彦锐用着人家的电脑,自然不好发作,只好将一口怨气吞了下去。
我却如惊弓之鸟,不依不饶。责怪他人走了为什么不把对话框关掉,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们之间的事情怎么可以和那老男人说,诸如此类,埋怨他半天。彦锐连连认错,不停告饶,直到等我出了这一口怨气,才算雨过天晴。
不过,经过这一次惊吓,我有了心结。如果再来一次,我怎么知道,那和我聊着的是彦锐,还是路人甲乙丙丁?
于是,彦锐想出了一个接头暗号,只有我们俩知道。一张憨笑的脸,和一朵鲜艳的玫瑰花。
每当我看到他将我们的暗号发送过来,都忍不住遐想,仿佛彦锐憨笑着举着一朵玫瑰,含情脉脉的望着我。
这种感觉,就是爱情么?那,爱情真甜蜜。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迫使彦锐下决心买电脑,却源自一场不快。
房东的老婆有个弟弟,二十出头,也在北京打工,偶尔会去房东家蹭吃蹭喝。偏偏每次去都能看到彦锐用他姐夫的电脑和我聊天,于是心中很是不快。那年轻人也想上网,偏彦锐又和我聊的没完,于是嘴里不干不净起来,在一旁摔摔打打。彦锐不是傻子,看出他的不快,于是匆忙下线,想把电脑让给他。男孩得了电脑,嘴里却还是骂骂咧咧,彦锐脾气上来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好在有房东夫妇拦着,才没打到一起去。
有了这一次不快,彦锐发誓要买台电脑,而且要买笔记本。
彦锐刚刚去北京没几个月,每个月那点工资,去了吃喝、房租、车费和日常零用,并没攒下多少。买电脑,说的容易,钱从哪来?
彦锐那次去北京,是一气之下走的。父母总说彦锐没出息,却好高骛远。彦锐面上不反驳,心里却很在意。憋着一股劲儿,要出来好好闯荡一番,将来好在父母面前抬起头来。可,出来混,哪那么容易。但就是再苦再累,彦锐都不曾和家里说过。自然这次买电脑的钱,彦锐也没想过要向家里人伸手。因为他知道,即便是伸手了,无非得到的是一通嘲笑。
正当彦锐苦闷之时,他的一个女同事主动借钱给他,这让他既高兴又惊讶。女同事是北大的法律系博士,有双学位,人很文静,长相却很普通,年纪和彦锐差不多。彦锐平时和她没什么交往,只是点头之交。这一次突然的示好,让彦锐很意外。
不过,彦锐并未多想,谢了同事后,连说等攒够了钱马上还给她。女同事波澜不惊的说,不急,这点钱,不算什么。等什么时候手里宽裕了,再还不迟。
彦锐有了钱后,没几天就捧回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银灰色的外壳,沉静而大方。
彦锐买回来电脑之后,第一时间内向我展示。通过视频,让我看他的笔记本。看他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我也替他高兴。高兴完了,我问他,从哪儿借的钱?彦锐和我说了女同事借钱给他的事。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恐怕,不是借钱那么简单。
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偏偏借给彦锐,难道是。。。。。。
我不敢往下想。
我提醒彦锐,有了钱早日还给人家,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单单借给你这么一大笔钱,会不会有什么企图。
彦锐大咧咧的说,能有什么企图,难不成借个钱还要我卖身了不成?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呸呸”几声,连说彦锐胡说八道。
尽管彦锐几次三番劝我不要瞎想,但我始终放心不下。彦锐是个帅哥,这样帅气的一个男子,天长日久的在眼前晃悠,又怎能保证,不会让那个女同事对了眼,动了心?
但愿是我多心了,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可,她到底为什么要主动借钱给彦锐?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