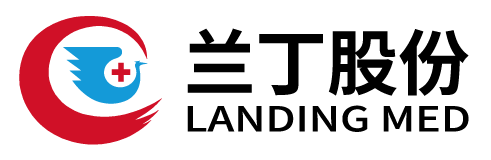2009年04月02日 10:06南方新闻网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 ,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2009年04月02日 10:06南方新闻网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 ,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