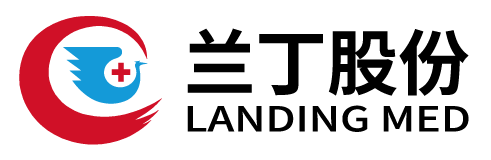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留学美国 author 海外流浪者99, 34岁
| |||
|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9-03-10 07:35:00 编辑
-
2.
我女儿读了一年高中,那一年,她每科都是A的成绩。她说:妈,在这儿读高中简直是浪费时间,学的东西是太简单了。而且她还没能得高中毕业证书,还得等学完所需的课程。其实我女儿离开中国时已在厦门的重点中学厦门一中学完高二。上完高二就已上完高三的课,因到了高三就是总复习准备高考,而且中国的中学理科学得比较深,难怪来到美国她觉得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都太简单了。我决定和NotreDame,我的母校,商量是否她能直接上大学。学院看到她的成绩,又看她英语托福成绩也很好,就吸收她了。原来在美国还有一种中学同等学历考试,我女儿在大学上了一学期后,参加了这种考试,也拿了同等学历的证书。这样她在美国公立中学只学了一年,我们在郊区只住了一年就搬回市区。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中。
我的女儿能上Notre Dame还幸亏一位不认识的老太太。她是Jay和 Rainy 的朋友叫Jean 。她的丈夫是辅金斯大学的数学教授。在一次车祸中,他的丈夫失去了生命,她活了下来,但一个人成了半个人。她的腰弯下,一头白头发,很长,又瘦又小,就像童话中的小女巫。Jay告诉我,她的命是检回来了,因医生都以为救不活呢。还没出车祸前,她是个打马球(polo)的好手。她再也不能打马球了,但她还经常去看马球比赛。Jay说她要借给我们钱,供我女儿上大学。因我在自费上硕士,她又自费上学士,两个人都上大学,太困难了。但我不肯向人借钱,也不肯请学校帮助,其实我是可以求助的。但我认为我们是已经得到许多帮助,我们是很有福的了。我们绝对能靠自己半工半读上完大学。但第一学期就很紧了,因私立大学学费较贵。而且我们还没拿到绿卡,听说国会通过后,那给中国学者永久居留权的条例被老布什否决了,大家说有绿卡是肯定的,但还得等。如果到公立大学读书,国际学生要交几乎是本州学生双倍的学费(Out of state tuition). 那么学费就和私立大学差不多了。
我毕竟是来没几年,我所活动的范围还很窄,现在想起来,我不该学理学硕士因我豪无工作经验,学位越高没经验毕业后越难找工作,而且找工作的城市就只在Baltimore,但是因继续攻读学位,才能把女儿顺利签来伴读。这也是上帝的恩惠。她以前申请过两次自费留学都被拒签了。中学的留学签证是很难得到的,而且母亲已在美,那移民嫌疑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她能顺利拿到签证,那是奇迹,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啊。
有一天,Jay给我一张从老太婆那儿来的5千元支票,还有她起草的借条。借条上写着:借给的钱是供我女儿读书,等到她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于一个月不超过200来还她。Jay是中人,要我签名收下。而且说每个学期都可借给我。这一辈子没向人借钱,我是非常不愿意借债。但她们非要我借不可。我接受了这五千就再也不肯借了。因一学期后,我女儿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也走上了半工半读的道路。
刚搬回市区,我们住在学院旁边的一老人家里。她的楼上有一套两房一厅。这位老人住楼下。本来这老人身体很健康,比起我们已前住过的任意一个还年青些,可能最多80吧。但她得了depression,一种我已前从不知道的病,可能是孤独引起的。在我们住的这地区,老人是有家庭医生上门来。她经常不起床,装病。一定要打电话让女儿知道。她就只这个女儿。在如何对待老人,我那时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其实Depression也是一种病, 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住在她楼上,对我们要求很简单,就是经常到楼下看看,她还能自己独立生活,如果老人有什么事向她女儿打电话。我们常到楼下看到她不吃什么东西,心里也很不安。但她什么也不让我做,就非让她女儿来不可。有一天,我们回到家,看到来了有十字的大车Van,看到四个彪形大汉,抬着担架进来,他们说老太的女儿决定要把她送进老人院。这位老太婆死也不肯去。她的手紧紧拉着床干子。她大哭大叫,要我们救救她。但这四个人有她的女儿的签字,硬把她的手剥下,把她拉上担架,带走了。看到这残景,我的女儿大哭起来。大骂老太的女儿太没良心了。本来我们对老太的女儿十分尊敬,是她叫我们来住的,老太婆走了后还让我们继续住,后来只收很少的房租。但那可怜的老太太的呼声永远还响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很大的震惊。我们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她女儿硬要把她送去老人院啊?
后来我在香港的好友家做客。和她一起去看她在老人院的90多岁老母。她母亲在家让女儿照顾了很久,到了九十多了才送老人院。那老人院是教会办的,照顾老人很是周到。进去要排队等很久。她几乎每餐都去喂她的母亲,生怕她妈妈不吃饭。她家到老人院很远,单花在来回车费就好几千港元一个月。看到她在喂她的妈妈,我想到这位美国老人,她就是因太孤独太凄凉而装病,为的是能让女儿多来几回,没想到得其反,被硬拉去老人院。那美国老人进去老人院后,更加depressed不久就去世了。她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家。钱是不少,但亲情太少了。人家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年青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地狱。这看来不是夸张。我们可看到了凄凉老人的不幸。
在我女儿毕业之前,那位借给我们钱的老太太得了胃癌。她是属于一种教会,不相信医院,只相信上帝的能力。她是在家中去世。在去世之前,她留下张亲自写给我们的信。她说那5千块是给我女儿读书用,不必归还,还另加了一张5千的支票给我们。当Jay拿着那封信给我们。我们很悲伤也很自疚。她和我们无亲无故,我们都来不及报答她的恩情,什么也没替她做过,她就走了。当我们去到她的墓地参加她的纪念会,只见一盒骨灰摆在石板上,前面摆了鲜花。就只有几个朋友,有Jay, Rainy,还有她从夏威夷来的哥哥,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儿,和Jean老太长得一模一样。
留学美国(7)
我的第一个babysitting的 工作是在学院墙上贴的条子help wanted找到的。当我和他们通了电话,知道是照顾一个五个月的女娃叫梅格。在电话交谈后,那天的第一次会面,是他们开车来校,带我去他门家。我刚见梅格的爸妈时,是吓了一跳。妈妈是一头长长的卷头发,爸爸不但有长长的大胡子,而且他的头发之长不亚于他老婆。就像是我们来美之前看到的那种喜皮士。这位母亲已没上班五个月了,打算先开始半工。她是社会工作者(Socialworker).她说工作时间可根据我的学习时间安排,非常灵活。所以我得到四个下午的工作。她到学校接我,然后丈夫回来后把小娃娃和我带上车,送我回家。他们是犹太人,两人都是大学毕业,男的是工匠。这娃娃的妈妈每天把自己奶水抽出来,一袋袋放在冰箱里。要喂娃娃时只要放到瓶子里,在水龙头的热水下冲,稍热就行了。我很好运气,因为这对夫妇是很好的人。他们在我工作一周后,主动把说好的每小时$4。 的工资提高到$5 。他们是吃素的。我在她家,我可找到吃的东西或煮我爱吃的。碰到节日或我大考时间冲突,我没上班,他们还照付工资给我。
后来我还在报上看到一篇对女主人的报导,原来她是非常尽职的社会工作者。常常在冬天天冷时分,和同事一起到处寻找无家可归者,把他们送到安置的地方。现在梅格已是大姑娘。我还和他们有来往。在申请我女儿绿卡时,他们是她的经济担保人,因我还是个学生呢。
另外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工作是在看到我的老师(我和她的照片就在首页)有一天贴在墙上的条子,替她的同学找 old-lady-sitter。她的同学也快60了吧,她的妈妈90岁了。这位老姑娘没结婚,但有一男朋友。他们周末都要出去航海。她需要我在周末去她家过夜因不放心90岁的母亲一人在家。我总是背着书包,在星期6上午到她家。晚上在那儿过夜,星期天才离开。这位90老太太是个非常不寻常的人。她非常顽强而且有识慧。听她讲话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非常幽默。我在那儿感到像回到我自己的外婆家一样。
早晨当我要把洗碗机里的碗碟拿出来,她会对我说:“我的姑娘,别剥夺了我唯一的工作。” 她坐在椅子上要站起来时,我伸手要扶她一把,她拒绝了。她说她必须自己站起来。吃完早饭,我可去学校或babysitting. 就在冰箱里给她留下三文治。如果没事,呆在家里,她听她的书 ,我看我的书。因她的眼睛不好,她只能听recording books.她还让我看她们年青姑娘时,到海军军校 (Naval Academy)和青年军官联欢的照片。她说,那时她们都幻想能吊到个英俊的小伙子。她也真的嫁给了一个军官,他们有了这个女儿。但他现已过世快四十年了。她现已90多岁了,上帝还要她多活几年。
晚餐总是一碗生菜色拉:埚苣,几片黄瓜,新鲜的西红市等。一人一碗。在冰箱里,包好的两块上好的肉鸡胸脯,或牛排,(steak)或猪排(steak),要用Broil 或fry都祥细写好注明,一定有烤马铃薯或烤地瓜,有时是mashed. 在我快准备好时, Set the table.又是她的工作。然后我们俩坐下,认认真真的enjoy这晚餐。晚餐后,甜食是一定要的。通常是冰其淋和一片蛋糕。晚餐后,她最喜爱的电视是Jeopardy . 她是那么喜欢,从不错过。
有一天她发现我牙疼,又不想去看牙医,因怕太贵。她催我去看牙医。她打了电话,安排了时间。祥细告诉我牙医的地方,是个私人牙科医生。在给我医治牙后,他不收费。他说他也有移民之经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Jean, (我的老太太),因她在电话中再三交代,要好好关照。 ”She is very fond of you.”牙医说。
要是她还活着她是一百多岁了。她是在99岁时去世的。
第三个插进去的美国人是一个德国老太。因我住的那朋友的分居丈夫,搬来和她住了。她离开她丈夫是因stepson对她不好。他的丈夫最终决定搬来她这儿。
Jay介绍我来这位老太家住。就在和Jay同一条街上。德国老太和她牙医的丈夫是犹太人,是经过千辛万苦才从纳粹手中逃出,来到美国。她的丈夫已去世,没有孩子,孤零一个人住五个房间的大townhouse。她说,现住第三层楼的学生将回德国。当他刚来时,玛利安老太心中很不舒畅,因这金发的德国小子是属于迫害他们的民族。在他来之前,她并不知道。只知道是Hopkins的学生。但这年青人彬彬有礼,在住了一学期后就要回去了。住进她家是不必交房租的,只需把拉积袋提出去就行了。老太孤零一人,爱有人进进出出。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对中国学生,连同他们的小女儿,也住在另一家的第三层,也是不用交房租的。主人对中国学生好感。相处容恰。在主人出门时,有中国学生替他们看家,十分放心。
有一天我从学院回来,看到家门口有For sale的牌子。老人告诉我,不用担心没地方住。她说她已和Jay商量好,把她家的三楼修好让我住。她说这房子不知什么时后才能找到买主。她的医生说她心脏有毛病必须到24小时有人看顾的地方。房子家产都给了这养老院,是比较好的,都是富有的老人住的地方。他们负责造顾她到死。要进去是不容易,还得排队呢。
留学美国(6)
我来美国留学,将经过的征程绝不是坦途,但她是有山有水的地方,神将给我所需要的。我的生活充满艰辛,但享有永不干枯的甜泉。来美国到了教堂接近了万能的神,它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重塑了我。我懂得什么是爱,忍耐,包容,奉献。我的神代表了真,善和美,是我的依靠和安慰。
来美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找到了中国朋友,那是在教堂认识的。实际上,在1980后到美的留学生很多,连同伴读来的家属就更多了。到了中国人的节日,我们都在教堂一起聚餐,每人带来一盘中国人自做的美食,来自五湖四海,摆在拼成一排的长桌上,可叫百家宴。
刚开始,因我没车。总是有热心的教友来接送,大多是台湾早期来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和他们都讲一样的方言,他们也讲和我们一样相当不错的普通话,但一听讲普通话的腔就知是南方来的。有不少歌,例“绿岛小夜曲”等 都一样喜欢。
从大陆来的学生,大都不是基督教徒,是来教堂认识中国乡亲的。我们常在教堂吃免费午饭,交流一整天。有个JohnsHopkins的大陆留学生,常常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混吃的来了!”但教堂确是个留学生能找到有爱心的亲人,朋友的地方。来到这,就像回到家一样。我们是借了美国教堂进行聚会的,而且是免费借给中国人的。常常是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集会。因星期天教堂是还主人使用的。后来我搬到加州,再回来就住到郊区了。有一次我回去找过,没找到,可能搬迁了。它是在Baltimore市区33街,叫亨通浸信会。此华人教会离约翰霍金斯大学不远。
我的父母虽是基督教徒,但自从解放后,我的父母不敢谈信教的事。唯一珍藏的一本圣经在文革时偷偷烧了,因知道红卫兵会来抄家。因而我们对基督教是一无所知的。唯听母亲多次给我们讲他们接受基督教的经过。那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占领厦门时,他们逃难到惠安乡下。有一年鼠疫流行,母亲说天天见很多裹在草席的死尸运出埋掉,后来死的人更多了,连埋都来不及。那时我还没出世,但已有上面的大姐和三个哥哥。三哥上面还有个姐姐,一岁多死了。三哥其时也得了上吐下泄。也快不行了。妈妈说那死的老鼠到处可见,逃都没地方逃。但就有传教士不怕死,开了大门让他们进去住。一位传教士给了母亲一包黑得像木炭一样的粉,让它给三哥吃。但母亲迟迟没用,这包黑炭粉有用吗?后来,看到三哥快不行了,就死猪当活猪医吧!妈把那包黑粉分几次,加了水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灌进哥的嘴里。奇迹发生了,他竟然不再拉了。过了几天他竟然会叫“妈,饿。”。我们一直不清楚那包黑得像炭的粉末是什么东西,但这奇迹使父母接近了教会,后来都洗礼了。父母亲所属教会是安息日会,是在星期六聚会的,后来我才知道是Seventh-day Adventist. 前年我回中国,听大姐说那真的是活性炭粉。在辽宁大学有位刚来的德国人一直在拉肚子,他的夫人问我哪能找到活性炭粉,后来我们在沈阳的安息日会拿到了。
那时在亨通教会的人很不多,就常只有二,三十人,有时才十多人。后来逐渐状大,有了自己的牧师。当我们在那儿时,没专职牧师。黄仰恩牧师是兼职来的,他和师母要开车一个多小时从别的地方来这儿。积极组织和接送的是位姓王的和几个早来的留学生,王先生是台湾人,约翰霍金斯大学物理学博士,他对我们影响最大。我写这些人是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永久的感谢。他们热情地向从大陆80年代来的留学生伸出友谊之手,让我们接近了万能的神,让我们在困难时有所依靠,不管我们信不信。其时,我们大都不信教,更谈不上奉献。每次最多就献一两块钱。而且就在那吃午饭,还得他们接送哪。
认识上帝,对我是不容易的。刚来时,上课的老师要是修女的话,她会在上课开始时,作祈祷。我总是半闭眼睛,等她说完,赶上一声“阿门”就完事了。在心灵上是没感动的。天主教的弥散从没去过。 大陆来的,尤其是经历文革的这一代人,看到牧师讲道时,要我们把圣经翻到哪一页哪一章的,我们心里就发毛,这不和我们那时读毛的红宝书差不多吗?千万不能刚从一个迷信出来又掉进另个迷信。但在这儿,我们可以公开发表我们的疑惑和争论,后来经过许多的亲身经历和许多的学习讨论,才逐渐认识了神,才在教堂受了洗。我是在美国得到了新生。
后来我参加轮值服务,经常买东西在那儿煮午饭给教友们吃。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大陆来的女孩子来到地下室煮饭的厨房找吃的。刚好冰箱空空的,她没找到可吃的,后来见她切了一块Butter往嘴里塞。她是饿极了。她弹一手好钢琴,也是像我一样插在洋人家的。那时很少华人请钢琴老师,否则她经济上应没困难的。听说她还是谋音乐学院校长的女儿。那时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都很辛苦,但大家都很吃苦耐劳,因为我们觉得受点苦值得,而且只是暂时的。 现在当然不同了,国内的工资和国外差距不再那么大了。
教会也有时组织郊外活动,大家在一起交流信息 互相帮助。有一些来约翰霍金斯大学的大陆交流学者都不打算回去。他们工作很努力,收入不高,又想尽量存点钱。有好几个就住在约翰霍金斯医院的附近。那时我们一来就被告知,那地方是“沦陷区”住不得。那儿的Townhouse几千块美元就能买到,但卖不出去,因是贩毒的地方。他们几个人合租一连屋,争取多人住在一起,因白天都不在家了,就只需个地方睡和煮饭。早晨出门后,门不用上锁,一起步行上医院搞研究,晚上一起走回家。他们说,那些想偷的都可以进去,家中没留值钱的东西,因大多数东西是拣来的。电视也是捡来的,家具也是拣来的,不怕偷。
留学美国(5)
1990年春天在学院Alison教授的极力推荐下,我参加了一个由中美友好协会出资组织的中国学者参观团,参加的几乎都是学文科的从大陆来的公派访问学者只有我和另一位加州来的是自费留学生。因是在六四后,绝大多数的访问学者也都留在美国了。我们访问了华盛顿首都,纽约市,费城,波斯顿等文化古城,名校和历史中心。除了在纽约市住旅馆以外,其他城市都住志愿者的家。我们的参观活动非常紧凑,每到一城市带队的都安排好活动内容。参观访问一个接一个,简直没休息,但这机会实在难得,大家都不怕累,紧跟着,带有笔记本认真记录,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和文学历史有关的人和记念馆,例如在纽约市还参观了林语堂故居。
梭罗于1837年刚进大学时就说过,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实现了这一愿望。在那里他仅花28美元多一点儿就建成起了自己的栖身的小木屋,每星期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生活。为维持这样简朴的生活,他一年只须工作六个星期就可以挣足一年的生活费用,剩下的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没有将这宝贵时光浪费掉,而是把它奉献给写作和自然研究。
|
刚到onclick="function onclick(event) {javascript: tagshow(event, " href="javascript:;" target="_self" %e7%be%8e%e5%9b%bd?);}?="">美国的前几年是很艰难的。插在美国人家,真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特别是那家要我一天干两小时家务以换取一间免费住的地方。这家是意大利人,女主人是很精打细算的,讲话不客气的人。她的先生是Hopkins的天文台台长。这位主人的外公还是名人,叫Guglielmo Marconi,发明无线电报系统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在他家的大书橱看到许多关于他的藏书。他们在意大利有大庄园。但这位女主人是个小气鬼。我是经布朗太太(Mrs.Brown)介绍过来的,她的先生是尼古拉。布朗,巴尔的莫港边上的那大水族馆(NationalAquarium)的馆长。布朗太太在我们学院学习。她是学院分配给我的大姐姐(bigsister and little sister program).当我来到的第一周,她就约和我见面。很少大姐姐像她那样认真负责的吧,可能我在那时是学院第一位大陆学生。她经常和我见面。第一年冬天来临时,她带我上她家,让我式了她的几件冬衣。她挑了几件长短大衣,非要“借”给我穿。她说这儿的冬天不像onclick="function onclick(event) {javascript: tagshow(event, " href="javascript:;" target="_self" %e5%8e%a6%e9%97%a8?);}?="">厦门,没这样的大衣不行。她还带我上Baltimore交响乐团。有时她没空,把票放到我的学院邮箱,每次都是两张,让我找人一起去看。然而,那时我没什么心思去,我的babysitting的那小娃娃的妈,就是团里拉大琴的,爸也在那。我都在忙学习和赚钱哪。
我刚来这家时对美国的家务事什么也不懂,但这位房主太太在教我做家务是非常耐心的,比如,吸尘,椅子一定得搬动,桌布必须掀起,床下必定得仔细,要弯下腰,灰尘才不会堆积在床下。她也耐心教我ironing,衣服,餐巾。我很惊讶那诌巴巴的餐巾,竟可变成那么漂亮。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学习当西方的家庭主妇来了,所以也就认认真真地做。虽然每天两小时,认真做家务,是可干很多活儿的。她每天都向我交代任务,经常向我强调在美国东西都很贵,必须懂得节约,在晚会完后,塑料盘子和刀叉还得收起,洗完以后再用。我也在那儿学会煮一些意大利餐。对我来说是辛苦,但后来变成我的一种新能力,我东西餐都会一手。她家有一条狗叫larry,翻译成汉语是拉痢,多难听的名字。还知道他们hello和goodbye都叫Ciao ciao.还记得这首歌吧。“啊朋友再见,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另一首我喜欢的意大利民歌是桑塔露琪亚。在这家还住有一位意大利来的女onclick="function onclick(event) {javascript: tagshow(event, " href="javascript:;" target="_self" %e7%95%99%e5%ad%a6?);}?="">留学生,她租一间房,一个月200。我们经常唱这两首歌,我唱汉语,她唱意大利语,算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吧。
在这家住了大约6个月,在署假班,碰到一位中年同学,她是老师。她自己一个人住。在问我住的情况后,她请我上她家去住。她家离学院远些,但她可在上班时把我顺路带到学院后,再去上班。她说我不必替她做事,只要她不在家时帮她喂喂猫。那时我有babysitting的工作,家长来校载我,下班把我载回家,所以我很高兴搬去她家住。她家在38街,不是有钱人区,但也不是坏人区,叫red-neck的区域。也就是保守的工人区。全是白人。听说黑人一进这区,屋顶或窗户会被砸,所以没黑人住这区。她叫玖迪,是爱尔兰人,家是连屋,走廊和屋顶都是绿色的。我才知道绿色是爱尔兰人最喜欢的颜色。
每天早晨我都在不到7点就到校了,因她还得开老远去上班。学院的校工都在忙着打扫教室和学校环境。我就静静的在看书,做onclick="function onclick(event) {javascript: tagshow(event, " href="javascript:;" target="_self" %e7%ac%94%e8%ae%b0?);}?="">笔记,还写日记,写信。那时没e-mail,都是书写寄回onclick="function onclick(event) {javascript: tagshow(event, " href="javascript:;" target="_self" %e4%b8%ad%e5%9b%bd?);}?="">中国。家中还有双亲,女儿和丈夫。信是每周都写的,不然,我现在怎有一大箱回信呢?还有那时写的日记,现在读那时写的日记,有的用英语写,有的用汉语写。白天讲英语,晚上梦中回中国讲的是汉语,醒来很奇怪到底是在哪?真是感慨万千那。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9-03-10 07:21:00 编辑
我在那时给很多家看顾小孩有的都是一周去一次人家,也较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母亲,有一份爱心和很强的责任感。我从小无形中已作了很多看小孩的工作了,因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爸妈不在家时,我是理所当然的看顾他们。记得小时候,我还带我的弟妹去 “远足”呢,因我们口袋都空空的,所以“远足”是别有心材的。那时从厦门到鼓浪屿的渡船是去不用买票,回来才买票,我记得票价是5分钱。 我就带我的弟妹乘船过了轮渡,到了鼓浪屿上了岸不出检票处,在那玩了一会儿,就可再乘船回来,这样就不用买票了。要是好运气,爸妈给我们几分钱,那时两分钱可买一条冰棒,有时两人共享一条,坐在小汽艇上过厦鼓海峡那是其乐无穷哩。大姐是十个兄弟姐妹的老大,其时已出嫁,我做为二姐姐,是常照顾弟妹 的。 我应该是从小就掌握了当小领导的本领和照顾小孩的耐心吧? 所以上学后,我当班长,很关照我的同学哩。
在 美国和孩子打交道时,我发现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爱他们,关怀他们,他们一下子就能体会到,而且和你特别知心。甚有个别几个和我的友谊很不寻常呢。在和孩子玩时想到, 当我是个母亲时,为了谋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享受这人间最美好的做母亲的快乐。想到在乡下,没有电灯,常常和老大,第一个孩子,天 刚黑,就躲到蚊帐里。我给他讲故事,有时讲完一个,儿子还要再一个,然而那时我是很累了,我常常是靠半记忆和半自编,故事越讲越短,讲得山穷水尽了,儿子还硬缠着要讲长的故事,后来我就说:“好吧,就讲一根竹子的故事,它长得很长,很长,很长...”他知道这个长故事再没舍好听了,也就绝望,睡了。 农民的孩子,大都很小就得放牛割草,甚至在田里干农活。有的一手牵着牛,背上还背着小弟妹。在我们下乡的农村还存在童养媳习俗。我们村有一个9岁的女孩,还经常背着小丈夫在放牛哩。这些童养媳,因家穷养不起。从小就被以一点点钱送走。要是这将来的婆婆心不善的话,她的地位很低。常常要服侍全家吃了,她才能吃,全家睡了她才能睡。
在美国,我所在的这地区,也就是中产阶级地段吧,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卧室。在床边都有书架和许多的儿童书籍。现在中国的城市的孩子,一家只生一个,他们的童年肯定大不一样了,也有了这些了吧?在孩子睡觉之前,我给他们读一篇 “ bed time story.” 睡前故事,书由孩子自己挑。有时候,孩子会把喜欢的故事,已经听爸妈读过的书,让我读。一般都在读完后,就乖乖的爬上床,躺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记得一个叫马修的三岁小孩,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住在我住的那条街上。还记得第一天到他家,他的妈妈已事先给他做了对新来的babysitter的详细介绍。当门铃响时,妈妈来开门时他就紧跟在后面。因是第一天,女主人花了时间细细的给我做了指示,几点孩子该吃饭,几点上床睡觉,出了事该给谁打电话。当妈妈和我讲话时,小马修把三只小指头塞在嘴里静静地听着。她的妈妈给了我一张书写的他和他弟弟的作息时间以及和他们联系的电话,包括邻居好友的电话。马修的Baby brother (娃娃弟弟) 叫亚当,他已含着假奶头睡香了。很多美国婴儿有含假奶头睡觉的习惯,他们把它叫 pacify (使婴儿宁静物)。当妈妈讲完,马修就迫不急待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他有着赤棕鱼颜色的头发,直直往上翘,个儿很小,但他的举止像小大人。他大方,充满热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当爸妈跟我讲再见时,他急忙拉着我朝窗口走去, “ Let’s go to the good-bye chair.” (让我们去坐在再见椅子上吧) 他说。他爬上窗边的一张大椅子,我们朝外面望出去,看到他家小车正在开出车库,车停在窗下片刻,车窗开了,爸爸妈妈向他摇手说再见,他和我向他们摇手说再见,就这样他们开走了。 小马修一点也不认生,不象有的孩子,第一次见了生人,父母要离开还会大哭小叫的。他严然象一位小主人。
马修该吃晚饭了。他坐在桌边,我端出他的妈妈给他准备好的晚餐,坐在桌边看他吃饭。他一会儿就吃饱了。我看他盘上还留下很多没吃完的。我对他说“马修,把它吃完吧,这晚餐太香了。” 他向我笑了笑说:“妈妈也总是说尽量多吃点吧,但爸爸说,要是真的吃不下也就算了。我现在已是尽量吃了啊。” 看他多狡猾呀!
在学院附近的家庭里都有很安全的小孩活动室,一般不必太操心。有时我读书给孩子听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纠正我的错误读音。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也练了我的英语听力,这工作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当我离开中国时,中学老师工资才80多人民币一个月,我一两个晚上的看小孩就可顶在中国一个月的收入。我赚下钱,除了存起来,还经常寄回中国。几年后我回国,发现国内发展很快,很多人的工资都提高了许多,我的生活比在国内的亲人还苦,也就少寄回国了。
我的功课是很重的,因不必交学费,我就尽量多学几门。我的指导老师 Alison说那太多了,我就对她说学不了,再drop吧, 但我从不必drop。而且后来我发现选修的科目,我要是选理科的话,我简直可不费力的得4分 (满分)。有一次署假,我修了一门数学。第一堂课是摸底考试,同学们都还没做出几道,我早就做完了,我检查了几遍就交上去。交完考卷我就离开了。第二堂课,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学这门,我吓了一跳因为Alison说这门挺难的,劝我以后才学。我正不知要说什么,老师给了我那摸底考卷,我得了满分。老师说:你不必来上了,我可给你4分。后来我明白,这间女子学院文科好,理科并不怎样。另外,中国学生中学的数学比一般美国学生强多了。我本来在读中学时功课很好,竟然那么久了还能记住,后来我学硕士学位时索性改学理科,因听说中国学生读英语专业难找工作。
这学院的文科老师,特别英语专业老师很强,很多老师是修女。那些修女老师就住在学院一座钟楼里面。她们终身未婚,对教学一丝不苟。文科班级很小,一般不超过十个。老师对每个学生了如指掌。在Notre Dame 相邻的是LoyolaCollege,专收男学生的,很多老师是天主教的Jesuit (男修士)。那间学院的理科就很有名。这两间学院共用一个图书馆。后来我听有的学科比Hopkins 还有名气。我完全可免费在那间学院修课,但刚来时,我对这些奥妙全不懂,虽然Alison 都有给我指出,我是一知半觉。我要是真的能减去十岁就好了。但我在ND修的不少门写作课使我终身收益。例如:“写回忆录”(writing memoir),写儿童书 ( writing for children), 商业书信( writing for business) , 写诗,如何写论文(做研究卡片,因写论文要标明每一句择语的出处) 等等。除写作还有各世纪的英美文学。后来我有了解到,大多数这种贵族学院出来的女孩子们毕业后不急着工作,很多结了婚,就专心在家照顾家和孩子了。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9-03-10 07:20:00 编辑
留学美国(3)
巴尔的莫 市区的北部是旧富人区,学院就坐落在这样的地方。刚来时,托普先生就交代我,学院的后面约克路不要去走,学院前面的查理大道可安全步行。我曾经从圣母学院门口的查理大道朝南走,要走大约一个小时才能走到他家。刚来时觉得有时走路也是一种享受,因查理大道一直到39街,全是非常漂亮的老殖民式的旧大房子,没有一座是一样的,每一家都有整齐的草地和花园,各种高耸入云的大树环挠。因我是从中国南方来的,而B 大约是中国的大连的纬度吧。当我在路上走,看着两旁的奇花异树,看到过去只能在书中看到的松鼠,它们就在我面前蹦跳,一点也不怕人靠近,每家门前都是象地毯一样的草地,一路步行难见一个行人,不象是走在闹市,而是在公园散步。大约半个多小时走到了39街交叉,如果一直走到底,可通往市中心直到港口,如果朝左拐就通往有名的约翰甫金斯大学 (
在我们学院学生休息室墙上有一布告处,经常有"help wanted"(需要帮忙) 的条子。根据美国法律14岁以下孩子,不能没大人陪而单独留在家,所以大人晚上出去得请 baby-sitter (陪小孩)来家呆着。每小时4 或5美金。后来我经常背着书包去当baby-sitter,特别是周末和假日,还有晚上。这就是我的主要经济来源。刚来时没钱买车,这是唯一的能做的工作。当我在学院墙上看到找帮工这样的小告示条子,一般都是住在这不远的人家,我就根据上面留下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去联系,她们一听到是ND的大学生,而且是个妈妈大学生,听到我在电话里和她们用英语交流,很流利清楚,一般都很喜欢。我告诉她们我没交通工具,需来校接我,而且送我回家,她们也没意见。这样我有了工作,家长开车来校接我,然后送我回家。当小孩睡了或自己在玩时,我可看书,不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