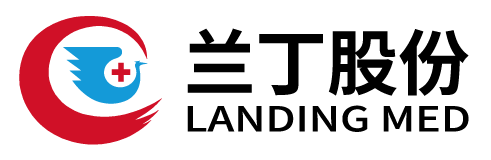| 图片: | |
|---|---|
| 名称: | |
| 描述: | |
- 浅 蕴 禅 思
-
禅给人最直观的联想,是在深涧竹林的幽径中缓缓拾阶而上的祥和老僧;明月下那一声清脆悠扬、震撼人心的钟鸣;空谷里与世无争的野花在山泉边怡然清冷的自开自落
借宿荒山古寺,院中的香炉升腾出氤氲缭绕的青烟,古朴浑厚的钟声在山林中盈盈回荡,召唤回点点归巢的昏鸦。大殿里宝相庄严的释迦牟尼沐浴在一片圣洁的大日佛光里,从莲台慈悲怜爱地俯瞰着劳苦忙碌的芸芸众生。在这神圣肃穆的殿堂里,就连落叶也带着几分飘逸的空灵,人的心智得到一种洗涤净化后的澄清明净,一切恩怨得失、爱憎情仇仿佛是前生的种种。禅,深,且冷。
据《世界史纲》记载:“佛教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我国。……此后中国遂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地区。佛教教义与儒、道观念在相斥相融、交错互动的复杂关系中相互取资、相互浸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诗歌、雕刻、绘画、建筑、音乐、人文……,都或多或少地注入佛教的元素。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无论从词汇语言、立意选材或是风格技巧,都得到极大的充实和丰富。
汉字是我见到的最独特、最具个性的文字,从外形看,她是世上唯一一种直立起来的文字,直立起来在空白的稿子上行走、奔跑,从外观就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纵横驰聘的张扬感和跳跃感,每个汉字里都包含着一个呼之欲出、蠢蠢欲动的灵魂,随时准备破茧而出、直冲霄汉。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与禅结合得最紧密且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首推诗歌,在禅与诗长期水乳交融的浸染中,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应运而生,--禅诗。禅诗可谓中国古典诗词中独秀一支的奇葩,古代的许多文人墨客毕生致力于禅诗的摸索和完善,为禅诗今后的大放异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谢灵运、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都有脍炙人口的禅诗问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一年)。据《旧唐书 文苑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年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薛王、宁王待之如师友……。”由此可见王维的青年时代是何等的春风得意、盛极一时。王维不光文采过人,还精通绘画、擅长音律,《历朝诗话》有着这样的记载:“王维未冠,文章著名,妙弹琵琶。春试之日,岐王引致公主第,使为伶人近主前,续进新曲,号《郁轮袍》。”
王维早年凭借过人的才华征服当时的达官显贵,一路平步青云地扶摇直上。政治上的得意让他这时期的作品多为雄浑旷达的豪迈之作,如《从军行》、《燕支行》、《少年行》等,无不尽显匡扶社稷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
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弟后调大乐臣,坐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一年,王维初次尝到官场失意的打击。长安厚重的城墙下,两扇朱红的城门徐徐开启,王维在一群友人的簇拥下缓缓走出长安。空中,残阳如血,遮天蔽日的风沙哽咽着祝福的话语,王维瘦削的背影在萧瑟的西风中频频回首挥袖,渐行渐远...... 身后,有家、有想念、有友人在呜咽吹奏凄凉的离萧;身边,一瘦马、一壶酒、一卷画、一琵琶;身前,是一条不知延伸到何方的漫漫长路。
据《世界史纲》记载:“佛教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我国。……此后中国遂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地区。佛教教义与儒、道观念在相斥相融、交错互动的复杂关系中相互取资、相互浸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诗歌、雕刻、绘画、建筑、音乐、人文……,都或多或少地注入佛教的元素。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无论从词汇语言、立意选材或是风格技巧,都得到极大的充实和丰富。
汉字是我见到的最独特、最具个性的文字,从外形看,她是世上唯一一种直立起来的文字,直立起来在空白的稿子上行走、奔跑,从外观就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纵横驰聘的张扬感和跳跃感,每个汉字里都包含着一个呼之欲出、蠢蠢欲动的灵魂,随时准备破茧而出、直冲霄汉。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与禅结合得最紧密且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首推诗歌,在禅与诗长期水乳交融的浸染中,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应运而生,--禅诗。禅诗可谓中国古典诗词中独秀一支的奇葩,古代的许多文人墨客毕生致力于禅诗的摸索和完善,为禅诗今后的大放异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谢灵运、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都有脍炙人口的禅诗问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一年)。据《旧唐书 文苑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年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薛王、宁王待之如师友……。”由此可见王维的青年时代是何等的春风得意、盛极一时。王维不光文采过人,还精通绘画、擅长音律,《历朝诗话》有着这样的记载:“王维未冠,文章著名,妙弹琵琶。春试之日,岐王引致公主第,使为伶人近主前,续进新曲,号《郁轮袍》。”
王维早年凭借过人的才华征服当时的达官显贵,一路平步青云地扶摇直上。政治上的得意让他这时期的作品多为雄浑旷达的豪迈之作,如《从军行》、《燕支行》、《少年行》等,无不尽显匡扶社稷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
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弟后调大乐臣,坐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一年,王维初次尝到官场失意的打击。长安厚重的城墙下,两扇朱红的城门徐徐开启,王维在一群友人的簇拥下缓缓走出长安。空中,残阳如血,遮天蔽日的风沙哽咽着祝福的话语,王维瘦削的背影在萧瑟的西风中频频回首挥袖,渐行渐远...... 身后,有家、有想念、有友人在呜咽吹奏凄凉的离萧;身边,一瘦马、一壶酒、一卷画、一琵琶;身前,是一条不知延伸到何方的漫漫长路。
那次坎坷的经历似乎为王维的归隐山林埋下伏笔,张九龄执政后,王维屡得升迁,而王维已无心从政,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据《旧唐书 文苑传》记载:“……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王维的归隐有他消极避世的颓废倾向,可是在君权主宰一切的封建王朝里,这恰恰正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温和反抗。远离污秽混沌的浊世,寄情山水,伴着月色终老,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唯一能操守的高洁情怀。
王维在与天地万物融洽和睦的相处中,将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禅相结合,不光展现出大自然恬静安详的美景,还流露出浓浓的禅机禅趣。这时期他的诗作已达到返璞归真的化境,尽显“幽冷入禅”的触目惊心的美感,即便是清风徐徐、浮云游动,都向他传达着天空或悲或喜的复杂心情。如他在《酬张少府》中写到:“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个内心清静远离尘嚣的长者,就这么豁达超脱的频频出没于月下的松林,无忧无惧亦无喜。
王维的生活孤独但并不冷清,他偶尔会到《临湖亭》等待来访的友人:“轻舟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王维的心境平静但并不麻木,风景蕴含生灭之妙的细微变化也逃不过他敏锐的观察,有时他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尔还会“偶遇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不再是王维,而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他本身就是一道旖旎动人的风景。 如他在《竹里馆》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在月下,人在竹中。一个散发抚琴的老叟,就这样缓缓被合进一叠叠厚重的古籍中,又在红烛下一页页翻动书的声响和伏案阅读的惊叹中复活。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一○七一年)。其文大开大阖、纵横恣意,如行云流水般淋漓酣畅,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间齐名,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驾齐驱,时称“苏辛”;还精通书画,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可谓百年罕见的旷古奇才。
据《宋史轶闻》记载,苏东坡出生时,有一仙人夜降苏家,对苏东坡之父苏洵说,我能让你儿子位极人臣、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也能赐予你儿子惊世之才,两者只能选其一 。苏洵最终选择了才华,一代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由此而生。这等六师外道的野狐禅自不足信,不过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苏东坡受人尊崇的地位不是一般。
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壮志难展,屡屡遭到贬谪流放。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在此他广泛的结交吴越名僧,与众多禅师悟道参禅、斗试机锋,曾自言前生是僧人。
和王维不同的是,苏东坡的禅诗更注重理性的思辨,并不是一味表达唯心主义的禅旨禅意,诗人凭借自己柔软敏锐的触角和通透深刻的理解力对形而上学的认知发出这样的疑问,--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东坡的光芒不光是一个时代的骄傲,还是后世子孙的自豪。正如他在《题西林壁》中所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只有真正跳出此山中的哲人,才会有这种睿智清澈的眼神吧?
禅诗的形成,使得一种新兴的文学团体蓬勃而生,--诗僧。诗僧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支遁、慧远、宝月等人堪称那时期的代表。到了唐朝,诗僧们名家辈出,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各显神通,禅诗的成就也达到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寒山、灵一、皎然、灵澈、封干、拾得等……。
寒山,姓名(一说俗家姓谢)、籍贯、生卒年均不祥,约唐玄宗及唐代宗年间在世,早年为官,因仕途坎坷而隐居天台翠屏山。寒山的一生被赋予了几分神秘色彩,翻开《旧唐书》、《新唐书》、《大唐才子传》,都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甚至打开集佛门高僧大全的《五灯会元》,也只能找到他和封干、拾得交往论禅时几个零碎的片断。
寒山的一生与世无争、清静无为,在他隐居寒岩的日子里,每有篇句即题于石壁树身上,天地万物赐予他的感触和顿悟,又被他慷慨无私的回馈给自然界。在百花争艳、诗人们异常活跃的唐代诗坛,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就象一簇被淹没在森林里的灌木丛,从始至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后人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录诗三百余首,这道苍凉的回音才在后世的传诵声中褪尽尘埃,光芒四现。
在他的《人生不满百》,诗人表现处超然物外、湛然静观的理智和洒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秤砣落东海,到底始知休。”寒山的可贵在于他的无欲无求、自在随缘,他在《一住寒山》里这样写道:“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位“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的隐者似乎没有预料到自己无牵无挂逍遥来去的身影,就象湖面上随波飘荡的不系扁舟,轻盈自如的在后世子孙的眼前来回穿梭。读寒山的诗,让我明白了人是生活在苍穹下的生物,除了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还要有所敬畏地对天地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种平稳祥和的心态。
历代诗僧多偏好竹、月、风、琴,信手拈来的一花一叶皆可入诗,清新温润中透出孤峭冷幽、超凡脱俗的禅机。以琴为例,宋代诗僧雪窦重显的《赠琴僧》便是一绝:“太古清音发指端,月当松顶夜堂寒。悲风流水多呜咽,不听希声不用弹。”而诗僧止翁的《无弦琴》同样出手不凡:“月作金徽风作弦,清音不在指端传。有时弹罢无生曲,露滴松梢鹤未眠。”
据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日本诗僧的成就夸夸其谈,我倒是看过一些日本诗僧的作品,当然是译本,也未见其高深,也许是因为水平的缘故,总以为言过其实,不知他有没有看过中国诗僧的作品?
王维的归隐有他消极避世的颓废倾向,可是在君权主宰一切的封建王朝里,这恰恰正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温和反抗。远离污秽混沌的浊世,寄情山水,伴着月色终老,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唯一能操守的高洁情怀。
王维在与天地万物融洽和睦的相处中,将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禅相结合,不光展现出大自然恬静安详的美景,还流露出浓浓的禅机禅趣。这时期他的诗作已达到返璞归真的化境,尽显“幽冷入禅”的触目惊心的美感,即便是清风徐徐、浮云游动,都向他传达着天空或悲或喜的复杂心情。如他在《酬张少府》中写到:“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个内心清静远离尘嚣的长者,就这么豁达超脱的频频出没于月下的松林,无忧无惧亦无喜。
王维的生活孤独但并不冷清,他偶尔会到《临湖亭》等待来访的友人:“轻舟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王维的心境平静但并不麻木,风景蕴含生灭之妙的细微变化也逃不过他敏锐的观察,有时他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尔还会“偶遇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不再是王维,而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他本身就是一道旖旎动人的风景。 如他在《竹里馆》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在月下,人在竹中。一个散发抚琴的老叟,就这样缓缓被合进一叠叠厚重的古籍中,又在红烛下一页页翻动书的声响和伏案阅读的惊叹中复活。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一○七一年)。其文大开大阖、纵横恣意,如行云流水般淋漓酣畅,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间齐名,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驾齐驱,时称“苏辛”;还精通书画,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可谓百年罕见的旷古奇才。
据《宋史轶闻》记载,苏东坡出生时,有一仙人夜降苏家,对苏东坡之父苏洵说,我能让你儿子位极人臣、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也能赐予你儿子惊世之才,两者只能选其一 。苏洵最终选择了才华,一代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由此而生。这等六师外道的野狐禅自不足信,不过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苏东坡受人尊崇的地位不是一般。
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壮志难展,屡屡遭到贬谪流放。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在此他广泛的结交吴越名僧,与众多禅师悟道参禅、斗试机锋,曾自言前生是僧人。
和王维不同的是,苏东坡的禅诗更注重理性的思辨,并不是一味表达唯心主义的禅旨禅意,诗人凭借自己柔软敏锐的触角和通透深刻的理解力对形而上学的认知发出这样的疑问,--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东坡的光芒不光是一个时代的骄傲,还是后世子孙的自豪。正如他在《题西林壁》中所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只有真正跳出此山中的哲人,才会有这种睿智清澈的眼神吧?
禅诗的形成,使得一种新兴的文学团体蓬勃而生,--诗僧。诗僧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支遁、慧远、宝月等人堪称那时期的代表。到了唐朝,诗僧们名家辈出,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各显神通,禅诗的成就也达到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寒山、灵一、皎然、灵澈、封干、拾得等……。
寒山,姓名(一说俗家姓谢)、籍贯、生卒年均不祥,约唐玄宗及唐代宗年间在世,早年为官,因仕途坎坷而隐居天台翠屏山。寒山的一生被赋予了几分神秘色彩,翻开《旧唐书》、《新唐书》、《大唐才子传》,都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甚至打开集佛门高僧大全的《五灯会元》,也只能找到他和封干、拾得交往论禅时几个零碎的片断。
寒山的一生与世无争、清静无为,在他隐居寒岩的日子里,每有篇句即题于石壁树身上,天地万物赐予他的感触和顿悟,又被他慷慨无私的回馈给自然界。在百花争艳、诗人们异常活跃的唐代诗坛,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就象一簇被淹没在森林里的灌木丛,从始至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后人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录诗三百余首,这道苍凉的回音才在后世的传诵声中褪尽尘埃,光芒四现。
在他的《人生不满百》,诗人表现处超然物外、湛然静观的理智和洒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秤砣落东海,到底始知休。”寒山的可贵在于他的无欲无求、自在随缘,他在《一住寒山》里这样写道:“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位“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的隐者似乎没有预料到自己无牵无挂逍遥来去的身影,就象湖面上随波飘荡的不系扁舟,轻盈自如的在后世子孙的眼前来回穿梭。读寒山的诗,让我明白了人是生活在苍穹下的生物,除了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还要有所敬畏地对天地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种平稳祥和的心态。
历代诗僧多偏好竹、月、风、琴,信手拈来的一花一叶皆可入诗,清新温润中透出孤峭冷幽、超凡脱俗的禅机。以琴为例,宋代诗僧雪窦重显的《赠琴僧》便是一绝:“太古清音发指端,月当松顶夜堂寒。悲风流水多呜咽,不听希声不用弹。”而诗僧止翁的《无弦琴》同样出手不凡:“月作金徽风作弦,清音不在指端传。有时弹罢无生曲,露滴松梢鹤未眠。”
据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日本诗僧的成就夸夸其谈,我倒是看过一些日本诗僧的作品,当然是译本,也未见其高深,也许是因为水平的缘故,总以为言过其实,不知他有没有看过中国诗僧的作品?
标签:
-
本帖最后由 于 2007-03-06 20:01:00 编辑